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角色扮演游戏《光与影:33号远征军》(Clair Obscur: Expedition 33) 的核心叙事如何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关键思想产生深刻共鸣。通过细致考察游戏设定的“绘母”诅咒、远征军的宿命抉择、以及“光与影”交织的美学风格,本文将揭示其与萨特“存在先于本质”、加缪“荒谬”与“反抗”、以及波伏娃“模棱两可的伦理”等核心概念的内在联系。文章认为,《光与影:33号远征军》不仅是一款具有独特美学追求的游戏作品,更是一面映照人类在绝境中探寻意义、自由与责任的哲学明镜。
引言:光影交织的末世悲歌与存在的回响
引言:光影交织的末世悲歌与存在的回响
角色扮演游戏《光与影:33号远征军》以其独特的背景设定,将玩家引入一个濒临毁灭的世界。故事发生在一座名为“卢明城”(Lumière)的破碎都市,这座城市酷似法国“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巴黎,却笼罩在末日的阴影之下。一种被称为“绘母”(Paintress)的神秘存在,每年会给人类降下诅咒:特定年龄的人们将化为尘埃,走向虚无。这一残酷的设定,无疑将“死亡”这一人类永恒的终极命题,直接推向了叙事的中心舞台,迫使游戏中的角色与玩家共同面对一种“集体的绝症”。
与此同时,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以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其核心关切恰恰在于个体的自由、选择、责任、生命的意义,以及人在荒谬世界中的根本处境。他们深刻地探讨了人类在面对虚无与绝望时,如何通过自身的行动来创造价值,定义自我。
本文的主旨在于细致地分析《光与影:33号远征军》的剧情叙事如何与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相互辉映,并揭示其内在的深刻关联。文章将依次探讨游戏中的“绘母”诅咒所体现的加缪式“荒谬”,远征军队员在绝境中的选择如何印证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他们的行动又怎样呼应了加缪的“反抗”精神,以及在“光与影”交织的道德困境中,波伏娃“模棱两可的伦理”所提供的阐释框架。本文认为,电子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媒介,其互动性和叙事性使其具备了承载和探讨深刻哲学思辨的巨大潜力。《光与影:33号远征军》正是这样一个范例,它不仅追求独特的美学表达,更试图引发玩家对存在意义的深层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游戏标题中的“Clair Obscur”一词,即意大利艺术术语“Chiaroscuro”(明暗对照法)的法语表达,其意义远不止于一种视觉风格。它更像是一种哲学宣言,预示着游戏将深入探索存在的二元性、模糊性,以及在一个缺乏绝对清晰性的世界中对真理的艰难求索。艺术中的“Chiaroscuro”技法,通过光与暗的强烈对比,在揭示的同时亦有所隐藏,暗示着真理并非全然敞开,而是在光影的微妙互动中才得以瞥见其残片。这种对世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强调,与存在主义,特别是波伏娃关于人类境况“模棱两可”的论述,形成了天然的呼应。开发团队(法国工作室Sandfall Interactive)选择使用一个法语词汇来指称一个源于意大利的艺术概念,这本身也将其作品更深地植根于法国的文化与思想谱系之中,从而使得游戏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对话显得尤为贴切与自然。因此,从标题开始,《光与影:33号远征军》便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哲学张力的光影世界。
一、 荒谬的画布:绘母的诅咒与存在的虚无感
一、 荒谬的画布:绘母的诅咒与存在的虚无感
《光与影:33号远征军》将玩家抛入一个被“绘母”的阴影所笼罩的世界。这位神秘的“绘母”,如同命运的冷酷化身,每年都会在一个巨大的石碑上刻下一个新的数字。一年之后,所有达到这个年龄的人类,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做过什么,都将无一例外地化为尘埃与猩红的花瓣,消散于虚无之中。这种设定创造了一种集体性的、可预知的“死亡判决”,一种持续了67年的倒计时。每一个新数字的出现,都意味着又一批生命的终结,也意味着幸存者离自己的大限又近了一步。
这幅由“绘母”描绘的末世图景,与阿尔贝·加缪在其哲学著作中深刻阐述的“荒谬”(L'Absurde)概念形成了惊人的共鸣。加缪认为,“荒谬”并非存在于人或世界本身,而是源于人类内心深处对理性、意义和清晰性的永恒渴望,与宇宙那令人绝望的非理性、冷漠和沉默之间的根本冲突与断裂。人类试图为混乱的世界赋予秩序,为无意义的存在寻找目的,但宇宙却以其顽固的沉默回应着人类的追问。在《光与影:33号远征军》中,绘母的诅咒正是这种宇宙非理性的完美体现。它为何存在?它的动机是什么?游戏似乎并未提供明确的答案,这种不可理喻、无从解释的特性,正是其荒谬性的核心。它强加于人类的命运是冷酷无情、不可抗拒的,人类对生存的执着渴望,在这种命运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构成了一种“令人痛心的前提,给整个故事蒙上了一层沉重的忧郁”。
“绘母”这一形象,与其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反派,不如说是加缪笔下那个冷漠、沉默宇宙的具象化身。她的行为并非出于可被理解的恶意或某种复杂的阴谋,而更像是一种固定的、不可动摇的程序,一种如同自然法则般(例如衰老与死亡)无情运作的机制。她的动机成谜,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天灾”,这使得人类的反抗更像是在对抗一种形而上的、无法根除的生存困境,而非一个有具体弱点和目标的敌人。因此,远征军挑战“绘母”的行动,其本质更接近于挑战存在本身的荒谬性。
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看似毫无意义的死亡,游戏中的角色(并延伸至体验其处境的玩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强烈的虚无感、焦虑与绝望。正如游戏资料所述,“卢米埃几乎没有人未曾以某种方式被死亡所触动。城市的孤儿院里挤满了孩子……夫妇们则在争论是应该为了人类的延续而生育后代,还是选择不将新的生命带到这样一个凄凉的世界”。这种弥漫在整个卢米埃城的集体性绝望,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质疑,正是荒谬体验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当个体意识到其存在如同在巨大的、冷漠的机器中等待被碾碎的齿轮时,对“为何存在”的追问便油然而生,正如加缪所言,某些创伤性的生命体验,或是对生命重复性的疲倦感,都可能唤醒我们内心的哲学家,让我们开始质疑既有的叙事与意义框架。
更深一层来看,游戏所设定的“破碎的现实”(fractured reality),特别是卢明城——这个“美好年代巴黎的超现实复制品,其中的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等地标被‘断裂’(Fracture)的奇异效应所扭曲、变形和破坏”——本身就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强有力的视觉隐喻。它象征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所经历的那种传统价值观崩塌、确定性丧失的精神图景,而这正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兴起的沃土。正如日本在二战后因巨大的失落感而使存在主义思想得以传播,“美好年代”本身,虽被视为艺术与进步的黄金时期,但也潜藏着“在耀眼的现代性之下有什么东西正在动摇的潜在感觉……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游戏中“断裂”事件对大陆的毁灭以及卢米埃城的破坏,就如同历史的创伤撕裂了昔日稳定与繁荣的幻象。这种对一个理想化、充满怀旧色彩的过去的物理性摧毁,恰恰平行于存在主义者所直面的那种意义与秩序的心理与哲学“断裂”。因此,《光与影:33号远征军》的游戏环境,本身就构筑了一个充满存在主义危机的象征性景观。
二、 “存在先于本质”:远征军的选择与自我塑造
二、 “存在先于本质”:远征军的选择与自我塑造
在这样一个被荒谬所主宰的世界里,个体如何自处?让-保罗·萨特提出的核心命题——“存在先于本质”(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解答视角。萨特认为,人并非生来就带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本质、目的或蓝图,如同工匠制造一把裁纸刀那样,先有其定义和用途,而后才有实物。恰恰相反,人首先是“存在”的,他出现在世界上,遭遇各种处境,然后,也只有在之后,他才通过其自由的选择和行动来定义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因此,人是其自身未来的塑造者,他要对自己是什么负全部责任。这种绝对的自由,也带来了与之相伴的沉重责任——人“被迫自由”(condemned to be free),因为他无法逃避选择,也无法逃避为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负责。
《光与影:33号远征军》中的角色们,正是被“抛入”(thrownness)这样一个生命被预先宣判、意义似乎已被剥夺的世界。然而,面对这严酷的“境遇”(situation)——萨特戏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强调环境为人物提供行动和选择的舞台,而非仅仅是情节的点缀——一些角色并没有选择坐以待毙或在绝望中沉沦。他们选择加入“33号远征军”,一个以杀死“绘母”、阻止人类灭绝为目标的行动,尽管其成功率先前一直为零,所有先前的远征队都未能阻止绘母,甚至未能返乡。当被问及为何要加入这样一场看似毫无希望的远征时,答案或许正如资料中所言:“但他们又能失去什么呢?”。
这个看似绝望驱动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存在先于本质”的体现。这些远征军队员,并非天生就是英雄或反抗者。他们的“本质”——作为反抗者、作为为人类存续而战的人、作为在虚无中寻找意义的勇者——是在他们做出加入远征这一自由选择,并投身于这一行动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游戏的主角古斯塔夫(Gustave),作为远征队的领导者,他的每一个决策和行动都深刻地定义着他自己以及团队的命运。其他角色,如面对巨大忧伤仍能保持“感染性乐观”的希尔(Sciel),以及“雄心勃勃地想要解开绘母之谜”的露恩(Lune),他们的人格特质与动机,同样是在这极端境遇下,通过自身的抉择与行动,对自我本质进行着不懈的锤炼与定义。
远征本身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体的萨特式“筹划”(project),旨在逃避“坏信仰”(mauvaise foi)。所谓“坏信仰”,即个体通过自欺来否认自身的自由和责任,将自己视为环境或命运的被动产物,以逃避自由所带来的焦虑。在卢米埃城中,那些选择对“绘母”的威胁视而不见、或沉溺于虚假希望、或仅仅是麻木地接受命运安排的人们,可能就陷入了不同形式的“坏信仰”之中。例如,关于是否还要生育孩子的争论,就暗示了社会中存在着多种应对绝境的方式,其中一些可能就是试图在毁灭的阴影下维持“正常”生活的自欺。相比之下,远征军队员们则以一种决绝的姿态,直面了存在的残酷真相和自身选择的自由,他们选择了一条即使可能通向死亡,却充满真实性的道路。这一行动是对萨特所批判的“严肃精神”(spirit of seriousness)——即将价值视为客观既定之物,而非个体自由创造的结果——的有力反击,也是对波伏娃所描述的那些将自由屈从于所谓无条件价值的“严肃的人”(serious man)的回避。因此,远征不仅仅是塑造个体本质的行动,更是一种集体性的姿态,反抗着在巨大荒谬面前社会性地陷入“坏信仰”的诱惑。
这些行动的重量,并不仅仅体现在其悲壮色彩上,更在于其所承载的责任。游戏中提及,玩家在远征途中会面临诸多“有意义的选择和利害关系”。这些选择,往往不仅关乎角色个人的生死存亡,更可能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安危,乃至人类文明的最终命运。这深刻地体现了萨特所强调的,个体的选择不仅是在为自己选择,也是在为全人类选择一种存在的范式。即使远征最终失败,他们以自由意志所进行的抗争行动本身,也构成了他们存在的意义。他们的“本质”,正是在这充满艰险与抉择的求索过程中,被一锤一凿地锻造出来。
甚至在微观的游戏机制层面,我们也能看到“存在先于本质”的影子。诸如古斯塔夫通过不断攻击来积攒“充能”以释放强力技能“超载”(Overcharge),法师露恩通过施放特定法术来获得“元素污点”(elemental stains)以组合更强大的魔法,以及希尔(Sciel)需要管理“光暗相位”和“卡牌堆叠”来有效使用技能等独特的战斗机制,都可以被解读为“本质创造”的缩影。这些角色在战斗中的效能,即他们在特定情境下的“本质”,并非预先固化,而是需要玩家通过积极的策略选择和持续的行动(例如,古斯塔夫必须先“存在”地去攻击,才能“本质”地拥有充能)来动态地构建。玩家与这些系统的互动,本身就是一个持续选择行动以积累力量或触发特定能力的过程,这与哲学上个体能力与身份并非固定,而是持续投入与选择的结果这一观念不谋而合。游戏中提及的“皮克托升级系统”(Picto upgrade system),允许玩家“在使用物品投入战斗的过程中进化和强化它们”,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念:即便是装备,其“本质”和效用也是通过使用和玩家的选择而被赋予和提升的。
三、 反抗的意义:向死而生的远征与西西弗斯式的坚持
三、 反抗的意义:向死而生的远征与西西弗斯式的坚持
面对一个由“绘母”所支配的、充满荒谬与绝望的世界,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出路——“反抗”(révolte)。加缪认为,当人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处境的荒谬性——即人对意义的渴望与世界之无意义的永恒冲突——他不应选择逃避或屈从,而应以一种蔑视、激情和自由的态度来对抗这种荒谬。这种反抗并非指望能够彻底推翻或消灭荒谬(因为荒谬是存在的固有条件,如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而是在于以清醒的意识直面荒谬,并在这种持续的、没有终极胜利希望的抗争过程中,创造出属于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加缪在其名作《西西弗斯神话》中,将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塑造为荒谬英雄的典范。西西弗斯因触怒诸神,被判处遭受永恒的苦役:他必须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每当巨石即将到达顶峰时,又会因其自身的重量而滚落回山脚,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这看似是世间最徒劳、最绝望的惩罚。然而,加缪却认为,“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快乐的”。因为西西弗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命运的荒谬与徒劳,他在每一次推石上山的过程中,都以其全部的激情和努力投入其中,他的意识充满了他的行动。正是这种对命运的清醒认知和在苦役中的不屈坚持,使他超越了单纯的苦难,并在这种与荒谬的对抗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意义。他的反抗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本身。
《光与影:33号远征军》的行动,正是这种加缪式反抗精神的生动写照。他们深知,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无数支远征队踏上了同样的征途,试图挑战“绘母”,但“成功率一直为0%,所有先前的远征队都未能阻止绘母,甚至未能返回家园”。尽管如此,33号远征军的成员们依然选择继承这看似注定失败的使命,踏上前往绘母所在之处的征程。他们的目标——杀死绘母,拯救人类——就如同西西弗斯面前那块不断滚落的巨石,是一个看似永远无法达成的宏愿。然而,他们的价值,恰恰不在于最终是否能够成功改写人类的命运,而在于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行动本身。这种行动展现了人类在绝境中的尊严、自由意志以及对生命最本真的热爱与眷恋。
游戏叙事中所蕴含的“紧迫感”(urgency)——源于“绘母”逐年逼近的死亡倒计时以及远征任务本身时间的有限性——如同一个催化剂,不断强化着这种反抗的真实性与力度。这种紧迫感剥离了生活中所有肤浅的顾虑和虚假的慰藉,迫使角色(以及通过角色体验游戏的玩家)直面生存的核心危机,无法长时间沉溺于麻木或自欺。在如此高风险、时间紧迫的境遇下,每一个选择都变得异常沉重而关键,而加入远征这一反抗行动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在步步紧逼的虚无面前,对自身价值与信念的更自觉、更深刻的肯定。这与一种从容不迫、允许角色有更多机会陷入“坏信仰”或逃避的叙事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处的紧迫性反而尖锐化了存在主义的困境,并激发了更纯粹的反抗。
在这种“向死而生”的行动中,生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使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且终将逝去,但通过反抗,他们超越了纯粹的生物性存在,在精神层面实现了某种不朽。游戏中所提及的“希望”,或许并非指向一个必然会到来的、彻底战胜“绘母”的完美结局,而更多的是指向反抗行动本身所蕴含的价值的希望,以及为后人留下宝贵“遗产”(legacy)的希望。正如评论所指出的,角色们“在毁灭的阴影下通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找到意义……被一种希望所驱动,即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的行动至少能为后代提供一个基础”。这种希望“并非天真或凯旋式的,而是谨慎的、饱受摧残的、不完整的。但它依然存在”。
如果说“绘母”代表着一种抹除一切意义的荒谬力量,那么《光与影:33号远征军》对艺术(如“美好年代”的背景设定,绘画本身的主题,以及音乐的重要性)和记忆(提及“《光与影》不仅被死亡所困扰,也被记忆所困扰……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形式”)的强调,则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特定的加缪式反抗。创造艺术、传承记忆,这些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意义被剥夺、存在被遗忘的有力抗议。艺术创作帮助人们“接受并应对死亡”,而铭记过去则是“尊重,而尊重则反抗了意义的抹除”。因此,在游戏中体验和欣赏艺术,(隐喻性地)参与艺术创作(游戏本身即为一件艺术品),以及努力保存和传承记忆,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心理慰藉,而是对人类价值和意义的积极肯定,是在一个被荒谬的、不断抹除一切的“绘母”所威胁的世界中,对人之为人的尊严的坚守。这与加缪关于即便在无意义的宇宙中,也要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来寻找尊严和意义的思想高度契合。游戏本身作为一幅“消逝生命的画布”,其存在也成为了一种元层面的反抗。
四、 自由的代价与模棱两可的伦理:光影中的道德抉择
四、 自由的代价与模棱两可的伦理:光影中的道德抉择
当个体在荒谬的世界中以自由选择和反抗行动来定义自身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复杂的道德困境。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模棱两可的伦理》(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ïté)中,为我们理解这种困境提供了深刻的洞察。波伏娃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模棱两可”性(ambiguity):我们既是能够自由选择、创造价值的主体,又受制于构成我们具体处境的“事实性”(facticity)——如我们的身体、历史、社会环境等——从而也是客体;我们既拥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又是终将逝去的有死肉身。人类的自由并非在真空中实现,而是在这种种矛盾和限制之中展开。
在这种根本性的“模棱两可”之中,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并通过这些选择来创造价值。波伏娃指出,不存在先验的、绝对的善恶标准或道德律令,价值是在人的激情和行动中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伦理判断往往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光与影:33号远征军》的标题“Clair Obscur”(光与影)及其核心的视觉美学风格,与波伏娃的“模棱两可”概念形成了巧妙的呼应。艺术中的“光影对照法”通过光明与黑暗的交错、清晰与模糊的并存,来营造深度和氛围。在游戏中,这种光与影的运用,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呈现,更象征着角色内心的挣扎、道德选择的复杂性,以及世界本身那种善恶难辨、真相往往被部分遮蔽的本质。正如开发者所言,这种美学“反映了一种信念,即真理从未完全揭示,而是始终部分隐藏,只有通过揭示与隐藏的微妙相互作用才能感知”。这恰恰呼应了波伏娃对人类境况和伦理判断复杂性的认知。
远征军的成员们在极端严酷的“境遇”下,必然会面临诸多艰难的道德困境和抉择。游戏据称“探讨了生存、信任以及做出艰难选择的代价等主题”,并且充满了“有意义的选择和利害关系”。这些选择往往沒有完美的、能令各方都满意的答案,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牺牲在所难免。这正是伦理在其“模棱两可”状态下的真实体现——在没有绝对指南的情况下,个体必须在具体的、充满矛盾的情境中,运用其自由意志做出判断和行动,并承担其后果。
波伏娃伦理学思想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是:“意愿自己自由,同时也要意愿他人自由”(To will oneself free is also to will others free)。她认为,个体的自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他人的自由紧密相连、相互依存。压迫他人、否认他人的自由,不仅是对他人的伤害,也是对自身自由的损害,因为它破坏了人类共同存在的基础。真正的自由,必然包含着对他人主体性和自由的承认与尊重。
从这个角度审视33号远征军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其深刻的伦理意涵。他们选择为拯救全人类的未来而战,这一宏大的目标本身就蕴含了对“他人自由”——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代的自由——的深切关怀。游戏对“遗产”以及“为后代而战”的主题的强调,进一步呼应了这种超越个体自身利益、关怀他者福祉的伦理维度。在远征的队伍内部,角色之间(如古斯塔夫、希尔、露恩等)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在互动中处理分歧、建立信任、共同面对危机,也为我们展现了在具体情境中,个体是如何在追求自身目标的同时,承认或否认同伴的自由与主体性的。
远征的整个过程,如同一个严酷的试验场,考验着每一个成员能否实现波伏娃所说的“真正的自由”(genuine freedom)。在巨大的压力和诱惑面前,一些角色可能会退回到各种形式的“坏信仰”或对自由的误用之中。例如,可能会出现因屡遭挫败而陷入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者”(nihilist),只顾行动本身的刺激而罔顾他人的“冒险家”(adventurer),或是为了达成目标而不择手段、将同伴视为工具的“激情者”(passionate man)。要达到“真正的自由”,远征军队员们必须在坚持个人信念和投身集体事业的同时,始终保持对同伴自由的尊重,并致力于一个共同的解放目标。游戏叙事中对“信任”的探讨,以及角色们“通过在篝火旁交谈和深入了解他们的背景故事,逐渐揭示每个人是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的”这些细节,都为探索这些复杂的伦理立场以及角色们在通往或偏离“真正自由”道路上的挣扎提供了可能。
此外,游戏独特的“美好年代”背景设定,以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潜在的衰败气息,构成了角色们所处“事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既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资源(如艺术的慰藉、知识的传承,或许还有一丝残存的理想主义光辉),也施加了种种限制(如文明衰落的阴影、已然破碎的社会规范)。角色们所做的每一个伦理抉择,例如在危机中优先保护什么、愿意牺牲什么、如何定义希望和未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并被这个既辉煌又腐朽的文化母体所塑造。卢米埃城的光芒,“持续被阴影所穿越,被一种对失落的敏锐意识所削弱”,这使得他们面临的道德抉择更添一层悲剧性的模糊色彩。
五、 结论:在废墟之上,艺术、记忆与未竟的希望
五、 结论:在废墟之上,艺术、记忆与未竟的希望
通过以上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光与影:33号远征军》这部角色扮演游戏,在其核心设定(如“绘母”的无情诅咒)、人物塑造(如远征军队员的自由选择与悲壮反抗)、独特的美学风格(如“光与影”的辩证运用)以及深刻的叙事主题(如死亡的逼近、遗产的传承、希望的坚守)等多个层面,均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加缪、波伏娃等人的核心思想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共鸣。游戏成功地将关于存在的荒谬性、个体自由的重负、选择的责任、反抗的意义以及人类境况的根本性模棱两可等重大哲学命题,融入到一个引人入胜的幻想叙事之中。
《光与影:33号远征军》作为一款当代的角色扮演游戏,其成就不仅在于其精良的制作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更在于它勇敢地承担起探讨人类终极关怀、激发玩家进行哲学思考的使命。游戏通过其互动性,允许玩家在一定程度上体验角色所面临的困境和抉择(如游戏中提及的“有意义的选择” 和玩家能动性),从而使存在主义的议题不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成为一种可被代入和感受的“生存实验”。正如一篇评论所言:“《光与影》独树一帜。它邀请玩家想象一种不同的英雄主义:一种并非植根于命运,而是植根于关怀的英雄主义”。
在这样一个被“绘母”无情刻写着灭亡命运的世界里,当一切外在的宏大叙事都趋向崩塌,当传统的意义体系都显得苍白无力之时,艺术的创造、记忆的传承,以及那份在评论中所描述的“谨慎的、饱受摧残的、不完整的但依旧存续的希望”,便成为了人类对抗虚无、肯定生命价值的最后堡垒。游戏本身作为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对意义的艰难建构之中。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最深沉的黑暗中,人性的光辉依然可以通过创造、铭记和不屈的希望而得以延续。
有评论将这款游戏标记为带有“后虚无主义”(post-nihilism)色彩的作品,这提示我们,尽管《光与影:33号远征军》深刻地触及了存在主义思想中固有的虚无主义潜能(如荒谬感、意义的缺失等,以及波伏娃笔下因“严肃性”破灭而可能产生的“虚无主义者”),但它最终的旨归似乎并非停滞于此。相反,它试图引领我们超越这种虚无,不是通过否认黑暗的存在,而是在直面黑暗之后,通过具体的、人性的行动——如关怀、传承、以及那份在绝望中淬炼出的坚韧希望——在废墟之上重新寻找和建立意义。正如评论所言:“在《光与影:33号远征军》中,角色们并不执着于宇宙的承诺或天定的命运;他们在毁灭的阴影下,通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找到意义。”并且,“通过拒绝轻易的宣泄,《光与影》赢得了它的希望”。这正体现了一种成熟的存在主义姿态:在承认存在的虚空之后,依然选择积极地投入生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文化的创造和对未来的责任感,来赋予生命以价值。
最后,《光与影:33号远征军》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引人深思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被“绘母”无情宣判的世界里,真正的“拯救”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孤注一掷地试图杀死“绘母”,彻底改变既定的命运?还是说,在必将到来的毁灭面前,更重要的是保有作为人的尊严与自由,以不屈的姿态活过赋予我们的一切,并为后来者留下反抗的火种与不灭的记忆?这或许正是《光与影:33号远征军》抛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存在主义之问”,一个在光影交织的末世图景中,久久回荡的关于人类境况的追问。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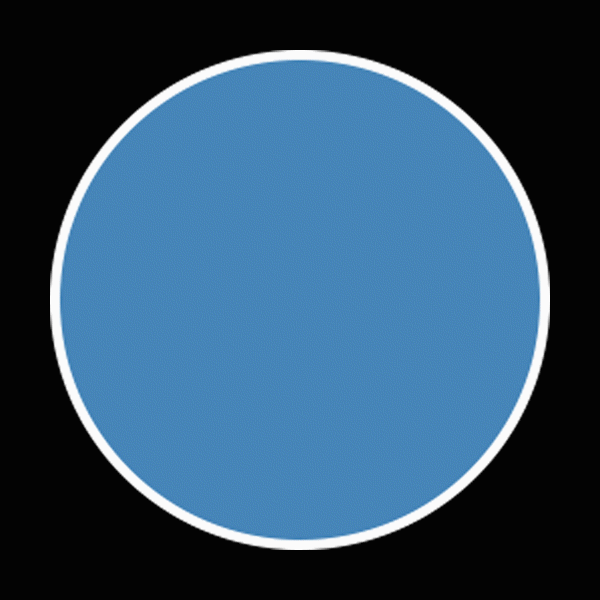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4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