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丁旦
编辑:柏亚舟
《忍者龙剑传4》如期发售。曾经被誉为“三大动作游戏”、定义了高速砍杀玩法的老IP有望在沉寂十三年后再获新生,而它的最初创造者板垣伴信,却在游戏面世的5天前离开了人间。
坑坑洼洼的面庞、总不离脸的墨镜和桀骜不驯的表情,让他被玩家们惯称为“硫酸脸”,除了摇滚明星或黑道组长般的外观,在世时,板垣伴信的公众印象同样总是伴随着狂妄、毒舌、锋芒毕露,但在托他人代发的遗言里,板垣伴信却流露出少见的自省与温情:
我生命的灯火,即将熄灭。
这篇文章的发布,意味着那一天终于到来,我已不在人世。
我的人生,是一场接连不断的战斗,我始终在胜利。
但我也给许多人添了麻烦。
我自认始终遵循着信念,战斗到底。
毫无遗憾。
唯独对粉丝们,无法再为各位送上新作了,这让我满怀歉意。
世事如此。
So it goes.
《死或生1-4》和《忍者龙剑传1-2》与板垣伴信的名字深深绑定,它们各自在格斗和动作两大历史悠久的门类中闪耀,也启蒙了无数开发者和玩家。自2010年离职组建新工作室至今,板垣伴信只推出过一部销量暴死的《恶魔三全音》,该作融合近战、枪战和多人对战,却并未得到市场广泛接纳。今后,全球玩家的确再也不会再看到这位个性制作人的新作。
大约十年前,板垣伴信最后一次聊起“特别希望制作的游戏”,说自己想做《铳梦》。当时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的《阿丽塔:战斗天使》尚未开拍,板垣伴信的发言依然带着浓郁的个人风格:“一旦我们公司在加拿大上市,我就会再次拜访卡梅隆。我很喜欢《铳梦》,也只有我们团队有能力做,难道你不这么觉得?”
板垣伴信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日本一批知名制作人都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他的悼念,包括原田胜宏(《铁拳》)、神谷英树(《鬼泣》)、樱井政博(《任天堂全明星大乱斗》)等。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前原田胜宏和神谷英树都曾因板垣伴信出言不逊,和他打过绵绵不休的隔空嘴仗。
原田胜宏和板垣伴信如果说“真正的死亡是被人遗忘”,板垣伴信在多年无作品的情况下,离开得起码不算悄无声息。而“明星制作人”,本身就是种独属日本游戏界的现象,人们耳熟能详的基本都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如今除少数特例仍活跃于一线(如生于1963年的小岛秀夫和相对年轻的生于1974年的宫崎英高),其他如三上真司、坂口博信、五十岚孝司、名越稔洋等等,或许不得不承认都已经过了创作黄金期。
板垣伴信的逝世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噩耗。日本的一代明星制作人和会诞生出明星制作人的时代,则似乎在和玩家们进行着漫长无声的告别。
“狂人”出走,独饮失败
“狂人”出走,独饮失败
板垣伴信“打工生涯”的顶点,是TECMO旗下Team NINJA的组长,2008年他高调离职,离职时不忘“大放厥词”。
对接替他位置,日后主导开发过《仁王》《浪人崛起》的早矢仕洋介,其评价是:“那只是我新收的小弟。作为小弟我认为他表现不错,希望其他公司的动作游戏制作人别被我的小弟干掉了。”对于自己的日后规划,板垣伴信则云淡风轻:“我的主业是摄影,游戏开发只是兴趣。”
“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背后动因,是职场并不罕见的上下级矛盾。担任组长期间,他就经常拿着辞职信要挟上司给团队更长开发周期,但TECMO新上任的社长不再吃他这套,面对他索要被拖欠的奖金的诉求,新社长态度强硬:要么辞职要么起诉。
板垣伴信转手就把老东家告上法庭,索要1亿4800万日元,TECMO不等他主动离职就给出一纸辞退函,板垣伴信再以非法解雇为由,又追加了1600万日元诉讼金。官司还没开打,TECMO股价几近腰斩,该事件也成为TECMO寻求卖身的导火索之一。
在起诉仅4个月后,TECMO便与光荣公司合并,重组成现在为人熟知的光荣特库摩,随着社长下台,板垣伴信也不再声讨公司。两年后,官司以庭外和解的形式告终,板垣伴信则宣布成立“英灵殿工作室”,核心成员是他从Team NINJA一并带走的20多名旧部。
有粉丝问过他为什么起名英灵殿(Valhalla),他套用北欧神话答:“我们就像在职场的战斗中倒下后,被女武神选中的战士们,这家公司就是我们的英灵殿,我们在这里重新开始。”不过这帮战士显然没选择从哪跌倒在哪爬起——第一个项目既不是格斗也不是动作游戏。板垣伴信的理由是:“让你回大学去重修你愿意吗?做新东西有意思多了。”
可惜板垣伴信离职创业的时机相当糟糕,彼时处于PS3/Xbox360世代末期,日本匠人、作坊式的制作风格在欧美工业化的大作面前溃不成军。“英灵殿”也不像神话里那般是个永远辉煌永恒不变的终极归处,反倒命途多舛。
板垣伴信原本像不少单飞的制作人一样,找到了微软这样的巨擘作为发行靠山,但又因微软想要主推体感设备Kinect,《恶魔三全音》却不支持,双方合作告吹。微软引介THQ作为新发行商,板垣伴信和THQ高管也很投缘,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为“什么叫独特的游戏”来回争辩四轮才坐下谈成合作,结果没过两年THQ就宣告破产。
某年E3,有记者问是否考虑让《恶魔三全音》登陆任天堂的新主机Will U,板垣伴信斩钉截铁:“我都懒得体验那设备。我的游戏可是很暴力的,Will U的用户群能扩展到什么程度?硬件方面我也没看出哪适配,在Will U上玩?说不定手柄都要搓坏三四个。”可偏偏,在又经过韩国一家网游公司转手后,最终《恶魔三全音》只能由任天堂发行,还成了Will U的独占游戏。
开发再不顺利,板垣伴信嘴上绝不认输。被质疑开发进度时,他会反呛:“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些无聊游戏你又认为有百分之几的完成度?”同时,他对自己离开后,TECMO继续开发的《死或生》和《忍者龙剑传》也颇有微辞,他将《忍龙3:刀锋边缘》的成功总结为“回归本源”,至于《死或生》则是“完全乱套”。
《死或生5》就不太符合他上手容易精通难、操作简洁但动作丰富的理念,新手和老手间的技术差距太大,不再能够“第一次玩就算乱按也能打出视觉效果很棒的招式”。板垣伴信认为,为了弥补对新用户的吸引力,TECMO才想要凸显出色情要素,但在过去,他分明是为了让系列正传维持硬核格斗的调性,才单开了一条子产品线《死或生:沙滩排球》来满足休闲玩家的需要。“(正传)用色情DLC榨干核心玩家的钱包——恶心!”
《恶魔三全音》开发八年且团队稳定,板垣伴信将此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尽管游戏2015年上线后,首周销量不到1000份,差评也如潮水,还尤其不受欧美媒体待见,Gamespot只给3分,一向宽容的IGN都只打了3.5分。
板垣伴信却认为,任天堂北美分部的发行不利是主要原因之一,让评测人员们只玩单人剧情却没体会在线模式的精髓,由此给出的评测“占整体差评95%,没有任何价值”。媒体的态度似乎也从来不影响他,反正《死或生》推出时,日媒也曾称其为“死或死”,《忍者龙剑传》研发代号是“Kunai”(武器名),批评者称之为“Yarita-Kunai”(我不想玩),“我是为了粉丝们做游戏,又不为媒体做游戏。”
但经此大败,亦可能只是单纯的年岁老去,板垣伴信的确有了隐居幕后的倾向,不再会表露游戏制作的雄心,就连公众形象相较过去都更柔和。
他曾登上《人民日报海外版》,还颇为反差地在采访活动的签名板上,写了中国思想家庄子的主张“无用之用”,报道描述他“这位印象中满嘴炸药包的游戏人也有儒雅睿智的另一面”。
他还为国产手游《战舰世界》站台,成为后者的高级顾问,说着国内玩家很熟悉的病毒式广告语“男人玩的游戏就必须要硬派”。同年,他也辞去英灵殿工作室的董事职务,退居顾问。
Xbox20周年时,彭博社以专题策划名义询问板垣伴信的近况,他表示自己过去几年都转而培养年轻人。那时他才刚成立新公司“板垣伴信工作室”,但对微软甚至表现出了几分希望被收购的示好意图:“过去二十年和Xbox的合作非常好非常舒服。如果他们主动联系我(成为微软旗下工作室),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
在《Fami通》的系列栏目中,板垣伴信相继主动选择了曾被炒得有过节的原田胜宏(《铁拳》系列)和小林裕幸(《鬼泣4》),谈话也被冠以“奇迹的对谈”、“禁忌的对谈”来宣传,但双方都在说清原委后“一笑泯恩仇”。板垣伴信还回忆道:“我们这些做游戏的,喝了酒就是业界好伙伴,聊得特别痛快。”
一边喝酒一边做经典
一边喝酒一边做经典
进入游戏行业前,板垣伴信在早稻田大学读法律,耗了七年才修满学分毕业,去TECMO面试时,他坦承是因为“花太多时间打麻将了”。
戴墨镜就是他大学时养成的习惯,声称“能避免在赌桌上被对手看穿表情”,而他选择公司也很随性,就算对世嘉的游戏更了解,板垣伴信也会因“离家只有一站电车的距离”而加入TECMO。
在他的回忆中,90年代初的日本因为刚经历泡沫经济破灭,整个社会一片黯然,时不时就能听见抱怨和叹息。刚入职第二年,当时的社长就把他叫过去苦笑着说,“你知道连续亏损三年意味着什么吗?”板垣说“不清楚”,社长说“意味着公司要完蛋了”。
随后社长下达了“要么做款赛车游戏,要么做款格斗游戏,打败世嘉”的目标,临危受命的板垣一想赛车游戏对街机框体要求高,有库存积压就麻烦了,于是选了格斗。他只花了两天,就完成了最初名为《忍者格斗》的企划,后来为体现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干脆改名“死或生”。
对初代《死或生》的8名可操控角色,板垣伴信倾注大量心血,他不止专注于格斗游戏中最重要的角色招式,还会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打磨每名角色的外形、性格、背景故事、成长轨迹等等,这种“对孩子般的爱”也延续到每款续作里。
《死或生》初代只有3名女性角色,如果只拿情色内容当卖点显然说不通,游戏的成功更多还是凭扎实的手感与对战的深度。这款游戏的确拯救了TECMO,发售那年,在同期有《VR战士3》和《铁拳3》前后夹攻的市场缝隙里,TECMO从上年亏损4.9亿日元转为盈利9.7亿日元。
虽然,后来板垣伴信自己也会调侃,“《铁拳》有历史积淀和玩家基础,《VR战士》有‘格斗游戏开创者’的优势,我们《死或生》有什么?有胸部。”
不过在他掌控系列的十年间,他一直努力在“四个支柱”之间求平衡,“四支柱”分别是互为对立的“休闲向”和“专业向”,“性感元素”和“暴力元素”——“太难会吓跑新手,太简单会流失核心玩家,太暴力不行,性感过度会沦为色情游戏,要确保没有任何一项盖过其他三项”。而按他的高标准,《死或生4》才算真正迈入顶级格斗游戏的行列。
当然,这一点不妨碍“让乳摇系统发扬光大”经常被玩家们看成板垣伴信对游戏界的最大贡献。就连《死或生》的死对头《铁拳》——一个早年禁止“乳摇”,被板垣喷成“我最讨厌的5个游戏是《铁拳》12345”的系列,都从5代开始加入乳摇系统,还让制作人原田胜宏感叹“可能板垣只是早就加入了最终我们都会采纳的功能”。
除了打麻将,板垣伴信的另一大爱好是喝酒,他曾理直气壮地说:“喝酒是工作吧?打麻将是工作吧?本来工作就和玩差不多。”
在TECMO任职期间,板垣也经常带着下属们下班后去居酒屋放松,边喝边聊企划,以至他甚至宣称,他担纲导演的游戏,只有一半的创意出自清醒的大脑,另一半来自酒桌。这可能也导致了,板垣伴信的游戏“从来没有一次能完全按企划书来,开发过程中总会忍不住修改或添加内容”。
如果只是名“格斗游戏导演”,板垣伴信多半不会有日后的江湖地位。在《死或生3》开发期间,他就开始筹备《忍者龙剑传》,2004年游戏发售惊艳世人,评论界普遍称赞游戏华丽、精确且爽快的动作,以及伴随着正反馈的高难度。
不久后在板垣伴信的坚持下,TECMO相继推出两个免费的DLC,并被整合进加强版《忍者龙剑传:黑之章》,也就从《黑之章》起,系列有了被津津乐道多年的“超忍”难度和最低难度——“忍犬”。
续作《忍者龙剑传2》则新增了断肢和终结技系统,但当被和同样暴力恣肆的《真人快打》对比时,板垣嗤之以鼻,他表示前者繁琐的终结技是为了羞辱,忍龙的终结技则是为了让敌人死得更痛快。“大卸八块或是砍得鲜血淋漓根本不算真正的暴力,像旧日本武士那样,把对手的手指砍去四根,逼得他因为再也拿不了剑只能自杀才是。”他曾一边挥舞办公室里的武士刀一边向英国记者演示。
跨入动作游戏领域后,板垣伴信也和同行们“结过梁子”。《忍者龙剑传2》宣发期,早已离职的“鬼泣之父”神谷英树正在开发《猎天使魔女》,有意无意贬低了《忍龙》,板垣立马回怼:“神谷英树的《大神》我女儿都玩不下去。他是不是还说过动作游戏自打《鬼泣1》以来八年没进步?难道他是睡了八年没醒?”
恰巧小林裕幸负责的《鬼泣4》和《忍龙2》同期宣发,板垣也是频频开炮,诸如“我都没听过小林这名字”、“《鬼泣4》我试玩了,战斗平淡又单调”、“这么烂的游戏还敢拿上台面”等言论层出不穷。
然而,多年后和小林裕幸对谈时,两人却一同怀念起了他们心目中那个,“西有卡普空东有特库摩”,“各自用心做作品,在同样的类型领域里切磋竞争,共同拉动行业热度的时代”。
明星制作人的黄昏
明星制作人的黄昏
板垣伴信所怀念的良性竞争与热闹繁荣,前提便是制作人和游戏监督对作品有绝对话语权,公司和媒体也看重他们的个人影响力。那个时代显然是一去不返了。
那批明星制作人大多都和板垣伴信成名于同一年代,这背后自然有特定历史因素。上世纪90年代,正值电子游戏从2D向3D转型的时期,有大批让人眼前一亮的新IP诞生,媒体们又习惯以“XX之父”来追捧核心主创,本质上就是借鉴娱乐圈的偶像引流做法,在游戏圈也进行“造星运动”。
其实同时期的欧美,开创3DFPS游戏的卡马克、罗梅罗等制作人同样名声煊赫,但明星制作人逐渐就变成了日本游戏界的专属现象,则是在日本的社会和创作特征下所形成。
一方面泡沫经济时代刚刚破灭,许多日厂都步履维艰,于是常见“新人接下重任,挽救公司,从此地位陡升”的故事,而日本职场的传统是实行年功序列制,跳槽率低,游戏公司也乐于把主创推到台前。捧红一位制作人后,同IP的续作只要有他站台就可以实现一定粉丝效应,不管他对游戏实际参与多少都有利销量。当然,这也是为何后来日厂明星制作人的离职总会闹得沸沸扬扬。
另一方面,日本游戏工作室的管理结构趋向“直线型”,位于顶点的制作人权力很大(且“明星制作人”一般兼任“游戏监督”,相当于电影业的导演),不像欧美工作室通常用“矩阵型”,程序、美术、创意等部门各司其职,制作人更侧重协调工作和项目管理(相当于电影业的监制)。当时的“大作”可能就只需要十几个人完成,所以制作人非常容易在游戏里展现个人品味,给作品打上自己的专属烙印,继而吸引同频的玩家。
几重因素下,板垣伴信简直又是明星制作人的最佳模板,他的游戏总沾染暴力、色情等直给的、讨论度高的特色,自身的外貌和发言还极富辨识度,想不成为游戏界的“明星”都难。
但随着欧美游戏业强势崛起,工业化浪潮碾过,“车枪球”玩法的销量能盖过日厂那些慢工出细活的角色、剧情、迷宫、招式等等,全球游戏界“西升东落”,日本自然也就丧失了造星能力。
转变的起点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微软在日本屡次展开收购行动,在频频受挫后,终于决定以自己做主机、做开发的方式介入游戏界。板垣伴信还是最早支持的制作人之一,他曾表示Xbox的机能比PS2强4-6倍,于是将《死或生》和《忍者龙剑传》的新作都带上了Xbox平台。
PS2世代基本也就是日本游戏业最后的辉煌,当Xbox用上欧美PC程序员们更熟悉的X86架构,索尼和任天堂也妥协后,日厂就开始在技术层面全面落后。起初还有一些厂商能靠日本本土市场活得比较滋润,但到2010年,日本在全球游戏市场的份额已经跌到10%以下。
既然转为面向全球开发游戏不可避免,那自然也要学习欧美的工作室制度,加大资金和人员投入。几百人规模的大团队就必须做更多综合考量,旨在凸显个性的“明星制作人”也就成了无根之木。
一边是开发模式的变化,另一边则是市场对“大作”的要求也在变化,这很可能导致了大多数明星制作人从母公司脱离后,都再拿不出符合自己曾经名望的作品。比如三上真司的《幽灵线:东京》,“寂静岭之父”外山圭一郎的《野狗子》表现都差强人意,名越稔洋被网易“挖角”已逾三年,更是连个“新建文件夹”都没掏出来。
当然理性来说,游戏开发从来也不只是制作人的功劳。强如宫崎英高,《只狼》的战斗系统出自公司的战斗设计师山村胜;《忍者龙剑传》里板垣伴信主要把关敌人和场景,主角的形象和招式由另一位监督松井宏明负责。现代大型游戏从来都是集体创意和努力的结晶,“造神”或者“毁神”本就都无必要。
日本的明星制作人们如今多数黯淡固然令人感叹,但从市场多样性的角度看未必是件坏事——既在技术实力和开发规模上跟上节奏,也不丢失自身特色、尝试分庭抗礼,可能是日厂们在如今时代最好的平衡点。《勇者斗恶龙9》的制作人日野晃博就曾说:“日本现在离过去那种世界游戏中心的感觉相距甚远,但创造独特的日本风格才是真正吸引人心的地方。”
更何况,即便已至黄昏,黄昏也可以是一天中最绚烂的时刻。还能关注一些“老家伙”们的新动向,看到被冠以某明星制作人名字的作品就依然可以从心里涌起期待,或许就是这场漫长告别里所留存的,一种物哀式的浪漫了。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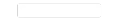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5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