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o引言:当我们在看赛博朋克相关作品时,我们究竟在看什么?赛博朋克的内涵?边缘行者们的反抗?还是仅仅关注其美学?借着《边缘行者2》的即将上线,说一下在下对于赛博朋克的理解吧,希望足够易懂和深刻。
一、什么是赛博朋克
一、什么是赛博朋克
在讨论一个概念之前,总归要先下个定义。
赛博朋克(cyberpunk),它是控制论(cybernetic)与朋克(punk)(说实话个人更喜欢‘叛客’这个翻译)的合成词。为此我们需要对二者进行一定的解释。
控制论:1948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bert wienerr 1894-1964)为自己的一本新著起名为《cybernetic》(即控制论),词名来源是希腊语“κυβερνήτης”(kybernētēs,意为“舵手”),书的副标题为“关于动物与机器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
控制论并非狭隘的工科技术,而是能运用于任何系统中的一般控制理论。我们不是学者,不用了解得过于深入,只要知道,它研究的是动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与反馈即可。其常与控制、反馈、信息等概念高度相关。
我们需要认识一点,控制论不需要了解研究对象的原理,只要反馈本身,即输入与输出。如果人与机器反馈过程近似,会怎么样?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如果实在好奇得紧,请跳转到第三章第一节中的第二个部分,即赛博格)
朋克:相较而言,朋克就好理解很多,一开始是20世纪七十年代的一种摇滚乐,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文化符号(这里很关键哦)。在赛博朋克作品中,它们往往表现得极端、碎片化、消极,但同时,它们也在反抗,哪怕不知结果。
朋克是赛博朋克的真正核心,对自由的追求与对异化秩序的反叛,骨子里是绝无出路的虚无。
综上所述,想来我们对赛博朋克有了一定的了解,也不难看出赛博朋克这个词本身,就将控制与反抗相结合,它是一个融合了矛盾与冲突的词汇。
二、赛博朋克的大致背景
二、赛博朋克的大致背景
提到赛博朋克,我们会想到什么?
通常来说,赛博朋克的故事往往是发生在较为接近的未来(其实早期很多是在外太空的,不过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几乎固定在地球了),高科技低生活,极致的垄断,极端的阶级固化......
其背景常是殖民地或近似的存在:阴雨连绵不绝,湿润的地面反映着暧昧的灯光,全息广告与霓虹灯牌挤作一团;与此同时,城市拐角,浑浊的水雾弥漫于东亚风的小巷,湿润粘稠的地面映着暧昧的灯光,各类非法或半非法的店铺堆积在一起——这种反差纷乱的场景构成了我们对赛博朋克世界的第一印象(文笔有限,姑且一看)。
这些城市一般都处在一个交汇改变的状态——极端落后的非现代的世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其中的冲突往往是故事的开端。
当然,也有其他的已经彻底完成改造的,但毕竟总会有遗漏的角落,所以大差不差。
三、赛博朋克中的异化
三、赛博朋克中的异化
这可以说是有关赛博朋克讨论中最重要的部分了,自然要分成几点细细阐述(当然,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谈到赛博朋克,还是讨论美学比较多,甚至只要是带霓虹灯带点机械就可以说是赛博朋克,这就是后现代啊(大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挺赛博朋克的)。
1、人的异化
科技发展到奇点,秩序失衡,人类也因此失格。
(1)四重异化
这里就用马克思的四重异化以及自己的一捏捏理解来开篇吧,不一定正确,还是姑且看个乐子。
其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
起初,人们劳动获得产品只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但在资本介入后,资本用金钱来购买你的产品,你可以用所得去购买其他产品,但你无法享用你原有的产出,甚至于你产出的越多,与你劳动相对应的所得越少,你反而被劳动产品反向掌控。劳动产品异化为商品,同时转为了压迫劳动者自身的力量。(譬如说,你在赛博朋克的工厂中生产高端义体,但你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当然,那时候真的还有人力工厂吗?笑死)
其二: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
劳动产物的异化转而让劳动本身被异化,人们劳动从为了满足自身变成了为了满足自身——原本的劳动是满足自我的途径,同时也可以满足自身的基础需求;异化的劳动只是目的,为了获得金钱以满足劳动外的动物性的需要,劳动本身是痛苦的。
劳动成为了一种折磨,但人却不可能离开这种异化的劳动。(公司狗固然是当狗,但狗都当不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惨)
其三: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在劳动本身被异化后,与劳动密不可分的人类自然也逃不过被异化的结果。
人类被降格成了动物般的生存工具——在本应该属于人实现自我的劳动中无法获得应有的满足,转而在劳动外的动物性行为(例如吃喝性居住装饰等等)中才能获得满足(即马斯洛需要层次中的最底一层)。
我不再思考明天何时到来,我只祈祷今夜再漫长一些。
其四:人同人相异化
在劳动产品异化、劳动本身异化、人自身异化之后,人和人的关系还会正常维系吗?
首先,被异化后,人在这个世界的定位是?他们无法在这个世界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成为了无力的受支配的存在,人与人自身的本质对立。
其次,异化后的劳动成为了金钱的衡量物,人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这直白的衡量方式,让人与人之间直接比较,同时为了赚更多的钱,需要去争去抢,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甚至于敌视。
再次,人的劳动被异化了,那异化劳动的人呢?不细述,总之人与这批群体所对立(他们同时也是被异化囚于其中的)。
(2)赛博格——人与机器与工具的属性模糊
前面说过,控制论只需要反馈本身,如果人和机器的反馈近似,会怎么样?答案是,生命系统与机械系统并不做区分,只要有近似的反馈过程就做统一处理,这在学术上当然没什么问题,那在赛博朋克这种幻想世界观下呢?
赛博格(cyborg),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Organism)的缩写,它自然有很多含义,这里只谈在下自己的理解。
正如前面的四重异化所言,人被异化成了工具,为了工作,为了追赶所谓时代的脚步,人类必须改造自己,植入各类生产型义体,装载脑机芯片,根据算法调度争分夺秒行动——人与机器的界限愈发模糊,又或者,在那个科技足够发达的世界,人和机器有何区别?
你该如何分辨激荡出的热烈情感是来源于大脑还是集成电路?人难以在这样的世界保有温情,机器在很多时候却有充满善意。感性的世界被技术蹂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很绝望吧。
正如现在爆火的ai,它们往往能给予你其他人难以给予的情绪价值,真邪?假邪?如果不想要陷入无端的内耗,那就不分辨了吧,哪怕世界是虚假的,但痛苦是真实的,感受到的爱也是真实的。(说起来,不是有个段子,在ai出来之前幻想ai替代自己工作,然后自己去写诗画画,结果ai出来以后,自己还是在工作,ai却在写诗画画,这也是一种人和机器关系的错位吧)
(3)底层与无用阶级
前面提到了四重异化,那如果连被异化的劳动都无法参与的人呢?这里多少有点恐怖而不可名状了。它们不值得专门去剥削。
足够发达的ai与机器自动化等等使得上层完全可以脱离人力生产,总的来说,赛博朋克世界中的底层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它们无法参与生产(因自动化取代人力)、也无法成为有效消费者(因消费能力缺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甚至是被赡养着的,有吃有喝(营养膏也吃不死人对吧)有时候还能有点娱乐(廉价的vr设备、drug,活泼些的,说不准还能在巷子里留下些尿渍似的涂鸦),它们活着,也仅仅只是活着。
可悲的是,对有“上进心”的底层而言想要成为可以被剥削的对象拥有一丝个人价值都需要拼尽全力。改造自身,踩着其他底层上位,无论是成为公司职员还是成为黑帮,最后都只不过是一个带有湿件的机器。所有获得个人价值的可能被剥夺,还能一直存在下去的人已经不是人了,这是究极的异化,它们成为一根根被塞入碎肉的人形皮子的香肠,连人都不是了。
那它们为什么还存在?为上层提供高人一等的情绪价值?醒醒,已经有中层负责干这个了,你不会指望老爷们会去贫民窟吧。那为中层提供情绪价值?还记得前面说的吗?他们也被囚于异化之中。那为什么还存在呢?这里先提第一个想法: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直接大量地消灭底层必然会招致反抗与自身阶级内的分裂,不如将本就过剩的资源稍微漏一点出来去养着他们,给他们生存下去的能力但不给他们希望,久而久之,底层就自然在内耗中失去反抗的力量走向消亡。
底层与无用阶级的论述先暂缓些许。
2、消费的异化
(1)符号消费
在四重异化的论述中,已经提到劳动产品的异化,而在实际生产力已经非常充裕的赛博朋克世界中,产品实际上的使用价值已经不是唯一的目的,可以说其价值一定程度上反而是通过背离使用价值多少来体现,甚至于产品本身被抽离,只余其上所带的概念或者说符号本身,这便是消费主义的极致——符号消费(当然,这并非一个贬义的概念)。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浅浅举个小例子,原创圈,指一群人沉溺于花钱约稿子(貌似还不便宜)买头像并猛猛打水印,这样的消费从使人们对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需求转换为“为欲望而欲望”的需求, 从而, 过去意义上为满足需要的消费被转变为为满足消费欲望的消费, 亦即对欲望本身的消费(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反正又不是我的钱)。
在相对了解了其概念之后,我们可以知道,符号消费的价值体现在其社会象征意义与身份的差异化上,故而,赛博朋克的资本方将商品转变为符号的载体,通过符号来构造伪需求,将消费异化成对虚幻概念的追求,如“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社会象征意义)、“8848”(身份的差异化)(为防不知道的,8848是一个用料很夸张的手机,说是成功男士的选择)等等。
底层为什么还存在?因为它们并未完全脱离消费体系,它们也被纳入符号消费(潜藏消费)之中,消费的本质是对符号价值的追逐,它们努力攒钱购买盗版抑或是二手的义体,并非追求功能,而是通过仿冒符号获得接近“上层”(今个我也吃上了烤鸭,我也是老爷了)的幻觉。而在赛博空间或者VR世界中,它们购买虚拟世界的物品,通过沉溺其中来掩盖现实中的无力感。看起来好像没那么糟?前者,它们看似自由但选项早已被预设(不懂就问,能流下来的货色还能是些什么呢),后者,它们主动放弃了自己能对现实世界造成影响的认知,完成了自我规训。无用阶级的消费不再是满足需求,而是维系奴隶身份的枷锁。
你以为就此止步吗?不,要到一个关键点了。前面说了朋克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符号这个词很关键!朋克音乐、街头涂鸦或黑客技术等等,表面上是对主流的反抗,那实际上呢?我提一个词——亚文化,是不是突然理解了什么。这些所谓的反抗,早已被收编成符号的一部分,作为商品被出售,同时,其意义也在符号化中逐渐被消解。
(2)贩卖理想
相比于贩卖带有符号概念的商品,对理想的贩卖无疑是更进一步,巨企编织虚假的“理想叙事”,榨取消费能力与行动力,达成究极的异化秩序。
其一:贩卖明天。例如说将义体与芯片等等人体改造包装成诸如成为更好的自己,暗示消费者可通过此举进行阶级的跨越。
其二:贩卖身份(阶级)焦虑。例如说不断迭代义体的型号,刻意营造“过时即是落后”“用旧款阶级就要跌落”的概念;亦或是宣扬全身义体化才是精英,以求得更多主动的工具。
其三:贩卖偶像。例如说将公司里的工具人编造为底层人通过努力或者改造而成功完成阶级跨越的实例(是不是感觉和第一个重了);又或是将反抗者包装成明星!朋克也是文化符号的一部分啊。将一部分真实的出名的所谓传奇的概念转化为各种符号制造潮玩等进行销售,再自己造一些“反抗者”明星出来营销。
其四:上月球。对于这些没有意义的人来说,上月球这个行为本身难道不是公司贩卖的理想吗?它们是怎么想到上月球的?因为它们看到了上月球的广告啊!“欢迎来到月球之旅,体验在超梦里前所未见的月球引力”。何等的讽刺!
企业以贩卖理想的方式将结构性矛盾转化为个人奋斗叙事,掩盖系统性的剥削,并为其添加难以挣脱的沉没成本,完成了对人类的终极异化——不仅掠夺其劳动力和财富,更窃取其希望与反抗意志。人们自愿戴上镣铐,只因镣铐被镀上了理想的金边。
3、文化的异化
前面一直在说底层人是无用阶级,你们是不是会有疑问:那艺术呢?反正它们也不会去参与劳动,同样也饿不死,这么闲为什么没有产出艺术作品?
这里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赛博朋克世界观的文化了。这样的世界有艺术吗?无疑是有的,赛博朋克式美学从诞生起一直都是个较为独特的美学形式,深受人们的热爱。那其他的呢?有归属于底层人的吗?
朋克艺术?涂鸦?不不不,它们已被主流性收编。还有更多的吗?属于底层人的文化属性?我们惊讶地发现,居然想不到什么。
这是为什么?其实思考一下看过的相关作品,你会发现里面虽然出现了各种文化的杂糅,但多多少少都带点似是而非的意味,或者说刻板印象,你说有那些文化确实有,你说是又很难评价。它们只是一些大而空泛的文化符号(该死,怎么又是符号)。
这就是赛博朋克的文化的异化,其所处地方的文化被打碎并重新构筑,成为了处处带着影子但细看又不是的存在,这样的背景是无法让底层留有无法被收编的有冲击力的文化。它们所接触到的文化只有企业为它们展示的。
四、赛博朋克世界的存在形式
四、赛博朋克世界的存在形式
在上述的论述后我们不难发现,赛博朋克的世界观貌似不是非常稳定,甚至可以说它并不存在供需平衡。那么,它是如何较为稳定地维系自身的存在的?我愿称之为赛博朋克世界观是资本主义最后的余辉,它处在一个崩溃的进行时,所有的生机都是崩溃前的回光返照。
这里在下提供两个存在形式与其可能的崩溃的结局。
1、世界工厂
既然赛博朋克世界内部供需不平衡,那有外部世界不就好了。内部只需要不管不顾地生产,然后销售给外部——是不是有点眼熟?
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世界工厂。
极端落后的非现代化世界与现代化杂糅交汇,人可以相对简单地生存但难以说是生活,其中的生产者无法享受生产的成果,上层与下层几乎不是一个物种,阶级间的鸿沟几乎无法跨越......
如果抛开赛博朋克绚烂的外壳,它们是多么近似啊。(个人觉得2077的夜之城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模板)
2、伪平衡
既然供需无法平衡,那就直接伸出大手。巨型企业垄断技术、资源与权力,通过人为制造稀缺性、异化劳动力、操控消费欲望,构建一种表面稳定、实则畸形的“伪平衡”。这种平衡的本质是系统性的剥削与压迫,而非真正的市场自由。
(1)异化供给
生产出的高端配件服务于精英阶层,并不断升级产品,制造“过时焦虑”,迫使消费者持续消费以维持社会地位。
将一部分次品流入下级市场,同时制造人为的稀缺,迫使有“野心”的底层人不得不成为债务的奴隶。
(2)扭曲需求
企业通过虚拟现实等提供廉价的感官刺激,转移底层对现实困境的关注。真实需求(教育、医疗、社会流动性等等)被虚拟消费替代,形成“奶头乐经济”。
(2)构造默许的灰色地带
放任黑市存在,将社会矛盾转嫁至底层内斗(如夜之城的帮派战争),同时从中获取数据与实验样本(如荒坂公司利用贫民窟测试未上市的义体)
这样构建出的供需关系并非自然市场的结果,而是权力与资本合谋的产物。企业通过技术垄断与需求操控,构建了一种表面稳定、实则脆弱的伪平衡。
3、终局
(1)资源枯竭
赛博朋克世界依赖外部资源输入(如能源、原材料)与全球化剥削维持表面繁荣,但掠夺性发展终将导致资源枯竭。资源耗尽后系统将迅速崩塌。
(2)阶级矛盾的爆发
无用阶级的潜藏消费与内耗无法永远转移矛盾。当底层意识到自己时,可能爆发大规模反抗。他们具有相当的破坏力,哪怕最后被镇压,世界也变了。
(3)技术失控
技术失控(如AI反叛等)以加速社会崩溃。
(4)终产者
如题,终产者诞生,赛博朋克时代结束。
五、赛博朋克作品中的角色们
五、赛博朋克作品中的角色们
这里就没必要挨个作品介绍了,只需要找出他们的共性再举俩例子。
1、边缘人
这里强烈推荐看一下《边缘行者》,它的名字可以说是完美概括了赛博朋克相关作品中大多主角们的形象——边缘人。
边缘人是介于上层与无用阶级之间的特殊群体。他们既非秩序的维护者,也非彻底的被抛弃者;他们既是系统的反抗者,又是系统的产物(譬如说《边缘行者》里的大卫,他的军用义体来自公司,其反抗的工具本身就是压迫的象征。);他们游走于法律、技术与道德灰色地带,他们是反叛者。
他们拥有着一定的能力,迷茫,在遇到了某些事以后渴求改变,却没有改变的方向。他们的职业往往是边缘群体,譬如自由黑客、佣兵、拾荒人、帮派小子等等。边缘人们总是在不断前进,他们无法停步,停步就会去探索内心思考意义,而意义在该死的赛博朋克世界是不存在的。
2、仪式化的自我献祭与西西弗斯
在赛博朋克的世界中,边缘人的反抗往往并非指向实际的胜利或系统性变革,而更像一场仪式化的自我献祭。譬如说《边缘行者》中大卫不顾负荷植入大量义体,明知身体终将崩溃,仍以“成为传奇”为口号。这种自我毁灭式的升级,实则是通过献祭肉身来向世界发出嘶吼。而《赛博朋克2077》中的“以我残躯化烈火”结局中,V选择单挑荒坂塔,其行为本质是用死亡换取符号(符号,符号,又是符号)性胜利——肉体消亡的瞬间,其反抗精神被铭刻为传奇的一部分。
这注定是失败的,边缘人的反抗依赖技术(如义体、黑客工具),但这些技术本身就由公司生产。例如大卫的军用级斯安威斯坦义体,本质是军用科技公司的淘汰产品,其反抗行为反而提供了试验数据。V的传奇表面上是对资本的挑衅,实则其代表的符号又被转换成商品消解。
边缘人的自我献祭与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异曲同工:明知结局注定,仍以行动本身定义存在。大卫的最终战并非为胜利,而是为证明“我曾活过”。
这种反抗的悲壮性在于:意义诞生于无意义。如《银翼杀手》中仿生人罗伊的独白:“所有这些时刻,终将湮没于时光中,一如泪水消逝在雨中,死亡的时刻到了。”反抗虽败,但那些“向死而生”的瞬间,已是最接近自由的时刻。
我们总是期望看到边缘人如何突破这种困境。但残酷的是,在赛博朋克的叙事里他们注定失败。真正的价值在于失败过程展现的人性微光——就像加缪说的,反抗本身定义了存在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赛博朋克从未真正火过的原因吧,几人愿意去看注定悲剧的故事呢?
六、赛博朋克式美学
六、赛博朋克式美学
说了太多沉重的东西,我们还是讨论些表面的轻松的大众化的内容吧,虽说赛博朋克本身并未火到哪里去,但其美学概念可谓是火爆了,火到了只要沾上霓虹灯要素乃至机械就可以贴个Cyberpunk的标签上去。
不过在下对美学并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只能说说自己浅薄的理解了。
极繁,反差,故障艺术,这是我对于赛博朋克式美学的第一印象。
1、极繁
在观赏赛博朋克相关作品包括小说动漫电影图片的时候我们总会感受到极致的繁复:鳞次栉比的大厦、绚烂多彩的霓虹灯、水雾弥漫色彩暧昧的街道、见缝插针的投影广告......其并非简单的“多”,而是有特定逻辑的视觉暴力。这些要素堆积在一起总是给人一种很“脏”的感觉,大量无序细节所带来的视觉刺激也在深层次上意味着某种失序,就好像赛博朋克的世界一样。而这种脏乱,却又带来了些许生命力,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尘世喧嚣吧。
与此同时,因为技术极度发达,导致时空、种族、语言、性别、物种、现实与虚拟等边界都在消解,形成了多人种杂居、语言混用、性别倒错、现实与虚拟空间交互、极度包容的多元社会,这同样是极繁的一部分,文化意义上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赛博朋克世界看似混乱无序实则高度可控,就好像极繁的画面实则引领焦点一样(看起来很繁杂但第一眼看过去就是广告)。
2、反差
反差可以说是赛博朋克美学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与泥泞混乱的街道、扩张的都市与难以喘息的贫民窟、迷幻的霓虹灯与交错复杂的电缆电线、科技感十足的全息投屏与牛皮癣一般密集的手写广告牌……无数反差与我们的认知对抗,塑造了赛博朋克的世界。
不过前面已经说得够多了,端下去罢(不懂美学真的没办法啊,哎嘿)
3、故障艺术
之前一直没提过赛博朋克的关键要素“赛博空间”,故障艺术的美感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故障艺术往往是残缺意外错位的,挑衅着我们的视觉神经。在赛博空间中,一切都是带着些许错位的,时刻提醒着我们皆为虚幻。其有意打破了沉浸感,迫使我们在其中必须不断思考,不得不去面对冷酷的现实。
它意味着技术的缺点,又在某种意义上充满了个性,与赛博朋克世界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反抗着主流的审美,这也算是一种朋克吧(话虽如此,说它象征怀旧,怀念不那么冷酷理性的世界也说不准?)。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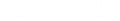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4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