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故乡是一条海岸水平线横轴,它的负轴是母亲的子宫;时间是一条无限的纵轴,与之反向的坐标是通往地狱的指示物。负的时间数值是倒退的时间,是记忆衰退的数据,是实际死亡的帧数,它们都属于地狱的空间范畴,负的进度条。无论人类、象征物或图像在章节与截帧中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被提前搭好的坐标系锚定它们能够被言说的位置。
在寺山修司剧团“天井栈敷”当过演员、和他有过多次合作的传奇女歌手Carmen Maki于2025年5月6日来华演出。来自厂牌textur3的策划,演出圆满落幕。时值首演,此文为留念Carmen Maki首次来华公演而作。
1969年发行的流行歌曲光碟里贮存着海浪的声音。
“一天,我将海舀进小小的烧瓶中,带回了住处。烧瓶摆在昏暗的草席上,里头的海已不再碧蓝。那温驯的海与我默默相视了一整天,仿佛是在幽会。”
——《关于海》(十八岁)
18岁的寺山修司一边写诗,一边把海带回了自己的房间。他绝不会料想到,14年后大多数日本居民的家中都贮存着海浪。
17岁的Carmen Maki凭借她独特的嗓音和妖娆神秘的气质演唱《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时には母のない子のように)后迅速走红。与此同时,包揽整张专辑歌词的作者寺山修司也因此名声鹊起。虽然此曲当时也被人诟病,这对真正无父无母的孩子来说是异常残酷的;但专辑《真夜中詩集--ろうそくの消えるまで》还是凭借这首歌总共卖出了百万张的好成绩。也让Maki一举成名,她还参加了第20届NHK主办的红白歌会。
我认为,《真夜中詩集》不仅是寺山修司60年代写作高峰期的产物,而且吸纳、运用了他在短歌、诗篇、散文中具有典型性的意象。细读这些歌词,我们得以窥见他的创作理念和强烈个性,结合他的身平经历,可以推算、构建出他未来电影风格与诗歌美学里接近永恒的坐标轴。
寺山像个天真而狡黠的孩童,他把自己的心思与秘密都藏在《真夜中詩集》专辑中、云淡风轻的歌词里,等待着听众、读者进入声音数据或文字文本时挖掘、解读他的作品的意蕴。专辑里每首歌像是他精心编制的关卡,里面藏着他整个童年与青春时代丰沛的善感柔情,藏着他整个人。他设置的文字捉迷藏游戏可以一直玩到未来,是无限的——除非是玩家自己想停下来。歌曲终焉,一旦从这场朦胧的游玩中醒来,我们会像他电影里拍的捉迷藏游戏那般重返现实、回到当前的时代,再次变回大人。
专辑中的成名曲《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前奏被喧嚣的潮声漫无目的地拍打着。喧嚣的海浪像处在青春期、试图离家出走的躁郁少年,尚未走远几步又放下匆忙的步调缓缓退去。
整首歌词有两条线索,一方面,海浪是此歌的主语,海洋是孕育海浪的母亲。“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一言不发地凝望着大海”讲述平潮现象;“那般试着独自踏上旅程/可是内心转眼就变卦”是轻微的潮涨潮落;“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试着写下长长的信 ”是时而离开大海的浪花,在平静期酝酿过自己绵长的心绪后,意欲在抵达海滨时与彼岸倾诉衷肠;“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试着大声地叫喊/可是内心转眼就变卦”表现了海浪在高潮时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气势,却在靠岸之际迅速退却了。“若成了没有母亲的孩子/就再不能对谁述爱了”,海浪一旦失去海洋便无法独立存在,只能化作一滩水渍。失去主体性身份的海浪,无法再表达由主体萌生的情感了。
另一条线是歌词直白地袒露少年渴望脱离母亲而存在、想离开家乡却又进退两难的矛盾心境。这不仅是青春期的病症,儿子与母亲之间深沉、隐秘而复杂的情感逐渐演绎为海浪与海洋之间深邃、缠绵而难解的眷恋。这类与俄狄浦斯情结相近的情感贯穿着寺山修司一生的创作。
之所以用相近来形容,是因为他童年里父亲总是缺场的;几乎完全不具备威胁性。他父亲是一名辗转各地的警察。家庭变动导致寺山从小就经历过数次搬家。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他的父亲被应征入伍,寺山修司十岁时(1945年),父亲病逝于塞班岛。同年,他的故乡青森市在空袭中受到严重破坏,和母亲住的房子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根据寺山回忆里的叙述,从战争疏散地古间木回到青森,第一个前来迎接他的,是海。
“回到自己出生的小城,晚上独自入睡时,我曾朝着月夜下大海的方向,将房门打开了一小会。并没有人趁机而入。而睡梦中那片无边无际的苍蓝海原上,漂浮着无数帆船,如同幻影。我开始憧憬怒涛拍打的洗礼。仿佛有一种肉欲上的疼痛,令我血脉沸腾。(而后,我便追寻着盛夏的海上潮响,渐渐睡去。)或许在身体里的海死去之时,我才会懂得去爱。”
——《关于海》(二十二岁)
于是海成为了“无家可归的孩子”的归宿。
1968年,这位后来被誉为“东方费里尼”的日本异色电影大师不会料想到奇遇会如剧本般发生。在他刚建立剧团“天井栈敷”不久,就空降了一位极为贴合自身文本气质的孪生形象临时加入:她是Maki Annette Lovelace,出生于神奈川县镰仓市,父亲是有爱尔兰和犹太血统的美国人,母亲是日本人。Carmen Maki是她日后作为歌手的艺名。她有着与生俱来、动荡而迥异的跨文化气质。这位从香兰女校辍学、离家出走后,仅仅因为和朋友出去逛街时观看了“天井栈敷”《蓝胡子》的演出后就决意加入游方剧团的少女,不正是作者笔下脆弱敏感、渴望逃离家园,加入马戏团少年的翻版吗?
虽然Maki在剧团的时间不长,仅出演了剧场版的《抛开书本上街去》,漂泊不羁的灵魂,注定在“马戏团”的停留是暂时的。1970年,也就是她凭借热卖单曲崭露头角后的第二年,突然宣布转行,从一位当红女歌星转变为一名女性摇滚乐手。一整个70年代,她不是组建、参加过多个乐队演出却又很快退出,就是总会面临乐队解散的结局。常以波希米亚打扮示人、职业生涯不稳定的她,在演唱过《无家的孩子》(家なき子)后,也总会被人视作“无家的孩子”;无家的孩子总在歌唱着。
歌曲《无家的孩子》是专辑中收录的第二首,奠定了整张专辑感伤、迷惘的基调。前奏的念白是寺山根据Maki的真实身份写就的。像一档深夜电台广播节目的群众热线环节,孤独的听众排着队被接入热线。长夜绵绵,一位17岁女孩在电话那头喃喃絮语,旁若无人地作着自我介绍,倾吐心境。
“晚上好 我是Carmen Maki / 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我和母亲本想去美国和父亲一起生活 /但母亲生病了/没办法乘船 /从我小时候起 /就经常收到父亲送的各种东西 /但是后来 父亲与我们的联系中断了/至今已将近10年/那时候的事我几乎都不记得了/也并不觉得寂寞
而至今也深深烙印在我心里的是/我出生的家里那白色的墙壁/我虽然是在镰仓出生的/但直到最近我才第一次回到那个家/一进家门,就看到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墙壁/为什么我唯独记住了这个/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 不知怎的/白色总给人一种悲伤的感觉”
独白的部分占了整首歌三分之二的篇幅,足见其在词作者心中的分量。模仿深夜电台的节目效果是寺山给每一位“无家可归孩子”的礼物。Maki和他们是同一代人。她忧郁的低吟,似与同代的友人分享彼此脆弱的秘密。迷惘的少年披露着内心。对家的情思,一方面是寺山自身独特的童年经验片段的写照,另一方面的外显形式是政治化、理想化的家国情谊与人类情感。它会绵延到广袤、遥远的未来;这是每一代年轻人都会经历的“无家可归”,他们游荡在精神的荒野里。
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后建立起驻日基地,这是二战的遗物,也是美国布局全球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无家的孩子”是指那些深受战争影响,经历过战争、战后出生的几代人。
他们共有一个家。母亲名为日本,缺席的父亲战死;继父叫作美国。“父亲去世后,寺山修司的母亲在三泽空军基地附近的酒吧工作,顾客多为大本营里的美军。这取材于作者独特的经历。“我和母亲本想去美国和父亲一起生活”体现了日本的政治地位总是处于美国权力阴影的笼罩下,母与子是家庭关系中身不由己的一方。词中母亲“生病了”,暗指日本社会的病症。1951年,两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从50年代开始形成的一系列左翼学生思潮也是围绕对此事件的抗议、反对而愈演愈烈的。比较典型的是1953年与1957的砂川斗争,东京都砂川町(现立川市)的居民和全国学生联盟发起了一场反对美军基地扩建的运动。由于决策层的软弱,国家内部出现反对者、改革者的呼号,母子关系的恶化加剧母亲的心力交瘁。“无法乘船”意指无法与美国海军抗衡而内心又徘徊不前的日本。一旦出海,即“一起生活”;意味着母亲与父亲双方经过慎思后,就各自在整个家庭地位中扮演的角色达成一致。
“从我小时候起/就经常收到父亲送的各种东西”,指美国对日本施行的各类政治、军事、文化政策;“但是后来/父亲与我们的联系中断了/至今已将近10年”,一方面指寺山年少时丧父之实;另一方面指日美关系的恶化,这种恶化是客观的,也是身为日本国民在周围不断发生的运动、事件里主观形成的反美反基地情绪。这几代人是相继失去“家”的:他首先失去父亲,继而成为没有母亲的孩子;或许这个象征统一、整体的“家”,无论在历史还是情感层面上,都不曾真正存在过,也早已丧失了在传统中它理应扮演的职能。
对国家、战争、左翼学生运动、全共斗运动的思索同样出现在《不了解战争中》(戦争は知らない)。作者发问:
“考虑过祖国吗?祖国和朋友哪个更重要?我有两个故乡——爸爸的和妈妈的/两地中间隔着宽阔的海洋/能马上说你朋友的名字吗?/觉得和越南战争有关吗?/能为了别人而死吗?/觉得自己被爱着吗?”
这种爱于政治、家国而言,是狂热而赤忱之爱。有人会为爱而死,在狂热的、近似宗教的神圣激情中感受到被爱:左翼运动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大趋势。“在1968年前,就曾出现过早稻田大学抗议事件、庆应义塾大学抗议事件等校园群体冲突案例,失去权威性的日本共产党无法在学生群体当中获得信任,然而全共斗运动却使得左翼政治与学生群体完全联系在了一起。”(《一场昭和式的红色幻梦》)一场连锁反应开始了。
在1968年学运的背景下,日本110所大学的学潮斗争日渐扩大,接二连三地进入无限期罢课。1969年初,日本已有165所大学因全共斗事件陷入紧张状态,大多数日本大学被全共斗运动所占据。直到著名的安田讲堂事件发生,东京大学遭到全国全共斗占据,防暴警察进入校园,强行解除学生封锁。可这依旧改变不了安保条约继续延长其时间效力的历史事实。全共斗运动由此达到了历史最高潮阶段。
当“祖国”和“朋友”成为必须作出选择、可能引起冲突的概念时,一切处在危险的倾斜中。走在街道上的年轻人被传单和口号湮没,对意识形态咄咄逼人的提问困惑,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有些人涌向左边的人潮,有些人在历史洪流里保守行进,更多的人则迷惘地在原地徘徊。寺山修司在随笔中写道:“东京大学生在运动中被政府镇压,然而却赢得了全国青年的支持,这样的胜利却是进入迷茫的开始——日本青年该何去何从?”
回到《无家的孩子》第二层独白,“雪白的墙壁”是家作为意义的空无。寺山修司在自传《我之谜》写过一篇名为《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的短文,他认为“家”本身所具有的各项功能都已消失。“家的教育性、娱乐性、保护性,已经被社会所取代,而宗教功能,性的功能则有个人来完成。”
家是沉重的桎梏,民族的血脉,世代相流的血脉无力地相连爱的机能。强烈而鲜明的集体记忆裹挟、吞噬着私人记忆。安田讲堂的场地废弃了20年,东京大学也在1969年停招了一年新生。白色墙壁意味着重装与新修,是这一代无家之人精神成长的空白期。一进家门映入眼帘的白色,也象征着个体被抹去个性、压抑情感后的创伤反应,一种袭上心头,难以言述的虚空。
可见寺山写作的歌词与它当前所处的时代、事件紧密相连;他的写作具有宽阔的视野、穿透性的目光;但他最钟爱的主题,总是围绕个体展开。《无家的孩子》歌曲部分唱到:
“没有母亲的孩子/也会恋爱/没有家的孩子/也会恋爱/所以我也会陷入恋爱/所以我也会陷入恋爱/流动的云/也会恋爱/空中的云雀/也会恋爱/所以我也会陷入恋爱/所以我也会陷入恋爱/可是我不明白/该如何去恋爱/即使远远地看着/百合花盛开的小径/没有母亲的孩子/也会恋爱/没有家的孩子/也会恋爱/所以我也会陷入恋爱/所以我也会陷入恋爱”
对恋爱的追寻是寺山修司创作中时常触及的话题。歌词中反复出现的“所以我也会陷入恋爱”,是对未知之物的憧憬,绵长而缥缈的迷恋。少年生了名为孤独的疾病,急需囫囵吞下名为爱恋的药丸。殊不知甜蜜的糖衣下包裹着清苦的哀愁。
在他创作的电影《草迷宫》中, 主人公根据手球歌寻找着母亲。少年遇到心仪的女子却总是处于爱而不得的状态。每当他想谈恋爱时,母亲的形象就会出现从中作梗。在歌曲《如果人生只有别离》(さよならだけが人生ならば)里,他借歌词感叹苦恋:
“如果人生只有别离/那邂逅那天算什么/美丽动人的晚霞/二人的爱又算什么/如果人生只有别离/刚建好的家算什么/寂寞冷清的平原中/点亮的灯光算什么”
女性形象的切换也是寺山本人对异性态度的真实写照。他以花喻人,认为花中混集了少女的纯情与上了年纪女人的情欲,令人难以应对;在与花相遇时感到的恐惧比怀念更为强烈。渴望与年轻女子恋爱,实质上求得与母亲的亲近,以找回在童年中未被确认的自我价值。
在《不了解战争》中,Maki唱道:
“战争中死去的悲伤父亲呀/我是您的女儿/二十年后的故乡/我明天就要成为新娘/新娘哦......不了解战争的我年满二十/嫁时已成为人母”
从以上两段歌词能体现出寺山对新娘与母亲这两个词幽微隐秘的情感态度与复杂惆怅的心境。他日后创作的电影《草迷宫》结尾的台词呼应了“新娘”与“母亲”的悖论, “那个梳妆打扮成新娘的女郎就是我母亲。让云彩做我的向导, 穿越海洋、山脉,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国家,去寻求真谛。不要问我为什么,我渴望听到手球歌,我将一直走下去。”
他梦想中的爱恋对象(即新娘)本该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却被日渐老去的母亲代替;电影最后母亲穿着一袭华丽的红色打褂,双眼含情脉脉间露出光艳照人的神色,相较原初疯女、娼妓、寡妇的形象有着云泥之别。
现实中渴望年青女子成为新娘-母亲的过程是同时的或递进式的,是自然流溢的爱恋与青春气息所致。寺山影片中的母亲-新娘是依存却游离的关系。比如穿着红衣、幻想自己是新娘的未婚先孕的女性角色,或是隐喻主人公的母亲是少年初次性幻想的实施对象,故为新娘。她们是少年内心世界的投射,映衬着少年精神依托的匮乏与贫瘠,他渴望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母性的认可。在他步入外部世界寻求真理之前,他要先与认可与信任结盟。
手球-婚约的过渡,源于孩童-成人的转变,用手拍打的球体,以手写就承诺的文书。而从一个家转向另一个家的中间地带,是少女的恋爱王国。里头有秋波流转的美人、冰肌玉骨的胴体;对少年而言,这个国度同时也是欲壑难填、情欲燃烧的地狱。怅惘的少年不得不避开她们寻找出路,不断找回自身。寻找母亲是为了寻回自我认同感,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寻觅到幸福之际,新娘会穿着白无垢,缓步走向神社。少年会彻底忘记母亲的音容笑貌、绣满花卉的华丽红色打褂。
寺山在《被山羊牵引》(山羊にひかれて)里也讨论了关于“幸福”的话题。他笔下的少年正被山羊牵引着。歌词写山羊牵着少年向遥远的国度前行。作者发出疑问,这是幸福、还是不幸?“山的彼端到底是什么/爱过的人/告别的人/都让他随大草原的风散去吧...回忆是唯一的旅伴/这就踏上追寻的旅途”......
山羊一方面代表罪孽,是西方基督教文化里被审判的罪人;是古希腊文明中魔鬼的象征,半人半山羊的潘神总以色欲的化身出现。山羊牵引少年的概念影响着寺山修司日后的电影创作。现实中山羊会被人牵引,人被山羊牵制的说法却很罕见,与他影片中运用的手法如出一辙:主客错位、理性与感性的秩序破环,现实生活与幻想世界的颠倒。
在《死者田园祭》中山羊以疯女的形象出现,她终日衣衫不整,在沙砾里折取玫瑰;少年被她吸引,镜头追随她的脚步,在恐山的海滨不知疲倦地跳舞。它被描述成一种性的引诱与对真实的偏离:它把少年领到山脚,刺激他的感官系统,触发他对现实与幻觉真假难辨的体验,赋予他对“山的那边”的无限怀想——寺山笔下的山与他童年故乡的恐山密不可分,它真实存在于青森县下北半岛中部,严格来说是座活火山,而非连绵的山脉与草原。
总体而言,《被山羊牵引》是寺山试图追问幸福而作的轻快歌谣,他的幸福观也能在随笔中找到答案,“人之所以追求远在‘山的那边’的幸福,是因为觉得自己现在所处的现实不真实。明治时代的挂钟、阴暗的佛龛以及在大家庭中永远存在的等级,这一切是多么地让人不堪忍受。”(《寺山修司幸福论》)
以“被山羊牵引”为题,或许是出于对中原中也的致敬。中原中也是昭和诗坛早逝而耀眼的流星,被誉为“日本的兰波”。他一生只出版了两本诗集,代表作有《山羊之歌》。其中收录的《羊之歌》是中原中也赠与朋友安原喜弘的组诗,里面有一段写道:
“若听见火车的汽笛声/便会将旅愁,幼时想起/不不,并非想起幼时抑或旅途/只是那看似旅途,看似幼时的事物......”
在寺山的自传中,他不止一次提到“我的故乡是一列飞驰的火车”,他总是笑称自己是在火车上出生的,处于摇晃、模糊而分裂的地带。被山羊牵引是追随诗文重返故乡的心境,而“看似幼时的事物”揭示了重返家乡的不可能性,回溯过去只是一场场模拟,一次次虚构。怀着对幸福的犹疑,寺山修司把写好的“山羊之歌”送给了Carmen Maki。
Carmen Maki也成为他后来电影创作中重要的女性形象: 《死者田园祭》里优雅隐忍的女邻,或镇上癫狂的疯女或媚眼如丝的马戏团空气女。她们都有一双密布着迷惘与哀愁的血丝却目光深远的明眸,挽着丝缎般秀丽的黑色长发。
Maki从海的另一边走来。走到定格的镜头前,被印刷成《真夜中詩集》专辑封面。她的半身像有一种与歌曲氛围相互冲突的神性美。她上下眼睑的睫毛如曼•雷(Man Ray)的摄影作品一般被拉长。东方的乌发、欧式的面部轮廓,媲美埃及艳后的眼线,背部大面积露出的肤色,媲美埃及艳后的眼线...她的面庞会击中任何一双企图凝视她的眼睛。从塞壬这儿离开吧...远处的背景是一片海。这片海的颜色与《草迷宫》中少年端详女子胴体时的海共用一个色调的远景。不用怀疑,Maki是望着这片海的声浪,录下《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中海浪独白的。
《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时には母のない子のように)、《生人即离别》(だいせんじがけだらなよさ)和《骡子与老伯》(ロバと小父さん)都收录于《寺山修司少女诗集》。《真夜中詩集》中每首歌词,都闪耀着寺山的奇思妙想,繁星似地点缀着他的童年。
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寺山修司少女诗集》中译者对《生人即离别》的诗题有这样一段注释:歌名来自唐代诗人于武陵的五言绝句《劝酒》中的“人生足别离”,日本作家井伏鳟二将其译为:“别离即人生”。寺山修司少年时代根据这段话,用反句来写下“生人即离别”。
寺山偏爱在诗中穿插谐音游戏,有如他的电影一直在玩“捉迷藏”的游戏。一种童心的外显形式。在《少女诗集》里他写医生的体重是十五贯六百四十匁,而“一五六四”与“杀人犯”同音;他写少年离家出走时经过的楼梯,“此时正好是八月八日五时六分四秒之前”。而“八八五六四前”与“杀死母亲之前”是同音。或许是因为他从小住在恐山附近,感受过周边的占卜师、通灵者用语言的力量祭祀魂灵,与死者沟通。在他眼里,同音异义和倒读有着同样的魔力。
《生人即离别》的歌词好比一纸咒语,光辨认文字、读出音节还不够,需要一位伶俐聪慧的祝巫来掌握仪式的进程,释放强烈的信息流与能量场:
“曾经进行过占卜/也念过咒语/尝试着说各种听不懂的话/驱魔辟邪保平安/为忘记悲伤的回忆/寂寞之时嘴唇微动/配合奇怪的咒语/我常说的是/离别有只生人/知道是哪的语言吗/离别有只生人/离·别·有·只·生·人/寂寞之时所说的/孤独的咒语/为了将分别之人的回忆/忘记的咒语/离别有只生人/离别有只生人/反过来读/就成了那人教给我的歌/人生只有离别/人生只有离别”
而另一首《ロバと小父さん》(骡子与老伯)则在出版诗集的过程中被改成《什么都附上价格的旧道具店老头子的诗》(何にでも値段をつける古道具屋のおじさんの詩),这一标题的转变削弱了歌曲本身反复询问的“爱和泪水哪个更贵”哀愁、感伤,更像是涉世未深的少女,踮着脚尖张望货柜里的商品,时不时从脑海里蹦出一系列天马行空的问题,极富童心童趣。
通过歌曲《海鸥》,我们得以窥见藏在专辑里的寺山修司。他本人的好恶、审美趣味和性情逐句现形。曲调优美得如同海鸥灵巧的身姿,它时而轻抚蓝天,时而低掠海面;水天一色,被海鸥跳的圆舞曲漾开了。
“相比星条旗更喜欢日之丸”,重申了寺山对日本民族的赤子之心。他是安保斗争的见证者。安保斗争是发生于1959年,是一次日本青年及学生为阻止《日美安保条约》条约自动延期而发起的一系列大规模反对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未能阻止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60年代的寺山修司写过富有煽动性的广播剧《猎捕大人》(1960),立即遭到当局的审查。后来这部作品成了实验电影《番茄酱皇帝》剧本的原型。
“相比穿鞋更喜欢光脚”,寺山修司的确不喜欢穿鞋。在《我之谜—穿长靴的男人》一文中他表达了自己对鞋子厌烦的态度,他认为鞋是家的象征,无论走到哪里都血脉相连的宿命。双足代表两亲,暗含父母压迫、自身需要削足适履适应之意。话虽如此,他还是在自己25岁时与电影演员九条映子成了家。
“相比紫式部更喜欢清少纳言”,紫式部工小说而清少纳言偏爱随笔,寺山大部分文字作品也是以自传、随笔的形式出现。60年代他写作了大量戏剧与电影剧本,短诗与和歌集;“相比钢笔也更喜欢铅笔”,铅笔是孩童在日记、涂画过程中会反复涂擦的实践工具,而钢笔代表少年时代的书写材料。更喜欢铅笔表达作者渴望回到童年的愿望,试图从拙稚的用笔重述童年。而在《寺山修司少女诗集》中,作者反复写到了“彩色铅笔”:“将两支彩色铅笔/放到枕头下”、“骑着/彩色铅笔/走吧去地狱买糖果”、“骑着彩色铅笔/奔往地狱的天文馆”。放在枕头下的彩笔是为了预演色彩缤纷、姹紫嫣红的梦境;而骑着彩色铅笔去地狱买糖果,丰富、加重了画面的质感。
寺山修司把彩笔的意象落实到电影里,成为极富代表性的具象化表达。在《死者田园祭》尤为突出:他给镜头加上色彩滤镜,增强画面的冲击力。流血的太阳、赤红的天空、中毒似乎的绿色河流与紫色地面,少年走进马戏团的场景,有时采用调色盘式的色彩柔化效果,使不同颜色和谐地并置在同个空间内。影像依靠色彩把主人公魔幻妖异、风云诡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浓烈的彩色笔通过对个人主观感受的加工、交叠、传递,连接起影片彼此交错的多重时空。
寺山修司写对马戏团的理解,伴随着充盈着神奇幻想的永恒“异国之梦”。他借哈特利的诗句来解释自己的创作理念:“过去皆为异国”。他试图在时空中寻找自己与异国的联系,每一次对故乡的重返都是抵达不同的国度。
故乡是一条海岸水平线横轴,它的负轴是母亲的子宫;时间是一条无限的纵轴,与之反向的坐标是通往地狱的指示物。负的时间数值是倒退的时间,是记忆衰退的数据,是实际死亡的帧数,它们都属于地狱的空间范畴,负的进度条。无论人类、象征物或图像在章节与截帧中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被提前搭好的坐标系锚定它们能够被言说的位置。
在《死者田园祭》中,地狱、时间、子宫,故乡的四方交点是零,如果把它放大它会像一尊圆口型挂钟,指针静止在转动处。它是地狱是时间是子宫是故乡是无法脱离空无而存在的永恒凝固物。第一象限是现在与未来发生的事情,幻想中的事物;第二象限是承托了回到过去杀死祖母的愿望,讲述母亲与孩子关系;第三象限是孩子需要通过祖母、母亲或超自然的母系氏族介质(母亲从地板上打开的那扇异世界门格/恐山的神婆象征祖母辈的氏族关系)才能完成与父亲对话的通灵仪式;第四象限是个体对回忆的无限回溯、幻想与自圆其说。
人生就是舞台上被搭好的马戏团帐篷.......
“相比托尔斯泰更喜欢亨利·米勒”,1955年,20岁的寺山因肾病住院了四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了包括亨利·米勒在内诸多作家与哲学家的书籍。相比托尔斯泰这位道尽严酷苦难的大部头作家,把情色是为游戏与幻觉的米勒更契合寺山的心境。他巧妙地运用了米勒来委婉地表达在战争阴影下笼罩着的性压抑与苦闷。这是一代的人难题,属于父母辈之间的难题,他们身上的难题又传给了下一代:父亲的意外去世加剧了死亡的禁忌性;母亲因守寡而缺失的生本能筑成一道藩篱,血气方刚的少年寸步难行。
“想要一直被别人爱着/不想变老/不想要钱”出于对母亲全然的反抗,母亲长久以来都是被爱的绝缘体,母亲苦守着墙上的挂钟老去,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为了赚钱糊口选择去美军驻扎的酒吧打工。“男人们都去向了远方/只留女人苦苦等待”,它们投射出作者内心厌惧之物,也因此作为他创作与抵抗的信条: 与不同身份、性格的异性周旋。《死者田园祭》里的少年与邻家美人计划私奔, 接受马戏团空气女的性暗示,和飞蓬乱首的疯女在海滨追逐嬉戏;企图阻止时间的流逝;《再见箱舟》的开头是男子埋葬全村的时钟,企图抹去时间的存在,让村民失去时间意识。他为赌马场的赛事撰文,一生酷爱赛马。含有运气成分的博彩行为是危险的,无疑是一贯淡漠的金钱观使他得以自洽。
寺山有一匹赛马名叫尤利西斯(Ulysses),与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同名。他为什么给骏马取这个名字?对于希冀常胜将军的玩家而言,此名着实为不详之兆。在特洛伊战争中取胜后,尤利西斯在途中因命运施展的魔咒,不得不在海上历经十年的漂泊才返乡归家。寺山视海如故乡,或许骏马疾驰的身姿总会激荡起他的心潮,是他无数次穿溯回少年时代的缩影,马蹄在尘土与空气之间,踏平、消弭着被压抑的冲动与渴望。马在地面疾驰,海鸥在海面盘旋。
失去了幻想的少年回到真实世界,只能寄情于无忧无虑的海鸥。喜欢之物并非拥有之物。
寺山修司在《关于海鸥的序章》里借少女之口讲述“在海里死去的人都会变成海鸥”的传说。而这个概念的原型来自于传奇女歌手朱丽叶特·格雷柯(Juliette Greco)唱过的歌曲。海鸥是沉溺在故乡情网里的死者,是回忆里盘旋不去的亡人,是自愿投海、自由无拘束的魂灵——它们飞过美国海军驻扎的舰队,它们没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不受管制,自肆交欢,这首轻快的安魂曲在水面上来回穿梭,飞越山海,天国或地狱。
萨特曾评价朱丽叶特·格雷柯(Juliette Greco)雷柯的嗓音里有100万首诗。“她就像一盏温暖的灯光,重燃我们所有人心中仍未熄灭的余烬。”;“多亏了她,我才写了歌曲,而我也是为了她而写歌曲的。我的词句在她的口中成了宝石。”同样,寺山的诗句经过Carmen Maki声带的切割,被打磨成珠玉。
寺山在《少女诗集》里丝毫不掩饰对宝石的热爱,为翡翠、祖母绿、蓝宝石、石榴石、无名宝石写下梦幻的诗篇。他把人生阶段划分为失去宝石-了解宝石-寻找宝石的阶段,并指出名为爱的宝石不是自己丢失的宝石。我认为宝石对作者而言是一种信念。信念本身包含着爱,爱是信念的原材料,是天然的矿物晶体,由于自身不同微量元素的添加而被命名为宝石,不同种类的水晶拥有与各自性质相符的信念类型。
“只看一眼那块宝石/士兵忘记了战争”,士兵有了信念,战争被崇高的事业替代;“只看一眼那块宝石/谁都会想要恋爱”,当作为一种感受的爱叠加一种不磨灭的信念,爱不再受制于幻想或理性,转为一种迫切的想法及行动。在《两个人的词》(二人のことば)中,紫水晶以无名宝石的形象出现,紫水晶代表的信念是持存和等待。
“这个戒指赠送给我的人/已经不在了/这个虽然不是紫水晶/但赠送给我的人曾谈过紫水晶的故事......既不太贵也不太便宜/正好适合我/巴西出生的宝石/和那个人毫无关系/也没有有用的回忆/但只是反复说着 紫水晶 紫水晶 紫水晶 紫水晶 /感觉眼泪正在干涸/两个人的语言/两个人的手 两个人的莫扎特/两个人的大海 两个人的歌/两个人的梦想 两个人的故乡/两个人的爱/只是在一起的两个人/让你和我感到幸福/在没有人的无人岛上”
在寺山的理念中,“眼泪是人做出来的最小的海”,海在枯竭,露出星罗棋布、荒芜的无人岛。只有主人公被业已消逝的幸福承诺锁住了手指关节,把等待和重复误作了信念。歌词中镶嵌在戒指上的晶体只是紫水晶的相似物,讲述的是独自一人苦恋的幻想与无限重复的感伤。
曲终人散。寺山修司留给读者、听众捉迷藏的游戏也即将结束。正如电影里玩捉迷藏的孩子们业已长大成人,穿着各色制服离开了。纵观寺山修司整个创作生涯,横跨诗歌、文学评论、电影、戏剧,都是诗中有画、图文并茂、声画并行且知行合一的,彼此相互交融渗透。
歌声停止,当游戏结束,我们重新回到开头的那片海。收录于《寺山修司少女诗集》的《浪声》一篇中,寺山讲述了一个被遗忘的女人的故事。她住在海港边上的红色旅馆。每天傍晚时分,她就走去海边,将浪声录到卡带式录音机里。女人的故事简单又老派,她等待着心上人,一位迟迟未归的水手重返港口。最终,磁盘里储存着她在跳海自杀时录下的浪声。
一声“扑通”如同波浪中心的水怪,在人类凝望大海时,突然出现一头阴翳的巨兽,它并没有扑过来也不会威胁游客的生命,可它就站在那边静静望着你的眼睛,随后沉入水底。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啊!离家出走和自杀是相似的,都源自一种原始冲动。
半明半昧、磨砂似的记忆在听众的耳膜里晃动。海浪正翘首以待。它卷起舌尖,发出叹息的音节,海风捎走残留的咸腥。沉溺在涨褪之间,被寂寞吞噬的声音穿透了所有海的墟罅。日复一日的白昼,远处的船会载着人类,打捞战争的残烬,情欲的尸骸。
最后,我想用Oricon(日本公信榜)在1969年的单曲年榜(1-30)来结束全文。榜单上Top1的歌曲是由纪さおり的《夜明けのスキャット》。它旋律优美,歌词简单真挚,讲述一对月下星前的情侣沉浸在彼此的爱恋里,时间仿佛为他们静止。歌词以“时钟停止”(時計はとまるの)作结。
把时钟拨回1969年,会看到一些并不热衷于投身政治的年轻人,他们身处于炽烈而极端的思想加速更迭的前夕。他们怀有的不安感更贴近当前时代的脉搏。他们不想抛开书本、不想上街、不想读书、不想占领学校。
他们轻轻地把自己的观念与情感收拢进历史的档案袋。比起信仰,他们更向往运动平息后宁静的星空,羞赧的青春期,能用简洁描述的爱。他们希望所有的时钟在此刻失灵,守护思想与行动的安宁。这一代人缺失的,是一个抚慰人心的深夜电台,他们期冀一位声线优美的女主持人倾听自己的童年、家乡,隐痛和梦想。他们期待在百货商店或音像制品店里买到一盒能抚慰迷惘的心灵工艺品,或者收到一份象征回到童年的歌谣曲作为温馨的圣诞礼物,强颜笑别昭和44年的尾声。
1969年也是寺山人生意义上的转折点。他剧团的“天井栈敷”有了地下剧场,他给唐十郎的状况剧场演出时送了花圈,引发一场误会,导致殴打事故的发生。两位同样才华横溢的导演不打不相识,反倒惺惺相惜。年底他与九条映子离婚。仅凭一张《真夜中詩集》,我们便能窥见寺山修司奇幻的笔调,以及他走马灯、万花筒似的人生中琳琅夺目的一隅。
人们不会曾料想到,即将跨入的70年代会是如此变幻无常。晚春的序幕是赤军的大型恐怖剧展演会。他们会犯下一系列包括劫机、爆炸、勒索等罄竹难书的罪行;三岛由纪夫同年切腹自尽;而寺山修司则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几个年头里完成了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五部长篇。他留下的文字与影像有如霓虹灯影,把日本新浪潮的招牌映托得五光十色。
业已发生之事,都会消逝于海平面的彼端。Maki那轻柔而略带沙哑的梦幻之音,逐渐被自戕的浪花、少女的泪滴湮没。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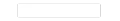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