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2024年,圣塔菲研究所出版了《复杂科学经典论文集》,其中收录了《行为、目的和目的论》(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1943,下文简称BPT)这篇奠基控制论的文章。
三年后的2025年,集智俱乐部发起了《文集》的复杂科学经典论文读书会,我很幸运地被邀请做关于BPT的分享,也恰好借此机会重读这篇控制论的关键文本,重新理解控制论的思想源头,厘清那些看似常用的术语在维纳的语境中究竟所指何物(例如「行为主义」),相信这对于澄清对cybernetics的误解有所裨益。
本篇推送即为此次分享的讲稿整理,并增补了《控制论的诞生》(The Birthday of Cybernetics)的译文。这篇短文是《文集》中《行为、目的和目的论》的前言,作者是英国控制论学者和科学史学家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文字概览式地呈现了BPT成文的前因后果,对于BPT文字本身是很好的引入。
一、控制论的诞生 The Birthday of Cybernetics
一、控制论的诞生 The Birthday of Cybernetics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Andrew Pickering, University of Exeter,2024 Cambridge University Express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该论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是一篇简洁明了的短文,对控制论这一新兴学科的奠基具有核心意义。控制论作为研究复杂系统的全新领域,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蓬勃发展,并至今仍在不断演变(Kline, 2015)。《行为、目的与目的论》(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源于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与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在美国期间的战争研究,旨在研发一种防空预测系统(Galison, 1994)。该装置的目的是通过追踪数据的外推,预测敌机在炮弹到达其位置所需的时间内会到达何处。该项目并未成功,但它促使维纳开始思考以负反馈和系统为基础的有目的行为(purposeful behavior),这些系统旨在最小化当前状态与预期状态之间的差距(在该例中,即目标位置与爆炸炮弹之间的差距)。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负反馈和伺服机构在工程学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可追溯至19世纪蒸汽机调速器及家用恒温器),但控制论的开创性举措在于将这一概念尽可能地推而广之。反映了维纳的朋友、墨西哥著名生理学家阿图罗·罗森布卢斯(Arturo Rosenblueth)的观点的是(Burbano, Reyes, 2022),BPT消除了机器、动物乃至人类之间的差异。作者们认为,对有目的行为的相同分析可以涵盖从伺服机构到有机体以及一般意图性行为(intentional action)的整个范围。维纳在其1948年的著作《控制论,或动物与机器中的控制与通信》中进一步扩展了该图景,将信息流与处理纳入其中,这些正是防空预测器等反馈机制的核心内容,并由此引入了数字计算、信息理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等领域。(此后,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例如,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科学催生了符号人工智能,这种认知大脑模型与通过反馈回路与世界互动的述行性[performative]控制论大脑形象截然不同。)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维纳的愿景在著名的梅西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阐述,该会议名为「控制论:生物和社会系统中的循环因果与反馈机制」(Pias, 2009),该会议于1946年至1954年间举行,汇聚了跨学科领域的专家,包括维纳本人、约翰·冯·诺伊曼、海因茨·冯·福斯特、玛格丽特·米德和格雷戈里·贝特森,沃伦·麦卡洛克担任常任主席。梅西会议标题中提到的「循环因果」(circular causality)指向了另一条综合路径。该观点认为,反馈系统中输出作为输入返回的循环特性,使控制论区别于现代物理学的线性因果关系,并由此催生出一种不同的本体论或世界观。为此,冯·福斯特选择了神话中的衔尾蛇(Ouroboros)作为控制论的象征。由此,控制论作为一门新科学(后成为斯蒂芬·沃尔夫拉姆2002年关于细胞自动机著作的书名)展现出鲜明的哲学色彩。随着控制论影响范围的扩大,它也成为政治批判的焦点。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981)到法国团体liqqun(2001),众多学者指出控制论的战争起源及其对控制(control)的强调,使其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重要工具。相比之下,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1991)在反本质主义对人类与机器界线的模糊甚至融合中发现了激进政治行动的潜力,该理念在她提出的「赛博格」(cyborg)概念中得到体现。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BPT的微小开端孕育了多条发展脉络。其中包括一种独特的机器人学风格,它依赖搜索机制而非人工智能计算,从格雷·沃尔特(Grey Walter,1953年)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乌龟机器人」(tortoises),到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在20世纪80年代的反AI包容架构。在冯·福斯特(von Forster, 2014)主导的运动中,所谓的二阶控制论将观察者纳入反馈系统,引发了更广泛的伦理学和激进哲学建构主义讨论(von Glasersfeld, 1995)。尤其在英国控制论领域,罗斯·艾什比(Ross Ashby, 1952)于1948年设计的内稳态机(homeostat)具有深远影响。与伺服机制不同,内稳态机能主动探索并适应环境,从而在精神病学、管理学、环境学、教育学、艺术和建筑学等领域催生了极具特色的项目和成果(Pickering, 2010)。控制论如今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中被广泛讨论,而在工程学中则较少提及,但BPT的回响仍遍布在各学科领域中。
二、读书会分享|控制论:一次终结了「旧」哲学的科学分类
二、读书会分享|控制论:一次终结了「旧」哲学的科学分类
本次分享整体遵循文章层层递进的分类法结构,主要以《行为、目的和目的论》原文为基础,以句子为单元,延伸一些当时的背景和后续发展,因此过程中会不断地跳出、返回原文文本。
1.两个目标
1.两个目标
BPT的开篇就单刀直入的说明文章写作的两个目标:
这篇论文有两个目标。第一是定义对自然事件的行为学研究(behavioristic study),并对行为进行分类。第二是强调目的(purpose)概念的重要性。——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第一个目标框定了行为学的研究方法。如今我们对「行为学」(或者行为主义)很容易望文生义,产生理解偏差,误认为BPT乃至控制论提倡的是那种条件反射式的机械方法。其实不然,行为主义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分野,而了解当时美国的行为主义发展有助于理解BPT提及「行为学」的具体语境。
首先是约翰·B·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提出的经典行为主义,这是20世纪20-40年代美国心理学的主流学派,将可观察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摒弃内省法和心理概念等研究主题。华生提出了「刺激-反应」(S-R)模型,将行为解释为简单线性因果关系。可以说这几乎等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
而稍晚一些的B.F.斯金纳(B.F.Skinner)提出的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直接从巴甫洛夫学派发展起来,认为个体行为是由行为发生后产生的结果所塑造和控制的,强调控制行为的「强化」和「惩罚」,认为行为是绝对机械、可客观化的。他最著名的模型就是提出了斯金纳箱,通过给小鼠奖赏或者惩罚让来塑造其行为。
然而BPT或者说维纳所提到的行为学,更接近于另一学派,那就是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Tolman)在20世纪30-40年代提出的「目的性行为主义」(purposive behavioristic),该理论在行为描述中引入「目的」等偏主观的心理学词汇。托尔曼挑战了经典行为主义的模型,他认为在「刺激-反应」中间存在着无法被外部观察到的因素,但可以根据引起行为的先行条件及最终的行为结果本身推断出来。他将这个因素定义为「中介变量」(mediater),并提出了「刺激-中介变量-反应」(S-O-R)模型。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无法被观察到的内部变量的概念封装。
同时,托尔曼不认为行为是一个简单的生理反应,而是包含了目的的完整行为序列,目的可以客观表现在这个序列中。托尔曼由此提出了整体行为(Molar Behavior)的概念。这颠覆了传统心理学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目的」是神秘的,是有机体的主观内部心理状态。
这里就完全涉及到BPT的第二个目标:对「目的」的强调。后文中可以看到,BPT通过严谨的、层层递进的分类法,将「目的」这个长期被科学排斥的概念,重新纳入可量化的科学研究范畴。BPT通过对目的的机制性定义,提供了一种「科学上可接受」的目的概念 ,将「目的」视为系统与环境交互过程中可观察、可测量的属性,也就是「输入-输出」关系,而非不可观察的心理状态从而诉诸于唯心主义。
这为在科学框架内研究目标导向系统提供了一条途径,有效地规避了历史上困扰科学目的论的哲学陷阱。因此这并非是对亚里士多德式目的因(causa finails,也译作终极因)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概念上的重构。
这种工程学/生理学模型与心理学探究的融合,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稳健的、可外部化的目的定义,使其能够被更具科学严谨性的心理学所接受,从而超越了严格的「刺激-反应」模型的局限,为托尔曼的理论提供了更加科学化和形式化的语言。
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中,维纳这样评价在此之前的心理学:
过去大多数心理学实际上不过是特殊感觉器官的生理学,而控制论正在引入心理学的整体观念,都是与这些特殊器官有关联的高度专门化的脑皮质区域的生理学和解剖学。 ——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1948
在BPT之后,维纳用大脑和神经层面的生理学和解剖学来解释心理学上的人类现象,这可以说是用一种更精密的科学来定义和解释诸如目的性行为等现象,而这原本被认为是属于科学边缘外的模糊地带。
2.定义一个过程,而非对象
2.定义一个过程,而非对象
输出(output)是指对象在周遭环境(surroundings)中所产生的任何改变。反之,输入(input)是指对象外部的,以任何方式改变了这个对象的任何事件。……行为(behavior)是指一个实体相对于其周遭环境的任何改变(change)。……一个对象的能够从外部所能检测到的任何改变(modification),就可被称作行为。——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BPT将行为定义为一个与其他因素相连的过程,而非孤立的对象,文中的行为学方法只通过「输入-输出」这个过程去了解系统的规律,一定程度上忽略系统内部的结构。这里维纳已经开始将电气工程师的思维和心理学的理论框架结合,更加严格的定义「行为」的概念了。
工程师是实用主义的,关注的是可行性(viability),也就是how,而不是what。因此BPT忽略了进行过程的实体的功能属性,通俗地说,就是不去探究对象是人、还是机器或动物等其他实体。这个被忽略的方法也就是文中所说的的「功能性方法」(functional method)。
用系统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功能性方法关注系统的内在组织,而行为学的方法关注的是系统与其边界之外系统的动态关系。
BPT中的这种行为学方法,隐含了一个认知框架:一个和做出行为系统共处同一时空的外部视角——是它观察到这个系统的改变。所以维纳是在更广阔的物理学坐标系中考察心理学中的行为概念,因此他的定义也更抽象,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具体内部细节。
总的来说,BPT定义了一个动态过程的基本单元。维纳把托尔曼的「刺激-中介变量-反应」,转换成了「输入-实体-输出」。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中,维纳这样描述输入-输出关系:
输入-输出关系在时间上是一种连续关系,并且具有确定的过去-未来次序。 ——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1948
一个超越了行为主体性质的分析框架就基本建好了。
BPT中的行为学方法,后来在控制论中被称为「黑箱认识论」。「黑箱」也是一个工程师常用的概念。简单的来说,就是坚信在输入和输出之间有一种起作用的机制,只是它隐藏在一个暂时还无法观察到的系统之中。
在早期控制论者、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那里,这又被叫做「解释性原则」(the explanatory Principle),指「科学家之间的一种约定俗成,用来在某个点上停止试图解释事物的行为。」(心灵生态学导论,2023)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就是一个在科学认知层面的黑箱。上文中皮克林提到的和世界互动的「述行式」(performative)方式也是建立在这种「黑箱认识论」基础上的,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对世界复杂现象保留鲜活感的科学认知方式。
而比较晚进的控制论学者则从认知科学角度进行阐释,比如拉努尔夫·格兰维尔(Ranulph Glanville)就认为「黑箱……是观察者在观察到变化之处进行的思想实验,目的是探索这种变化。」(激进建构主义 = 二阶控制论,2013)黑箱并不真的存在,它只是人们为了解释行为变化的规律性进行的一种认知建构。但不同于工程师的是,控制论认为黑箱终究是不可能被打开的,因此这种规律性也不是黑箱本身的属性,而是观察者根据输入-输出进行的自我建构。
BPT在上述基础上,构建了一种分类法,一步步聚焦在所谓的具有预测性的目的性行为之上。下面让我们一层层的展开这个分类。
3.第一层分类
3.第一层分类
主动行为(Active behavior)是指在给定的特定反应中,对象是输出能量的来源。……在被动行为(passive behavior)中,对象不是能量的来源。——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第一层分类给了主动和被动一个相对客观的区分,标准并非来自主观意图的判断,而是按照能量的来源。这里其实可以看到工程师思维的影子,也就是考虑过程中能量的来源与流动。主动行为的能量不是从系统外部输入的,而是系统内部供给的,也就是说在和该行为最相关的时间序列中,能量只参与系统内部的循环。
4.第二层分类
4.第二层分类
主动行为可以细分为两类:无目的的(purposeless,或随机的 random)和有目的的(purposeful)。——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第二层分类是对主动行为的再次划分,并开始引入「目的」的概念。但这里的目的仍然不是主观的。那么BPT是怎么定义「有目的的」(purposeful)呢?
「有目的的」是指该行动或行为可被解释为导向一个目标的达及(directed to the attainment of a goal)——即,指向一个最终状态(final condition),在此状态下,行为中的对象达到了一个明确的与另一个对象或事件在时间或空间上的相关性(definite correlation)。——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BPT没有将目的定义为对象的主观意图,或一种先验的神秘力量的内在状态,而是一种外在状态,即「行为中的对象达到了一个明确的与另一个对象或事件在时间或空间上的相关性。」要用上文提到「外部观察者」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句话:要注意是谁,在什么情况下描述了这个状态?答案只能是和行为中的对象同处于一个时空系统中的另一个对象,在这篇文章中指的是三位作者,也指所有观察到对象的行为的人。所以BPT对目的的定义是纯粹外部的,也就是说文中考量的是「黑箱」输出了什么以及如何输出,这让目的被形式化了。
目的(purpose)概念的基础是对自发性活动的认知(awareness of voluntary activity)。现在,自发性行动的目的不是一个武断解释的事,而是个生理学事实。当我们进行自发行动时,我们自发选择的是一个特定的目标,而不是一个特定的运动。——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BPT进一步阐释了「目的」和「行动」的关系:目的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先验终极,而是需要从非常形而下的,具体的生理学意义上的行为单元来考虑。
文中用喝水来举例:
如果我们决定拿一个装水的杯子并把它送到我们的嘴里,我们并没有命令某些肌肉以特定程度和特定顺序收缩;我们只是触发一个目的(trip a purpose),而反应随后自动出现。——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也就是说,在一个行为的时间序列上,目的先于动作出现。先触发了一个目的,然后才有了一系列动作完成该目的。这并非一种假设,而是一个神经生理学的事实,在1943年前就被发现了,但当时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
如今的神经科学和脑科学更近一步了,但也没有完全统一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本杰明·李伯特(Benjamin Libet)的「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认为,在人们报告自己有意识地决定进行一个自发动作(如屈腕)之前,大脑中就已经出现了缓慢的、持续的电位上升。更新的解释认为,自发活动是受大脑随机神经噪声影响的。
这个问题的如果继续再追问下去,很容就滑入关于自由意志的终极命题上了。例如人类的能动性从何而来?你做出的每个行为到底是自主的,还是完全随机的,或者是被其他因素影响的,或者是完全被决定的?但是BPT显然不打算这么做,维纳仍然希望将其限制在行为主义的科学框架中严格讨论,也就是说,不去追究是否真的自发,而只是通过「外部观察」判断是否在主动追求一个目标。
对目的机制化,而非本体论的判断标准带来了一个结果,「有目的的」这种曾经只能用来描述自然造物的词语,也可以被用来描述人造物了,例如机器。
紧接着,文中提到:
伺服机制(servo-mechanisms)这一术语正是为了命名具有内在目的性行为的机器而创造的。——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也就是说,不论被观察到做出行为的东西它是由什么材料所造,如何被组织起来。只要它在输出上能被观察为「有目的的」就可以——即达到了一个明确的与另一个对象或事件在时间或空间上的相关性。可以说,伺服机器是控制论分类下行为主体的一种具体形式。
我认为,对于是否有目的的判断,其实是一个观察尺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观察者的尺度上,对象的目的是否内在于观察对象的系统边界中。例如文中提到的轮盘赌,它作为单个的轮盘赌,本身当然是无目的的随机机器,达不到一个明确的时空相关性。但是在整个赌场这个更宏观的尺度上,轮盘赌的低尺度随机性,反而能达成赌场尺度上收益的确定性。
再比如导弹,在其自身的尺度(系统边界内)是有目的的,其系统动力指向一个明确的打击目标。但它也可能在整场战争中成为某种随机因素,可能无关紧要,也可能决定战争走势。这里更关键的是决定一颗导弹的目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过去,「伺服机制」经常被称为是自动化的同义词,但现在可以这样重新描述它:在自身系统边界中,依靠自身系统动力达到对特定目标时空相关性的机器。
再回到BPT的分类法,「目的」在其中被彻底去魅了,它被摆上了科学的手术台,同样被摆上来的还有(旧)哲学,也就是关于认识人类自身的古老学科。
这里稍微提一下后续的二阶控制论的对哲学的态度,二阶控制论绕过了诸如关于自由/决定,主观/客观的二分法这些哲学终极命题,代之以系统内与外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动力。例如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就用系统/环境的区分,取代了主观/客观的区分,而所谓客观只是因为观察者在被观察系统之外,或者它在被观察系统内但不处于决定系统动力的循环中。
4.第三层分类
4.第三层分类
有目的的主动行为(purposeful active behavior)可以细分为两类:反馈的(feed-back,或目的论的 teleological)和非-反馈的(non-feed-back 或非目的论的)。——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第三层分类是对于「有目的的主动行为」的进一步划分,并开始引入「反馈」的概念。此处以及之后的控制论中的反馈主要指「负反馈」(negtive feedback)。这里的负反馈和日常语言中用法的不同,日常语言中强调负面的回应,而在本文和控制论中主要是指修正相对于目标的偏差,文中这样表述:
一个对象的行为由该物体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参考一个相对具体的目标所处的误差范围(margin of error)所控制。——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BPT通过对目的和行为的前置定义,将「反馈」从工程学术语转变为一个普适的科学概念。
BPT将有目的的(负)反馈看做「目的论」的同义。这里的「目的论」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里的「目的因」,指事物存在的根本原因,蕴涵在事物自身中,这意味着事物未来可能成为的最终状态决定了事物现在的状态,即一种未来决定现在的线性因果论。而文中使用「目的论」,只是借用了其原意中时间上「未来-现在」的时序关系,但是排除了其中蕴含的必然性和终极性。
BPT通过将「目的论」精确地定义在行为分类框架里,使目的论的行为只意味着「由负反馈调节的行为」。虽然维纳认为与此相关的哲学讨论超出了文章范围,但是引入目的论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决定,不论如何,BPT都由此搭接到哲学话语上了。
再来看看后来他在《控制论》中,更精确的定义了这种普适概念的反馈:
反馈:当我们希望一个动作按照某个给定模式来进行时,给定模式与实际完成的动作之间的差异,被用来作为一个新的输入,以调整动作出现差异的地方,使之更接近于给定模式。——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1948
「目的」在这句话中被描述成「希望一个动作按照某个给定模式来进行」。它不是一个事物存在的终极因,也不是用来描述特定类型对象的演化规律,而只是一种和反馈的动态时序过程相关的参数,系统依照它来进行反馈,修正自己的行为。
这就是控制论最著名的图示:输入输出的反馈循环。
反馈循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控制」或者操控,因为它既非强制,也不意味着必然性,它只是一种指向某种时空状态的动态调节,或者说是对外部信号的适应。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真正的控制论者(cyberneticist)认为「控制论」是一个糟糕的中文翻译。即便不考虑cybernetic后来在社会学科中延伸出来的人文意涵,这也和「调节」的本义有出入。
具有反馈机制的机器,很早就在工程领域出现了。18世纪发明的瓦特蒸汽机中的离心调速器(Centrifugal Governor)就是一种机械反馈装置,它通过机械结构自动控制蒸汽机进气量实现转速稳定,转速通过连杆「反馈」回去,直接调节蒸汽阀门(输入)。而按照机械和生物的二元分类法来看,机械反馈的另一端是生物反馈,例如上文中提到的喝水动作。
在两者之间是维纳在1940年代末制作的「夜蛾机器人」(Palomilla),机器人模拟了昆虫的行为,配备传感器、电路和电机,可以根据光源「有目的地 」,也就是「反馈」地在空间中导航。那么维纳为什么不设计一个能被精确控制机器工具,而是要创造一个更像某种生物、行为具有一定随机性的东西?因为他想显示有目的的反馈行为是不论对象的具体功能结构的,BPT的行为学方法分类是超越了有机和机械二元论的。
既然维纳只强调了负反馈,那么为什么还说他的反馈概念是普适性的呢?因为他所定义的反馈过程,也就是输出作为输入返回对象这个过程本身是不分正负的,不论正反馈还是负反馈,都要经过这个循环的过程。
行为也通过该循环有了能被数学化的可能。既然目标和现状之间的误差是可测量的,那么「有目的的主动行为」就是可测量的,「目的」就是能被数学描述的,不论是对有机体还是机器。
「反馈」也因此成为了理解系统动态行为的关键机制,用来考虑单个系统的动态循环。系统的输出既直接进入环境,也返回到系统自身,上一个时间点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下一个时间点的原因。这即使不是严格对应的因果,至少也是具有强相关性的影响因素。虽然在日常的时间中,人们可能会感受到前因后果这种线性的因果关系:这一刻的因可能是过去某个时间的果,这一刻的果可能是未来某个时间的因。然而一旦将一个系统及其本身的行为作为一个观察单元来看,那么所观察到的就完全是一种循环,系统自身动力的闭环。
这种反馈机制和循环因果就是控制论的核心。如果看一看梅西会议,可以发现第一到第五次会议的主题就是「生物和社会系统中的反馈机制和循环因果系统」,而在《控制论》一书出版后的第六次会议,控制论成为了主标题,先前的会议主题变成了副标题。
出版这本论文集的圣塔菲研究所是著名的跨学科研究机构。而梅西会议可以说是圣塔菲之前最重要的跨学科事件了。梅西会议由小约书亚·梅西基金会(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赞助,起初是纯医学领域的交流会议,但在后来演变成了跨学科研讨会,现在说的梅西会议一般是指1946年-1953年的十次跨学科讨论会。梅西会议可以说是在现代科学分化成各学科后,「软科学」与「硬科学」的首次激烈碰撞。
会议的议程设置和人员邀请主要由主席沃伦·麦卡洛克(Warren·S·McCulloch)负责。具体来说是在每个学科都至少邀请两名学者,为了他们可以彼此交叉印证。而且讨论时的每一个话题,都会经历双重讨论(dual treatment),就是让来自硬科学和软科学的科学家相互类比和讨论。
很多人都知道,圣塔菲研究所形成了很多研究工具和成体系的理论,并且有长期的研究组织。相比之下,梅西会议更像是一场即兴而猛烈的科学事件,除了控制论外没有可复现推广的理论成果,也没有建立长期机构有效融入科学体制(美国控制论学会只能说部分继承了其遗产)。而且其实就连控制论本身也是非常混杂而且边界模糊的学科。反而是梅西会议上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的交锋甚至是争吵,这种碰撞方式本身的独特气质,更为人所乐道。
很多参会者都觉得会议的内容很难被总结和评述。麦卡洛克在最后一次会议的发言这么说:「我们所达成最显著的一致意见就是,我们学会更好的了解对方,并且身着衬衫公平的彼此争斗。」(前九次梅西控制论会议达成的协议要点总结,1953)
虽然如此,但BPT中提到的反馈模型却通过这次会议,迅速的被其他学科所接纳,其中有工程学和硬科学,但最主要的还是向社会科学。这是一种非常有解释力的认知模型,可以在不同的领域间通约,例如人体调节体温的过程是关于通过感觉器官对传入的环境温度的反馈循环,而经济系统中价格的浮动是系统接收到了关于供需关系的反馈形成的循环等等。
其实BPT还是没有说明调节反馈的「目的」到底从何而来,具体来说可以是人类的适宜体温范围的「目的」从哪里来?经济体中导致供需关系变化的期望从何而来?维纳适可而止地没有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仅仅止步于行为学定义带来的操作性便利上。但是他已经为复杂系统的动力学埋下了一颗关键的种子。
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是一个更高尺度的问题,也就是一个更庞大更复杂的系统动力问题,在不同尺度间流动系统动力是否有始有终?这也是圣塔菲的复杂科学中关于模式和涌现想要探究的问题之一。
此处就不做太多的探讨了,文集中的文章和其他分享者都会有很好的讨论。
6.第四、五层分类
6.第四、五层分类
有目的的反馈行为可以再次被细分。它可能是外推性的(extrapolative, 预测性的 predictive),也可能是非外推性的(非预测性的)。……预测性的行为可以被细分为不同的等级。猫追老鼠是个一阶预测(first-order prediction)的例子;猫只是预测了老鼠的路径。而向一个移动的目标投掷石头需要二阶预测(second-order prediction);目标和石头的路径应被预见。——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第四层和第五层分类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它们已经开始涉及对复杂行为的洞察。外推性的有目的反馈行为不只考虑自身和目的的关系,而且在时间序列中考虑自己与环境,也就是环境中其他对象和系统的关系。能作出这种行为的对象,有能力处理多种输入,而它对未来的高阶预测也正是基于此。最重要的是,该对象会根据预测提前做出行动。
说到这里,可以稍微展开谈谈前面提到过的维纳和毕格罗在二战时期的防空火炮研究了。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一套控制火炮系统的方法,让火炮能具备一定程度的自动化能力,迅速响应雷达目标,精准击落敌机。直到1942年,最终的样机能够把10秒到20秒内观测到的目标飞机的位置信息,转换成一系列电子信号,并计算出未来某一特定时刻的位置。但维纳过于追求预测的精准性,再加上当时的技术水平限制,最成功的一次试验,样机最多只能提前半秒预测飞机的位置,但这在实际应用中远远不足够让火炮响应。这也导致系统最终没有投入使用。该研究最后形成了一份报告,《工程应用中的外推法、内推法和平稳时间序列平滑法》(extrapolatlon, interpolatlon, and smoothing of stationary time series With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内容主要是将统计学中的时间序列分析与通信工程相结合,提出一种数学方法。该报告1942年由维纳提交给军方,因为涉密,直到1949年才出版。
在这两层分类中,BPT将预测这种高等动物的行为科学化了:即目标导向在时间序列中对行为进行持续的反馈和修正。维纳将预测变成了一个统计力学问题,他在后来的控制论中说,预测是关于「许多动力学系统的统计分布」。可以看看维纳在《控制论》中用非常有趣的数学方式描述捡铅笔的过程:
捡起铅笔……一旦我们对此做出了决定,我们的动作就这样连续进行下去,这种方式可以粗略地表述为,每个阶段铅笔还没有被捡起的量都在减少。——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1948
维纳认为,在触发了一个目标后,人的身体就会自动做出预测和修正,去达成这个目标。在捡铅笔这个比较简单的动作中,达到未来的目标似乎是必然的。因为该行为相对于人类预测能力的复杂度来说,是很低的。但是对于更复杂,影响因素更多的事件的预测呢?
BPT随后概述了决定预测复杂度的生物学限制条件:
生物体的感觉接收器(神经末梢,receptors)或机器的对应元件可能会限制预测行为。……中枢神经系统的组织,决定了哺乳动物可能达到的预测行为的复杂度。——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预测行为的复杂性,取决于做出预测的对象自身的感觉子系统的限制,处理信息的能力、建立复杂连接通路的能力,决定了能处理参数的数量。人类的神经是无差别编码原则的,接受到的信息是多种感觉器官的编码的复合,让人能够有进行「相当高阶」的预测行为。这里隐含了一个推论:能接收和处理的信息越多,预测行为也就越趋于准确。要注意的是,此处只能表述为预测准确的可能性更高,而不是必然。
但是如果要预测的对象远超过人类自身的所能处理的复杂度,例如社会系统,结果会怎样呢?维纳认为几乎不可能做出完美的预测,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根据过去进行统计,预测出未来最可能的值。
我认为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是量子力学的世界观,世界的底层是随机的,因此无法通过观测获得全部的信息:
没有任何一组可以设想的观测,它能提供我们关于系统的过去的足够信息,而这些信息能提供关于系统的未来的完全信息。——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1948
第二点是统计工具方面的,需要合理可靠的常用数字技术。也就是说如果要实现社会尺度的预测,需要对于精度和响应速度要求都极高的统计工具。而统计工具是受到材料属性和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等基本的因素制约的。但是现在数据处理的速度和量级都在提高,各种模型层出不穷,人们对于预测未来的热情又被激发了。这似乎就是控制论近些年又被重提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新版梅西会议文集的编辑者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认为控制论这种预测未来的方法和愿景,是被重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也认为这是一种「幻想般的过度信念」。
控制论的持久遗产正是这种幻想般的过度信念:即对未来的控制,通过有针对性地控制其某些方面。——控制论时代,2016,Claus Pias
控制论本身从未许诺完美的预测和控制。维纳只谨慎的提到「按照各种不同目的,调节其各个组成部分,以遏制秩序紊乱的自然倾向」。将控制论工具化,满足人类对复杂世界的控制欲,映射出人们对未知的永恒焦虑。这和控制论的述行式认识论,即与未知共舞的前瞻探索式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7.取代「旧」哲学的科学
7.取代「旧」哲学的科学
最后谈谈本次分享的标题,取代「旧」哲学。
这其实是海德格尔在1966年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提到的:「控制论取代了哲学」(takes the place of philosophy)
《明镜》:那么现在,什么取代了哲学的位置? 海德格尔:控制论。 《明镜》:或者是虔诚之人,保持自己敞开胸怀。 海德格尔:但那不再是哲学。 《明镜》:那是什么呢? 海德格尔:我称之为另一种「形式的」思考。 ——Only a God Can Save Us,1966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已经终结,因为它无法让我们在思想中体验正在开启的技术时代的基本脉动。但是海德格尔也直言自己无法阐明这种新思想,他坦白自己对技术的无能为力。
这一部分是因为控制论在技术方法上完成了哲学的很多任务,圣塔菲这套文集的第三辑里关于非线性动力学和控制论的部分,很多话题都是曾经海德格尔时代曾经的的旧哲学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控制论根本没有思考哲学,它只是从最形而下的技术去向上反思追溯,但确实终结了这样的哲学思维过程:预先设定有一种抽象的「形而上」,或者说先验规则,然后通过不断认识具体的特殊现实,也就是经验,来返回「形而上」。
因为控制论展示了一种既是纯粹具体的又是纯粹概念的反馈循环过程,这使哲学的抽象推论和演绎彻底终结。它从最初(也是最终)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合一,它即是最纯粹的自身,控制论在形式上完成了哲学的任务,但却与哲学的概念无关。所以说,控制论作为一种新的「科学」取代了旧的哲学。
维纳在BPT里无意讨论哲学,但他确实从根本上解构了哲学思考。他用工程师的方法对待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特征的心智,将其去神秘化,形式化。「心智」和「精神」被放在了工程师的桌子上。
之后,人们将控制论反馈循环的方法论发展成一种社会、经济或政治控制/干预手段的模型,用来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套模型最初的构成,除了BPT和控制论之外,还有皮茨(Walter Pitts)和麦卡洛克的神经元模型的逻辑运算;以及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论。现在历史研究表明,他们三者都和梅西会议甚至维纳本人息息相关。
现在我们用更复杂的模型来模拟真实世界的复杂性, 从数学到物理学再到经济学、社会学。从各种意义上来说,现在都是一个模型的时代了,各种模型算法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关于模型和它模拟的东西之间的关系,BPT中有一点洞察:
一只猫的最终模型当然是另一只猫,无论它是仍由另一只猫所生或是在实验室里合成的。——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这句话在原语境中更多地指所建立的模型是有机的还是人造并不重要,但前半句让我想到了比维纳小五岁的作家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论科学的精确性》,讲的是一个国家为了精确的呈现国土上的所有事物,制作了一张和国土面积等大的地图(用维纳的话说也就是,一个疆域的最终模型当然是另一块完全相同的疆域)。人类当然无法使用如此尺寸的地图,所以这张地图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BPT成文的时代,人们无法想象数字模拟技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对于数字地图来说,尺寸已经不是问题,但人们对地理信息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了,从前的地图比如水文图、疆域图、等高线图、建筑图、商业分布图……每一张单独的地图都是对于某一类信息的建模。现在的数字地图把他们都整合在一起,而且还附加了基于定位的实时性,并能够基于历史数据做出某种预测,例如导航的预估时间就是一种最简单的预测。
这样的地图对于人类来说,问题或许不在于尺寸,而是复杂度。它的信息维度越逼近真实世界,它的复杂度也就越接近世界本身,相应地对于人类自身,它就越难以理解。
或者再推进一步,假如能有完全处理世界复杂性的模型,也就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模型,那么人类要如何理解它呢?它对于人类自身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存在的意义当然是用来模拟和预测,但相应的,我们也需要新的工具和媒介去完成人和模型的交互。从以前的图例指引到现在的大模型,工具本身的复杂性也在增加,虽然工具处理信息的量级和频率增加了,但是人能处理的信息维度是有限的。我们终究还是要在人的尺度上思考怎么面对复杂性,也就是人在面对复杂的世界时目的是什么,期待什么样的未来。
这恰好对应海德格尔对控制论的另一重担忧。他认为,控制论反馈循环「系统」是「方法的胜利」,即「实验中可获知和可验证的所有内容的全面可预测性」,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可计算性。在这种方法中,未来作为一个「降临到人类」之物,必然在现在到将来的过程中被计算耗尽。
这种担忧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还是要面对那个终极问题:人自身的「目的」是什么,人怎样筛选输入自身的信息,做出怎样的选择。另一方面,这种建模方法也给人类处理自己这个复杂系统提供了工具。它带来一个额外的作用,那就是人类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信息机器」。
福柯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提到「人类被抹去,就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The Order of Things, 1970)这里的他不是悲观的,他只是认为「人」的概念是一种现代知识构造,而随着知识型的再次变革,这个以「人」为中心的认识论框架将会崩溃,被新的、可能不再以「人类」为主体/客体的思想形式所取代,例如一种基于二进制的信息本体论。
控制论在这种认识论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维纳在1950年这样说道:「我们(人类)无非是川流不息的江河中的漩涡,我们不是固定不变的质料,而是自身永存的模式。」这意味着传统的、功能性的对人类的定义方式,在控制论的视角下不再适用了。「人」的概念可能只是基于信息循环和动力的一种模式,至于实际组织和结构、物质构成是什么,很有可能都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这就是从BPT的分类法中延伸出的本体论问题。从这里开始,关于人的本体论、甚至存在的概念都从根本上被颠覆了。
旧哲学除了思辨世界规律和人类自身外,还有一部分是承担寻找人类意义和道德准则的。那么在计算的时代(也是文集第四辑的标题),我们要怎么寻找这部分?
这里就要引出二阶控制论了。二阶控制论最早是作为对控制论自身的反思出现的,提供关于反思的反思。
控制论者由于进入了他自己的(控制论)领域,就必须对他或她自己的活动做出解释。于是控制论就变成了控制论的控制论,或二阶控制论。——Heinz von Foerster, Ethics and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1991
总的来说,二阶控制论通过递归观察、递归认知的现象,提出了很多关于意识中自指和悖论的课题。但是因为研究经费和地缘政治等原因,二阶控制论研究的中心,冯·福斯特创立的伊利诺伊理工的生物计算实验在1974年关闭了,这部分内容很多,在这里先不展开。
虽然二阶控制论的出发点是硬科学的,但是它的研究没有走计算和工具化的道路,而是用一种相对更社会科学和人文的方式,这与梅西会议后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二阶控制论有时呈现出「旧」哲学中寻找人类意义和行为准则的特征。
冯·福斯特认为,控制论是「观察者通过规定系统的目的进入系统」,二阶控制论是「观察者通过规定自己的目的进入系统」。既然这样,你的每一个行为都会通过不同尺度的反馈产生后果,有一些是作用到你自身上的,有一些是作用到其他系统上的。这样一来,你的选择就会催生出新的规则,而这在更大尺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全局规则的涌现。
归根结底在于,你作为人该相信什么?相信哪种规则?哪种道德?冯·福斯特认为,你要做的不是去相信某个形而上的规则,而是相信你所选择的,并且选择你所相信的(这里体现为一种知与行循环)。最重要的是,你要为此负责。
人的目的就存在于行动中,不存在旁观者,每个人既是行动者,也是自己的观察者。不论远近,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在复杂的系统动力中反馈到自身。所有人都是置身事内的,所以不要用客观性去逃避责任,奖励和惩罚都寓于主体行动的自身之中。
问题不在于真理,而在于相信。——Heinz von Foerster, Ethics and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1991
最后让我们回到维纳和他的控制论,其实上述这种人文考量是控制论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控制论》出版两年后,维纳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该书的大致内容和控制论差不多,只是去掉了其中比较技术和数学的部分,更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并且提醒人们关注以控制论为基础的延伸思想所带来的后果。
格兰维尔认为,维纳先出版《控制论》后出版《人有人的用处》,是一个巨大的战术错误。因为控制论技术性过强,先入为主的引导人们把这当成一门技术性的学科,而忽视了其中的哲思和人文关怀。
其实维纳自己也知道自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控制论中自动化和有效控制那部分知识实在太有效了。就连维纳自己晚年,也在反对产业应用所带来的失业等社会影响。经典控制论造成了这些影响,但这不是以维纳为首的控制论者们的初衷。
我认为,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看,《人有人的用处》更有现实意义,虽然书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现实。维纳在本书中所体现的的价值观,底色悲观但是仍有向死而生的优雅姿态:
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我们都是这个在劫难逃的星球上的失事船只中的旅客。但即使是在失事船只上面,人的庄严和价值并非必然地消失,我们也一定要尽量地使之发扬光大。我们将要沉没,但我们可以采取合乎我们身份的态度来展望未来的。————Norbert Wiener,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1950
以上就是全部要分享的内容,谢谢。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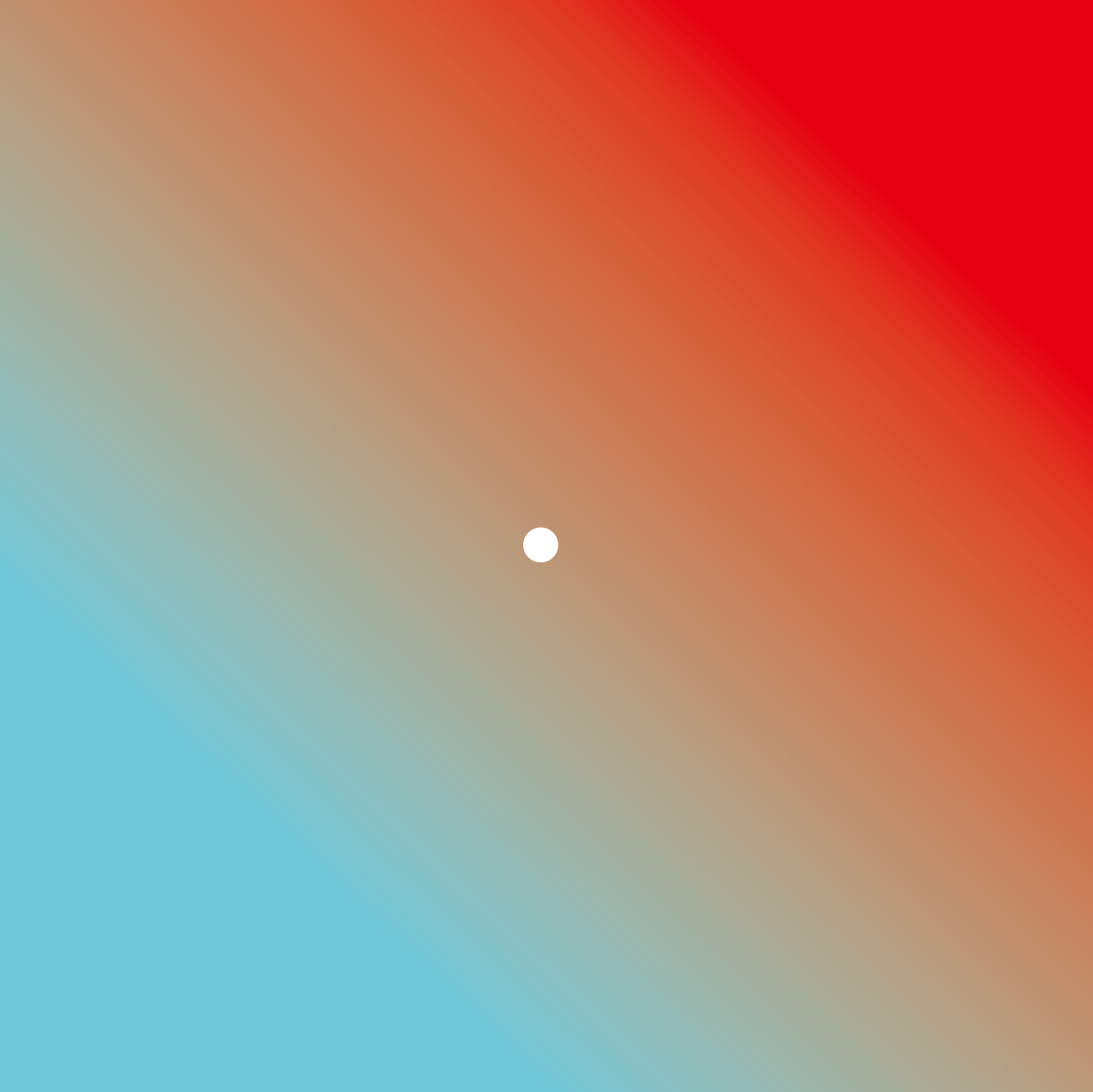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