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雅克·桑贝:最后的晚餐,像猫一样温柔
巴黎的黄昏笼罩在薄雾中,城市到处是零散信号般的灯光。画面中央,有一位披着旧大衣、双手扶栏、眼望远方的老人;在这硕大的画面中他看起来是那么普通,可在这忙乱的城市背景下,依旧扎眼——高楼大厦伫立天边,街上人来人往吵闹;他一个人形单行,简直就是两个平行世界。

sarahasfliedalready
2025-11-05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巴黎的黄昏笼罩在薄雾中,城市到处是零散信号般的灯光。画面中央,有一位披着旧大衣、双手扶栏、眼望远方的老人;在这硕大的画面中他看起来是那么普通,可在这忙乱的城市背景下,依旧扎眼——高楼大厦伫立天边,街上人来人往吵闹;他一个人形单行,简直就是两个平行世界。
让-雅克·桑贝的画就是如此,他习惯用钢笔线条勾勒出城市闪过的瞬间,捕捉日常生活的疏离和心底的渴望。在幽默与温柔中,突出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一种荒诞现实。
从童年的困苦到漫画巨匠,桑贝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创作热情,这本《稳住,别慌》作为他离世前的最后一本代表作,高度浓缩了人性、社会洞察力,赋予每个微不足道的瞬间以永恒,必定是他的遗产最佳注解。在疫情期间上市,这本书也引领着人们在混乱的当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航向。
画:逃避与自愈
画:逃避与自愈
桑贝的幽默向来非单一的搞笑,我常会觉得他很适合说一段脱口秀。这种风格是对存在主义的视觉回应,在《稳住,别慌》中尤突出,插图与文字在看似凌乱的背景中,结合传递出冷静而温暖的信息。即便身处大浪潮的不确定性之中,你依然可以在见微之处找到具体的方向,这样亲切的语言唤起对自我与世界的重新认知。
就像很多喜剧演员并非如台上快乐一样,桑贝的青少年深受家庭影响。父亲酗酒,母亲情绪不稳,总发生争吵。 他在学校时喜欢恶作剧,十四岁时就被开除,不得不挨家挨户卖牙膏、给酒厂送酒来打工谋生。18 岁开始创作各种幽默漫画,第一位青睐他的买家是《西南报》。
他曾说,最开始是为了“描绘快乐的人而作画,后来他把绘画当作“逃避与自愈”的手段,因此 “疗愈”的动机贯穿在他的作品始终,当然也包括这本《稳住,别慌》。书中许多场景捕捉了普通人在琐碎困境中“坚持保持方向”的韧性,也是桑贝从小便在贫困中“坚持守住航向”的力证。
“我们希望有所改变,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又希望保持不变。考虑到您创造的世界如此复杂,甚至如此混乱,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
从 18 岁到《稳住,别慌》
从 18 岁到《稳住,别慌》
这本《稳住,别慌》虽不是专门描述童年的一本漫画,但整本书的幽默所透露出的“忧郁讽刺”均来自桑贝的“童年”,源于他早年惯于“逃避现实”的本能,强调“永远保持孩子气”才能持续创作的理念。
《稳住,别慌》的这种基调,间接疗愈并呼应了他那不算多么幸福的童年。
《小尼古拉》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世界经典童书,于是桑贝开始独立出版个人作品集,并为《纽约客》绘制海量封面。
此时他的线条更具表现力,人物细节更加丰满,场景转向巴黎城市与小镇,进入高远视角的社会观察。漫画的发生地从室内走向街道,包括资产阶级的琐碎生活尴尬等,愈发成为面向成年人的幽默。水彩笔触带来了温柔的氛围感,依旧保持极少文字的视觉语言。
从 1980 年代起,桑贝开始成为享誉国际的艺术家,1988 年与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合著了《Catherine Certitude》(中文译名:戴眼镜的女孩);1991 年为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Herr Sommer 的故事》绘制插图。
此时的桑贝由于常年受到热爱音乐的影响,他的绘画作品变得更有节奏感,已完全是成年人的自省。
晚年代表作便是这本《稳住,别慌》,收录近期未发表绘图,主题聚焦当代法国城市生活,如空荡教堂、老式剧院、艺术画廊与心理咨询师等场景,描绘出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甚至很少出现现代元素(手机或互联网),依旧是“光荣三十年”的怀旧。
《稳住,别慌》是桑贝漫画作品风格的集大成,笑点更加持久回甘,比起之前的几本代表作更静态,场景梦幻宏大而人物抽象。从 18 岁的素描到这本《稳住,别慌》的坚守,桑贝永恒不变的是:小人物在广厦间的渺小滑稽,温柔中暗藏对平庸、愚蠢的批判讽刺,幽默引发阵阵苦笑,是对生活的温柔思考。
松散的主题,随意非线性浏览。从个体到集体,关于时间与荒诞的哲思,没有明确以章节划分每个段落,不列出漫画的标题,是自然呈现出来一种音乐式的节奏感,每幅图与其前后呼应,形成微妙的对话。
“我们从阿索斯山给你们带回来了几只蚂蚁。”
“嗨,阿喀琉斯!近来好吗,工作怎么样,家里和孩子们怎么样?脚后跟还好吗?”
“什么?历史课零分?历史才刚开始没多久啊!”
个体与日常
个体与日常
《稳住,别慌》的开篇聚焦于渺小的人类微观体验,主要描绘属于个人的焦虑与孤独,常以单人场景为主,勾勒出正在沉思的人,表现生活的疑虑与疏离感。这部分采用近景居多,人物表情半喜半忧,是对自身的伪装与挣扎。
主题围绕失败的心理分析,桑贝报以温和的嘲讽:患者支吾着无人倾听的自白,幽默含蓄而精妙,我们都可以投射到自身的挫败上。
四年前,您问我:“您希望得到什么?”我回答说我不想得到吸尘器。原本是个笑话,却没把您逗乐。某天晚上,我梦见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有个吸尘器。它开始吸走玄关的各种玩意儿,吸走了客厅、我的太太、我的孩子们,乃至整个公寓。
我惊慌失措地打电话给妮可。她来了,吸尘器不见了。
梦的意思很明确: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从此和妮可过上了美好的日子。不过,我现在需要您的帮助:有天晚上,我又梦见门铃响了,门外还是吸尘器。我没开门。如果它再来,我该怎么办?
一个带有心理隐喻的梦境叙事,表面是荒诞的“吸尘器”,实则层层嵌套失去、逃避、补偿与再临的恐惧。
梦境: 吸尘器 = 吞噬空虚,从玄关(边界)→客厅(家庭中心)→太太、孩子、公寓。 打电话给妮可→ 外部救赎者,吸尘器“消失” = 问题被他人解决。
第二次梦境(重演): 门铃再响,吸尘器再现,但这次没开门→ 恐惧升级,主动拒绝面对。
这段不是担心吸尘器吸走新生活,而是害怕自己发现他人无法帮自己填补空洞;逃避承认那种“完美的日子”只是糖衣。
桑贝不帮助你解决问题,只留荒诞,但你是否看清了自己?
如果是桑贝来回答,大概会:
如果是桑贝来回答,大概会:
“开门。 它只是来收垃圾,你忘了倒垃圾,它当然会按铃。”
吸尘器是我们没扔干净的旧生活,之所以它每晚都来,因为你每天都在制造灰尘。
进入漫画中段,视角转向外部世界,聚焦社会荒谬。桑贝讽刺世俗化的宗教,凸显另一种疏离感。这一部分的构图更广,城市全景展现出人群中的孤独,且最简单的语言描摹出复杂的文本却又精准、荒诞、温柔而尖锐的心理自嘲。
“前几天,女邻居家的一盆天竺葵绽放出绚丽的色彩。我觉得美极了,心旌摇曳:为了修身染性,我重读了保罗·克利'和巴特"。第二天下了雨,天竺葵又呈现出炫目的淡紫色和幻彩粉色、我的邻居读着一本名人杂志,汤姆·克鲁斯、约翰尼·哈莱迪、卡罗琳的精彩人生故事深深吸引了我。
现在我像向修请教神父一样请教您:“您觉得一盆天竺葵里是否有可能藏着魔鬼--有文化的魔鬼”
这段文字表面上是一段闲聊,桑贝被邻居家一盆天竺葵的绽放所打动,进而联想到艺术、名人、修身养性,最终抛出一个看似荒诞却意味深长的问题:
“一盆天竺葵里是否有可能藏着魔鬼——有文化的魔鬼”
先关注下这几位:
保罗·克利,瑞士裔德国籍画家
罗兰·巴特,法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
约翰尼·哈莱迪,法国摇滚巨星
这几行文字完成了一个从美学 → 伪修养 → 消费主义 → 存在焦虑的心理斗争
- 视觉冲击天竺葵 → “绚丽”“炫目”“幻彩”
- 精神升华为“修身” → 重读克利与巴特
- 世俗回落第二天看名人杂志,被汤姆·克鲁斯等人吸引
- 哲学叩问一盆花里是否藏着“有文化的魔鬼”?
桑贝写出的心理状态是矛盾:
想“修身” → 却被通俗名人杂志吸引 → 最终怀疑花里有“有文化的魔鬼” → 既恐惧诱惑,又渴望沉溺,典型的是一种自厌:明知消费文化低俗,却无法抗拒;明明想追求美,却怀疑美本身有毒。
“有文化的魔鬼”是浮士德式交易:以灵魂换取知识/美感/快感,披着文化外衣的消费主义
- 是艺术史(克利)
- 是符号学(巴特)
- 是流行杂志(汤姆·克鲁斯)
- 最终泛指藏在一盆花中
魔鬼不再是中世纪的撒旦,它们不再需要契约,只需让你看见美,让你想拥有,然后自我折磨。
那么一盆天竺葵里是否可能藏着有文化的魔鬼?
当然有,而且它已经住进去了。
它不是撒旦恶灵, 却是一种精致的诱惑: 让我们在欣赏美丽生活的同时, 怀疑着自己的品味、 消费修养、 最终在“美”中迷失。
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你明知是魔鬼,却仍想每天去看它绽放。这是真正的定义“有文化”何为的魔力。
“美是魔鬼的糖衣, 我们这些自诩有文化的人, 早已排队张嘴。”
翻开任何一本桑贝的书,包括这本《稳住,别慌》,都会找到这样的温柔之刺—“一朵花,戳穿一个伪装”。
桑贝与超现实主义
桑贝与超现实主义
《稳住,别慌》是桑贝个人艺术遗产的巅峰,也折射出法国艺术中一贯的“存在主义”幽默传统,不限于漫画领域,它是一种对荒诞的温和审视,以微笑安慰绝望。
但桑贝的《稳住,别慌》是“温柔的超现实”,面对巨浪,他选择柔化风暴,注入希望。若布努埃尔如手术刀般锋利,桑贝则如羽毛般轻抚安慰。
2022 年桑贝逝世,遗憾他的音乐梦未圆,每个音符般的线条,是桑贝梦想的落空,也塑造了他的艺术风格:永不消逝的颤音,是对“选择与错失”的证明。
荒诞与坚持
荒诞与坚持
让-雅克·桑贝(Jean-Jacques Sempé),并非依旧以一声叹息的荒诞收场,比起前面所说的吸尘器噩梦、文化魔鬼,或酒馆里人们对足球、政治与爱情的无谓争论,最后一页选择说明:“然而,我们仍在前行。”
画面中央,一棵老树在秋风中凋零,叶子如叹息般飘落;镜头微微拉远,树根旁,一株新芽悄然破土。这不是巧合,是桑贝一生的象征主义巅峰。
以微笑面对失败,从痛苦的内省到欣然接受生活的混沌,将空虚化为希望,鼓励我们在漂浮的世界中前行,正是桑贝的一生。
《他知道岬角并不存在,但仍保持航向》
《他知道岬角并不存在,但仍保持航向》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sarahasfliedalready”
请点击:https://mp.weixin.qq.com/s/zbcyEBA70kr7SmQ-CaWZ-A
喜欢请关注我,欢迎多多打赏支持
更多请点击⬇️
微博 | @sarahasfliedalready
小红书| @sarahasfliedalready
公众号| sarahasfliedalready
I

sarahasfliedalready
3 人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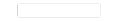
安利大帝
18473 人关注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