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视频版
视频版
文章
文章
《杀出重围:人类革命》其实是《杀出重围》第一部的前传,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时间上承接的关系。那么如果你玩过《杀出重围》一代,你就会在这里面发现很多对于未来的伏笔;如果你先去玩这一部,然后再去玩第一部的话,你就会有那种感觉——它里面提到了很多,比如我们熟知的 Page、VersaLife、纳米科技,尤其是纳米科技在本作里是一个从一开头贯穿始终的伏笔,但是整部作品都没有进行收尾,因为这个尾巴在《杀出重围》一代里。
我是先玩的《杀出重围》一代,再去玩的《人类革命》。但也不用担心,如果没有玩过初代——因为一代太老了——是否可以直接玩这一部?完全没问题。虽然有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伏笔,但大体上,毕竟是前传,所以不影响理解。
另一方面,这一部作品基本是奠定了、确立了《杀出重围》现在的视觉风格和整体氛围的基调。
可以说,这一部定义了系列的“样子”。
这个基调叫“文艺复兴赛博朋克”,官方称作 Cyber Renaissance,也作“Renaissance Cyberpunk”。在附加菜单里的纪录片里开发组也讲到了这一点——它为什么这样叫、设计上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之后会展开聊。
沉浸式模拟
沉浸式模拟
在正式说那个之前,先讲玩法。
玩法上,《人类革命》是一个纯血的沉浸式模拟游戏(Immersive Sim),是我最喜欢的游戏类型之一。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 ARPG,它的大类确实是 ARPG,但它很注重“如何自由运用世界的规则与逻辑”,以实现自由路线选择、战斗方式和任务达成等多样可能性。
关卡设计和系统逻辑紧密结合,所以它被称为沉浸式模拟。如果你玩过《耻辱》或《掠食》,那种感觉你会很熟悉。
这款游戏有大量的植入体,它是一个围绕改造人主题、聚焦人体强化议题的赛博朋克作品。所以装备系统非常丰富。
每个改造功能、每个装备都可能彻底改变你进入一个地点或解决问题的方式。
比如,有的装备能让你直接打穿墙壁,开出新的路,而那条新路里可能藏着一个炮台,可能通往完全不同的空间,也可能是藏有奖励的密道。
再比如,你拥有黑客技能,就可以入侵并接管敌方炮台;如果你还有“搬重物”的负重改造,你又可以把炮台扛起来,当移动炮台用——走到哪、搬到哪。
但如果你没有这些能力,这些选项就不存在。游戏的玩法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非常注重玩家的 play agency——我不知道这个词中文怎么说,也许可以理解为“玩家主动性”。
换句话说,它让玩家自己的决策真正影响角色成长与世界状态。不是那种很多 RPG 那样只是数值高低的差异,而是会改变你在世界中移动和潜入的方式。
例如:你可以跳得更高,或者拥有无下坠伤害的能力,这些都会彻底改变你在空间中的行动逻辑,从而改变你完成任务的方式。
虽然游戏允许正面突击,但整体感觉更倾向于鼓励潜行。不过,你完全可以正面打;很多关卡我都是直接正面打过去的,但我能感觉到游戏在结构上是偏向潜行的。 这种差异完全会改变你“如何潜入目标、如何完成任务、如何进入一个地点”等等。
它给了玩家同时存在的多种手段:绕过敌人、非致命攻击、直接击杀、利用环境致命、利用环境非致命——全都有。什么时候该用致命、什么时候该用非致命,虽然系统会给经验值奖励差异,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
比如我自己,对于我个人的价值观,如果对方是主动使用致命武器攻击我、意图杀我的敌人,而且他显然不是什么“好人”——我就不会刻意去非致命。我不会说,“哦这游戏鼓励潜行,所以我全程非致命”。我不是那种。如果对方是邪恶组织的武装特种人员拿着突击步枪冲我开火,那我也会让他付出代价。
但到了游戏后期,比如那些被精神控制的工人、平民,或者那些并没有恶到那种程度的人,我就会用非致命手段。最后一关我全程都用的是非致命,而且我还特意没有动用任何致命型机器人。虽然用那些机器人可以轻松消除威胁,但我都没有动用。
总而言之,整个流程中你想讲出什么样的故事,完全取决于你选择怎样的角色成长、怎样使用世界里的工具。
当然,本作的沉浸式模拟深度并没有达到后来的《掠食》那种程度。毕竟这是 2011 年左右的游戏。《掠食》那是 2017 年的作品,很多技术上能做到的事情在本作里还不存在,比如通过安保窗的小缝发射泡棉弩,让泡棉弹跳到按钮上触发机关,这种“空间物理解谜”的层次在当时还不现实。
本作中依然存在一些“不是那么彻底”的沉浸式模拟设计,比如:什么能拿、什么不能拿,系统并没有给出解释。你能拿的物件是因为它被高亮了,不能高亮的就不能拿。设计逻辑相对封闭。但在这个既定框架下,本作依然表现得很好。在系统设计上,它可能不如《掠食》复杂,但在关卡引导上,它非常出色。 尤其是在比较线性的关卡里——比如潘查亚设施——我几乎没有遇到卡关。那一关有多条路线:一条地上,一条地下。地下那条有电流阻隔,虽然你有办法解除,但即使你没找到,系统也会用极为巧妙的方式引导你。
它的引导方式不是生化4RE那种生硬的黄油漆,而是通过灯光冷暖对比来实现。暖色的室内灯光与冷色的外景形成冲突,自然吸引你的视线,引导你前进。这样的设计手段非常高明。
说服系统是另一个极有趣的地方。本作不是那种单纯的“点数判定”对话系统。 它的设计非常炫酷——甚至有点高大上。不是“口才+10 就自动成功”那种
游戏里其实存在两种说服机制: 第一种是完全无提示的,你只能凭对话内容去判断、揣摩对方的心理。没有任何技能点修正,也没有附加几率。这完全考验玩家是否能察言观色,能不能揣测人心。
第二种,是安装“社交强化模块”之后激活的高级系统。装了之后,你就会在对话中看到一个分析界面,显示对方的心跳、脉搏、瞳孔变化、嘴型等,通过这些细节分析出他的人格类型——分三种。 然后你在对话中,一边观察哪种人格占主导,一边选择对应的信息素去影响他。这种对话形式不但好玩,而且极具沉浸感——它完全没有脱离剧情,而是融入在人物关系之中。 我认为这是我在游戏里体验过最棒、最有成就感、同时也最酷的说服系统。
所以什么是“文艺复兴赛博朋克”?
所以什么是“文艺复兴赛博朋克”?
说到这里,我们就得说一说本作最特别的地方——它的美术与整体风格。
这一作正式确立了《杀出重围》系列现在大家熟悉的视觉基调:文艺复兴赛博朋克。 什么叫“文艺复兴赛博朋克”?我们都知道赛博朋克里企业强于政府、资本控制世界、高科技搭配低品质生活。而这里的高科技议题主要聚焦在人类改造上。
为什么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代表人类从中世纪宗教至上的状态走出,回归以人为本,夺回个体性、夺回对自身进化与社会进化的主动性。不再把一切交给神权,而是把自主权收回来。整个人类社会在科技崛起下被撕裂成两层——改造人与未改造者。另一方面,它又与传统冷色调、机械感、霓虹闪烁的赛博朋克完全不同。
它的整个气质是暖色调、金色调的,充满古典构图与人文气息。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因为文艺复兴意味着“人类重新夺回主动权”。 在历史上,文艺复兴代表人类从宗教手中夺回对自身命运与价值的掌控,从“神权高于人性”转向“人性高于神权”。
而在《杀出重围:人类革命》的语境里,这个“神”已经变成了自然本身—— 人类从自然进化的轨道中、从命运与生物法则中,夺回进化权与定义权。
人类不再等待自然安排,而是要自己改造自己。 这正是游戏名字“Human Revolution(人类革命)”的含义。 这里的“革命”是人类从自然法则手中夺权。 在这一点上,整部游戏的主题和“文艺复兴”的精神是完全契合的。 过去人类从宗教手中夺回人性,而现在人类从自然手中夺回自我。
游戏中这一象征反复出现——例如你会在办公室里看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是否有权重写人类自身?”
美术上的“文艺复兴”特征就是以人为本的肖像群像、对人体的描绘、人的姿态与神情的刻画——这与游戏要把关注焦点重新放回“人”这个概念是契合的。 灯光的布置是柔暖的,仿佛烛光照在金属上;城市虽然布满钢铁与机械,但有一种近乎宗教画的温度。
人物服饰吸收了大量文艺复兴元素:高领衣襟、硬肩线、皮革质地的镶边; 在赛博朋克的铁灰世界中,重新找回那一点“人”的庄严。
如果你对比初代《杀出重围》,会发现它的美术风格是完全冷色调的——蓝、灰、银、白。 那是一个已经坠入“后人类时代”的世界。
而《人类革命》处在一个转变期,它的暖色调象征文明仍然有温度、仍然挣扎着维系理想。 这个时代的人类刚刚踏入强化技术领域,依旧抱有“技术能拯救人类”的幻觉。 这种暖调不是浪漫,而是一种濒临破碎的理想主义色彩。
配乐上也贯彻这一理念。 Michael McCann的音乐融合了古典合唱与电子节奏。 听起来既像吟唱的赞歌,又像机器的心跳。 这种风格延伸到叙事结构: 整个游戏的世界还没有彻底坍塌,科技与信仰、理想与恐惧同时存在。
你能看到希望、你能看到腐败、你能看到矛盾的信仰并行。 正如历史中的文艺复兴也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一个进行时。
舞台与叙事
舞台与叙事
再说地域与多元化。《杀出重围》系列在地域覆盖上更加多元,不只在美国或欧洲,也去到亚洲。上一代出现了香港,这代出现了上海(虽然我个人觉得游戏里的上海看起来更像香港),但总体上这是个值得肯定的尝试。
游戏在不同地区展示了不同意识形态带来的优缺点:比如在游戏设定里,中国在人体强化和生物技术方面走得更前沿,监管较少,但相应代价也有体现。美国这边有其问题,其他地区也各有问题,整体上呈现的是一个黑暗未来,无论你在哪,都不是美好结局。
关于叙事与结局。我最终的选择是把休达罗的信息公之于众。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为什么?不是因为我认同他的做法——我非常反对他的极端行为,见到他并与他说话后我就把他崩了,为什么要把他崩了,很简单就是他要为这场成千上万无辜者。辛勤劳动的人民的流血死亡而负责,杀他是我能做的最仁慈的事情,我依然秉承这个道理——杀人偿命。但我把信息播出去是为了把真相公布。我相信人类不会因此彻底放弃强化技术,短期内可能会禁止相关研究,但长期来看人类不会完全放弃这种“潘多拉盒”式的技术。我相信,若真相被揭露,尽管不能保证绝对,但更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人类会变得更谨慎。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有玩家会问,既然你想让人类更谨慎,为什么不把光照会或威廉塔格利的信息曝光?因为威廉塔格利代表的那群人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人民无权参与决策,他们躲在暗处不愿抛头露面。社会之所以能有契约和权力讓渡,是因为存在追责机制;若一个组织无法被追责,出事后拍拍屁股走人或把责任推给他人,你怎么能把权利让渡给他们?因此这些暗中运作、无法追责的组织本身就是问题。他们若真是“正确之人”,那么修达罗引发的灾难本不可能发生;事实证明,他们也没有把工具保护好,间接地对灾难负责。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至于沙里夫,他本来给我一种比较负责任的生物科技公司家的感觉,但当他说出“这是必要的牺牲”这种宏大叙事时,我对他的好感大打折扣。所谓“必要之恶”终究还是恶,时代的一粒沙压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那些被称作牺牲的人都有家人、有生命,不能被一句“必要”轻易辩白。因此沙里夫即便并非坏人,我也不再那样尊敬他。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从文艺复兴赛博朋克的角度来看,游戏讨论的是科技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并非简单对立的复杂话题。你的最终选择在这语境下就会不同:是隐藏一切,还是公布真相。我觉得真相隐藏不住,长痛不如短痛,所以我选择传播真相。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很具讽刺意味的是,我最反对的休达罗,最终反而通过我或通过事件达成了某些目标,而威廉塔格利等组织也难辞其咎。休达罗之所以能做出极端举动,不完全是因为他反对强化技术,而是因为他被反噬了:他最初推动这项技术,他的身体状况与研究有关,结果发现自己属于基因不相容的那一批人。
这种被自己发明背叛的感觉是极端的痛苦——类似程序员无意间写了能取代自己工作的 AI,或商人卖出了勒死自己的绳子。修达罗作为强化技术之父,最终被技术抛弃,这种背叛催生了极端仇恨,能理解他为何走到极端。
综上所述,我对本作的叙事与角色塑造持高度评价。我认为它是目前在涉及人类强化、机械化议题上讨论最为深刻的游戏之一。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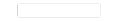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