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作者:wanglingZ1Z
引介
引介
有一种叙述,不为解释,也不为反抗,而只是将目光放在一个地方,让那里的时间自己流过去。
《李师语塾纪行》是一篇以芥川式“低温自我”视角书写的教育纪实小说。作者不设评判,不设情绪,仅以一种迟疑、缓慢、克制的节奏,记录了“我”被送入一处乡村语塾,从试探、卷入,到成为制度的一部分,直至最终被边缘化、沉默而出走的过程。
这是一个关于“声音”的故事:有人领读,有人背诵,有人失声,有人在梦中低语。语言成为纪律的工具,吐字成了集体行为。而那个“我”,既不逃走,也不归顺,只是悄然记下每一次重复的声音、每一页油墨未干的纸张、每一次榜单的张贴与遗忘。那是一个尚未形成意识的自我,仍处于感官的层次,被声音塑形、被气味裹挟、被制度安置,却从未说出“我是谁”。
你不会在此文中读到批判、反抗或救赎的词语。你会读到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安静、变得清晰、变得沉默的过程。正如芥川笔下那些在意识边缘漂浮的人物,“我”从未拥有一整块的命运,而只是在制度机制之间,被一段段语言轻轻撞击、又轻轻带走。
那是一种迟钝的感知力,却是最真实的文学温度。
其一
其一
四月清明前数日,母亲谓我:“吴桥有试,可往。”我不甚知其详,只记得她于手机上翻阅许久,所称者乃一姓李之人,立有一处私馆,名曰“疯狂英语・国学基地”。有传言称,此处所收之童,若循其法习之三月,即有望录入本县重点中学,且无一例外。母未言信,但面色间已有计较之意。
是言最早见于微信群转发,有人称“李师亲口承诺”,又有截图为证,其语曰:“不看分数,看孩子意志。来我这儿的,不走弯路。”我未细读,母却存之于手机相册中,偶有翻看。她不多言,语气中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焦急,那是家长在择路时特有的一种沉默。
我知母非轻信之人,但她一向好于“试一试”。此行,也许便是那“试一试”的一次。于是我不问,也不拒,便成行矣。
是日清早,天色未明,余与母即乘车而行。自城中出发,绕行乡道,逾五百里。道旁田垄皆干,草色未回,风自北而来,冷意尚在。母不语,余亦无言,心中但觉此行无谓,然亦未曾抗拒。
至村口时,未及晌午。村落无名,路旁数屋,皆灰瓦土墙,形制简陋。院约二十步见方,北有二层楼一幢,南有平房相对,窗皆闭,门皆锁。其地寂静非常,风吹沙走,纸屑低旋。母止于院前,取出照片细看,点头曰:“正是此间。”
院中一墙书红字数行:「疯狂英语・国学基地」。漆新而字拙,其形似人为仓促所涂,未加章法,尤有漆滴未干者,斑斑如血。
四顾无人,院落无声,犬吠不闻,鸡鸣亦绝。母复翻日历,叹曰:“来早一日。”是日遂归。途中未语,入县城,观一杂技。其人衣单而技陋,跳跃之间,光怪陆离,座中寥寥。母神色如常,余亦无感,观毕而返。
次日复往。未至午时,院中已聚众多。昨日之空寂已不复见,四处喧哗,呼喊不绝。家长带子而来,手携水壶与点心,形色纷杂,如市集初开。墙角立二旗,上印彩字:“口语速成”“十日敢讲”,风吹旗动,猎猎有声。
入北楼,大厅之中已布桌椅数排,人声鼎沸。前方一男子立于讲台,年四十许,身肥面油,口齿甚快。其言皆围绕“孩子未来”“改变命运”等语,语气激昂,状若演说。其身旁立一少女,年约十四,自述于此学习英语已一年,进步良多。其声清亮,吐字明晰,惟神色呆板,似已熟习此番言辞。
母面带微笑,目光柔和。余默立厅后,望屋顶之梁,心无波澜。彼时未敢断言此为骗局,亦未生欢喜之情。只觉其中一切过于整齐,如同剧场开幕,台上台下,各司其职。
午饭在院西。砖屋低矮,窗小而暗,设圆桌七八,每桌四五人,皆自取饭菜。所供者不过豆腐、青菜、汤水各一,味淡而温。母频频点首,低声道:“终究还算朴实。”
饭毕,入南屋看宿。其屋设铁床,上下相对,铺布旧而薄,床脚有锈迹斑斑。窗外风起,尘影浮动,屋中有潮气,隐隐洗衣粉与鞋垫混杂之味。数少年坐于床上,低声交谈,手持手机,神色空茫。
午后二时,试始。我与数人分配入一屋,坐定。卷纸粗糙,字迹微糊,所出试题,多为旧题所改。监考者斜倚讲台,低头看手机,不问诸生。
窗外风止,纸页微动。不远处传来高声齐读,如诵经文,起落有致,声声不绝。
六时许,考毕。母取得一纸,其上印:“数日后短信通知成绩。”读毕收起,笑意未消。归途之中,暮色渐浓,田野模糊,唯远处数灯,如星微明。
我知,此地之事,未竟于此。后之来往,渐由观者转为参与,其间始有所谓“模范之生”,亦尝领读、背诵、夜宿、集训、远游,其种种事,今忆之,若雾中行履,记得其形,忘其向也。
其二
其二
数周之后,试卷之分已出,我名列第五。母亲见状,面有喜色,不语而笑。她将手机中的那张截图又翻出一遍,反复端详片刻,随即订行程。
是月初五,再赴吴桥。
彼时已非首次到访,院中气象却与往时稍异。人仍多,然秩序井然。院内张贴新榜,榜首之列,书“模范生”三字,于其下列五人之名。我名在列,居第三。母于榜前拍照,发群,群中连连回应,言辞羡艳。
自此,我之身份亦稍有转变。
其处授课之法,并不复杂。以一册薄书为准,收英语短文五十篇,每篇配音一则,语速渐增,腔调统一。所谓学习,不过反复朗读。单读、齐读、领读,读之大声而不容停顿。书页之侧,每段均注“语感”“节奏”之评语,字体粗黑,似为强调而设。讲师所用音响极大,一开即震屋梁。
数日后,有人引我至讲台旁,说:“祁老师让你领一段。”我未及思索,手中便已递来一张纸。纸上所印,不过是我读过多遍的一段对话。于是我站在众人之前,照读不误。
有人随我同读,有人望我不语。空气中浮动着小孩的汗味与油墨的气味。讲师站在角落,不语,偶点头,亦未笑。
自此,每来一次,我几乎都站在前列。那“模范”之名,亦无人问由,只是默认如旧事。母偶尔问我:“老师说你读得很有感觉。”我点头,不语。
过半月,一日忽换书,不再读英语,而为诵经。首为《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后为《地藏菩萨本愿经》。课前讲师未作解释,只言:“先读,读熟。”
书页为繁体,竖排,印墨浓黑。内容多为愿文、咒语、地狱之形。初读时多有错音,后日渐流利。至数日后,已可一气读毕,声调起伏,无人中断。
他人亦读,齐声诵之,如寺庙暮鼓。讲师未作讲解,亦无人发问。日中风过,窗纸震动,经声不止。
其后每次集训,皆有朗读之环节。初为热身,后为中心。音响开至最大,讲师站于一侧,偶批音调,然不涉内容。屋外有家长张望,远远看着,神色凝重,仿佛窥视某种玄秘之事。
午饭、午睡之后,复读。有人打瞌睡,有人嗓哑,有人因喉痛被送回宿舍。然课程不减,读者更替。
我从不主动请辞,也不曾请求留下。只是被安排,被递纸,被指名。无抗拒,亦无意愿。读毕,退下,如初。
夜间偶梦,经声不散,耳中犹有残响。梦中无人,唯声在堂上回转,如空屋之回音。
某夜将歇,一少年忽问我:“你信不信佛?”我未答。他又笑言:“念多了,总该灵一点。”
我低头看书,未置一词。那页经文写着:“众生闻名,得解脱苦。”字体整整齐齐,不见一丝异样。
彼时屋外有雨,檐下灯微,纸页翻动,似有人轻叹。
其三
其三
集训营开至第三期,学员已过百人。
所设课程依旧,早诵、午读、晚测,三日为一轮,七日为一循环。讲师更迭频繁,多数不留姓名,来者讲一段英语,或朗读数篇经文,即退下;下次再见,已是数周后之事。
每期开营之日,院内张榜,列出“优秀”“模范”“进步”等数栏,名字重叠者居多,未见淘汰。榜前总有家长驻足拍照,有者转发朋友圈,附言“孩子变化大”,末尾加一祈愿符号。
孩子们从不看榜。有人说名字错了,有人说照搬上期,还有人说那不过是老师凭记忆写的。众人听后一笑,无人深究。
真正的秩序不在榜上,而在“读”。每天早六时,起床、刷牙、集合,屋内开灯,全员站立,轮流朗读。读者声音若低,即有人在角落开扩音器,以示“标准”;读者速度若慢,旁人即被要求一同补读。此时屋内回音错乱,语调相冲,句意全失,唯剩一种巨大的响声。
一日晨课中,有人读错三个词,讲师忽喊:“坐下!”全屋安静。讲师走至其前,将书夺下,厉声斥责。孩子低头不语。旁人面无表情,仿佛此事与己无关。训毕,讲师拍桌:“继续读!”众人应声,声音更大,仿佛为掩盖刚才的沉默。
午饭后有“感恩练习”。要求每人轮流讲一句感谢李老师、感谢语塾的话。多数人照本宣科,有人说“这里让我更自信”,有人说“我原本胆小,现在敢说了”。有孩童犹豫片刻,被催促三次,终低声曰:“我……我其实……还想回家。”话音未落,讲师即道:“停。”纸页翻过,下一人继续。前一人悄然坐下,神色未变。
夜晚,宿舍更为混乱。房间五六人不等,上下铺紧靠,气味交杂。睡前多有喧哗,常为游戏、八卦、调笑,亦有打闹。然每日清晨,无论夜中何事,众人皆仍准时起身,无一迟到。
一夜我睡半醒之间,闻有人小声哭泣。隐约为下铺者,声音细碎,如风拂窗。未敢探问,亦无人提及。次日其人神色如常,甚至朗读更勤,速度更快。讲师称其“有转变”。
有一晚,我被叫去大厅协助搬桌。途中见南屋宿舍门未关,有人正趴于床上模仿老师讲话,句句滑稽,音调夸张,旁人哄笑。有一人录像,另一人放哨。笑声忽然止住,只因窗外有人经过。众人迅速起身,关灯,躺床,静如无人。此事后再无人提起。
有数人嗓子哑至失声,依然被要求参加朗读。“即使不出声,也得动口。”讲师如是言。有者嘴唇干裂、咽喉红肿,发音破碎,仍站至最后。
有人趁夜写信,藏于床板之下。我曾在一次铺床时偶见一封,未拆,复放原处。几日后再看,已不见。
集训营如旧日落灰之钟匣,其中人声错落,皆如齿轮相咬。有人朗声背诵,有人倚席而眠,梦中低语如泣。窗外大人立而不语,面无喜怒,神情静极,似在听,又似不在。他们只等,等屋内之人归于某种形状,仿若久置的模具,已失其温。
某日课后,有孩童于门外独立,其目光呆滞,衣角未理。问之,不语。片刻后,讲师至,将其领走,未再归。
日后再见其名,尚列于“优秀榜”中。
其四
其四
暑热临身,空气中弥漫着粉笔与黏尘的气味。语塾之门在无声中重开,白墙上旧字犹存,唯窗纸略新,帖得歪斜,有墨迹未干之感。李师自堂后踱出,执一薄册,眉目阴郁,言辞不变,只道:“今次只讲十套卷。”
此言初出,学生面面相觑,心中尚疑其意。直至卷纸发下,始知非虚。其上字迹清晰,题目编号井然,不附解析,无旁批,题后只注:“记住。”纸张略厚,边缘有湿痕,似是匆忙复印。字体非打印,疑为李师手抄,虽不潦草,亦不整洁,有错字三两未改。
昔日讲课尚杂以例证与探讨,李师虽不善辞令,偶亦引《论语》、《古文观止》数句,以博生心。然而自此番始,尽然无之。李师起讲,自上而下,语调平稳,面无喜怒。若有学生问“为何此题选C”,李师仅言:“不必问。”
或有生不甘,再问:“不懂便易错。”
李师抬眼望窗外,语气微顿:“所以才要记。”
此一语出,如釘入板。其后诸生渐寂。问者寥落,纸笔交错,唯余沙沙抄写声。堂中温度日渐升高,墙角扇叶无力地转动,光线自百叶窗隙漏下,如刀片分割空气,落在每人额上。黑板边沿满是粉尘,讲桌之下,有未拂去的饭渍与脚印。
李师每日如常登堂,白衣整洁,步履不疾。讲课不再抑扬,唯声声准确。若有错抄,不骂不训,亦不赐详解,仅言:“重写。”其面容愈显瘦削,双颊隐现青筋,右眼常有微跳之状,语止处,往往闭目数息。
某夜,风起,寝室略凉。许海新悄声唤我,言之嬉笑,说:“你搜过黄片没?”
我迷中未应,他递我手机,示意搜索。我手起键入“黄片”二字,画面空空如也,遂弃之不理。
次晨,祁老师将我与许唤至前列,声未高,言甚冷:“昨夜搜了什么?”
我一时语塞,只得点头。他不再言语,径自请家长,后事无所交代。
自此,我之席被移至角落,靠门而坐。无师提问,无生交谈,仿佛已自卷轴中剥离。上下课皆独往独来。
十卷之讲,日夜并行。初有试图理解者,终为“背下”之声所淹。有人错者,李师不问缘由,仅授“正确答案”,命其背之。讲台之上,语录愈简,笔迹愈重,章法愈定。墙边写有“要进名校,先破自我”,墨迹新覆旧痕,似连此句亦背熟而不信。
某夜课终,李师分发一张单纸,上列“高频考点”。纸色灰旧,边角已卷,上无标题,仅数行数字与题号,排列无序,宛若占卜图表。
有生低问:“老师,真会考吗?”
李师未答,只将教鞭轻敲卷首一题,似在定音。
考试既至,果如所列。所出之卷,正为“卷四”全篇。群中哗然,有言“神算”,有言“神助”。母亦言我“争气”,转发成绩于诸亲。
两载之后,于馆门遇许海新。彼时他面色稍沉,语带迟疑,道:“你知道吧,那题是怎么来的。”
我摇首。
他低声曰:“是他有旧识在校中,打点而得。李师一句不说,真沉得住气。”
我答:“他不会说的。”
归家后,我取出旧册,翻至卷四。墨迹犹存,字迹犹寒。
我凝视良久,将那本旧笔记翻至最后一页。
末行写着:“此题务必牢记。”
我静静望了片刻,复将其合上。灯光照在书脊上,纸边已微微卷起。
于此不欲再言。
创作谈
创作谈
这篇小说的缘起,是朋友的一段零碎讲述。
他提到过某些教育机构的片段经验。我被那种语气打动——不是愤怒,不是指控,而是一种“过去在那里,但已经离开”的冷淡感。那成为某种契机,引我进入对教育体制长期以来的压抑感与异化感的反思。
我始终对“声音的规训”这件事感到不安。一个人的语言如何变成工具,变成评估标准,变成通往某种“成功路径”的刻度——这是当代教育中最隐蔽也最强硬的控制方式。朗读、记忆、背诵、听话、分组、上榜,这些看似中性的动作,本质上构成了一种安静而高效的同化机制。
我没有试图描述任何真实事件,也没有打算还原哪个具体人物。《李师语塾纪行》更像是一种结构的提炼,一种氛围的重建。它是一种冷的写作,平稳、不动声色、带有文人笔记式的审视感。不是因为我想保持距离,而是因为我想让语言本身也接受规训的感受——就像被教育的那个人一样。
写作过程中,我受到芥川龙之介很深的影响。他笔下那些自我尚未成形的角色,那种“不说”的克制,那种“明知荒谬却不挣扎”的内在审美伦理,让我意识到:有些真实,只能用冷静写出来,才能被看见。
I

wanglingZ1Z
37 人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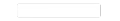
故事烩
9266 人关注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