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最近一直在做一个天津的文化展厅项目,为这个项目组织一些内容。总体来说有点无聊,因为大多数故事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而我又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本地人,就更熟悉了。不过,在整个过程中,还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图片侵删
要说最有趣的,还得是抗战时期的各路地下工作者的故事,毕竟《潜伏》就是以天津为背景拍摄的嘛。而天津也不愧一个“复杂“的地方,不仅有我党的“峨眉峰”,还有国党的“蓝衣社”,甚至还有不少民间爱国志士的自发组织——这其中就有一个叫“抗日杀奸团”的学生团体。这个团体主要由天津南开、耀华学校的学生构成,后来扩展到北京、上海,成为一个覆盖三地的学生地下抵抗团体。他们焚烧日伪教科书,刺杀投敌大汉奸,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而天津作为这个组织的发起地,自然也发生过很多鲜为人知的事件,出现过更多鲜为人知的“少年英雄”。
在正式讲故事之前,我还是得叠个甲——不完全保真、保准、保全。因为毕竟还是在工作中发现和整理的,且甲方也有时间要求,不能做特别深度的档案考据。之所以想自己再处理一下,一是因为展厅毕竟规模有限,讲解员素质和展示界面都不充分;二是确实被这些少年英雄感染,想趁着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的机会,把这些深埋在历史长河里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
————————————
说到“抗日杀奸团”,首先还是要说一说背景,为什么在天津会首先出现这样一个学生抵抗团体呢?我想,这也许与天津沦陷后日寇大力推行的“奴化教育”有关。
大家知道,天津是一座中国教育名城。从北洋大学堂到南开系学校,再到如今的“学区落户”,可以说它的文化教育水平在全国范围还是能排到前列的。据统计,在抗战爆发前,天津已经有大大小小的高等学府和专科学府30余家,学生数量更是成千上万。而且,作为中国马列主义早期的策源地之一,这些学生中不乏有大量的左翼进步群体,这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有周、邓参与的“觉悟社”。
天津爱国学生组织“觉悟社”社员合影,不过他们主要组织活动,不做锄奸,你能找到周总理和邓奶奶吗?
南开学校校长、教育家张伯苓,他北洋水师出身,身材高大,目光随“核”,坦白讲学生可能不敢不好好学习- -
所以,当日寇攻入天津市,首先就把炮口对准的学校,将南开大学夷为平地。不仅摧毁了学校的建筑,还摧毁了大量学校图书馆中珍藏的文献图书近万册。同时,从占领东北开始,日寇就特别注意在各级伪政府中建立汉奸教育机构,层层推进,从幼儿园开始强行普及日语、灌输“亲日”思想。孩子们入学的第一课,居然不是学习中文,而是学习“五十音表”和日本国歌,强制要求学生参与“中日中小学生交欢学艺会”“学生日语讲演比赛”等等“文化亲善”活动。
这是一张网图,应该是日寇在东北推行的奴化教育
天津作为当时的北方金融和贸易中心,日伪推行“奴化教育”的程度更高。其中,在汉奸组织“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下,就常设一个“教科书修正委员会”,玩起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把戏;还出版“共荣地图”,将“满洲国”切割出我国版图,愚弄当时的中小学生。
这是伪满洲国的日伪课本
而在表面上的“亲善”之下,对于那些不认同的学生和家长或者老师,日伪就会上门“恳谈”,邀请“参观日租界”,还通过汉奸鼓动学生和家长间相互举报,并做成“日报”每天上交给负责的日伪组织。
而“抗日杀奸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自然诞生的,参与的人员无外乎是一群十八九岁的中学生。所以直到抗战结束,这些人也仅仅不过二十六七岁,果然是“自古英雄出少年”。据不可靠的信息说,由于“抗日杀奸团”表现出色,后来也得到了戴局长的帮助。不过据团员回忆,当年他们看中的是参加抗日,而并不关心党派之争。
这是百度词条里的一张图,看起来像但不确定
————————————
一开始,“抗日杀奸团”的目标还局限在对抗日伪奴化教育上,执行过一些焚烧日伪教科书、焚烧日伪出版社的任务。不过,随着抵抗的深入,“抗日杀奸团”终于还是将“刺杀汉奸“列到了首要目标,而第一个“祭旗”的,就是天津伪教育局长陶尚铭。
1、刺杀陶尚铭
1、刺杀陶尚铭
关于陶尚铭,他虽然也做过一些好事,但是在抗战时期确实是一个汉奸。早年,陶尚铭留学日本早稻田,并长期担任张作霖的秘书与张学良的高级幕僚,在“东北易帜”中出过力。不过,在抗战爆发后,他成为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的代表。而关于这次“刺杀陶尚铭”,网上也有不少浪漫化的处理,不过我们还是多少再实事求是的,基于天津档案馆资料和当事人回忆录,尽量还原一下事件的原貌。
1938年11月4日,彼时陶尚铭上任天津伪教育局长不到一年。或许是觉得自己未来还有“上升空间”,所以他并没有在天津买房置地,而是和太太一起租住在现马场道上的“西湖饭店”。而这也就给“杀奸团”提供一个良好的刺杀地点。根据当事人祝宗良晚年回忆,这次刺杀他们一共派出了四个人。由孙若愚和孙湘德担任刺客,宋长福和祝宗良负责掩护,提前在西湖饭店埋伏好,只等陶尚铭现身。
这是关于马场道西湖饭店的一张网图,原为民国军火大亨雍建秋所有,现已经不存,虽然我就住马场道附近,但也不保证是对的
下午3点30分,陶尚铭果然从饭店出来,与太太和副官一起坐上了早已停在门口的汽车。就在他们叫开车的司机之时,之间从饭店的拐角处突然冲出两辆自行车。这两辆车上分别坐着一名身穿蓝色大褂的青年,看起来似乎人畜无害——万万没想到,这两人一蹬到汽车旁边就立刻从大褂下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对着汽车“啪!啪!啪!啪!”连开多枪!并在人们还没醒过味儿来的时候,迅速蹬车逃离现场!
可惜是的,事后团员才了解到,这次刺杀其实并没有成功。陶尚铭大难不死,只是头部被子弹擦伤,太太则毫发无伤,只有副官伤势严重。少年们对此也进行了总结,认为一是隔着汽车的铁皮和玻璃,让弹道发生了偏差;二是虽然勃朗宁手枪小巧易于隐藏,但是杀伤力不够,应该马上换枪。不过,虽然陶尚铭逃开了制裁,但是日寇对日伪政府大为光火,最后罢免了伪天津警察局长周思靖,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为抗日做出了贡献。
2、刺杀王竹林
2、刺杀王竹林
兵荒马乱的年代,这次“不成功”的刺杀事件也很快就被其他“热点”盖过去了。所以,在总结前次经验之后,“杀奸团”很快又有了新的目标——刺杀王竹林。
汉奸、流氓大亨、伪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
谁是王竹林?可以这么说,王竹林在抗战前就是天津地面上的一个“社会人儿”,估计多少有点“涉黑”。在天津沦陷之后,王竹林马上主动投靠日寇,并通过担任所谓的“天津商会会长”控制了全市的工商业,让天津的企业、工人都成了发动日寇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尤其可憎的是,他还与其他汉奸串联,一起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积极的给日寇做鹰犬,可谓“人人得以诛之”,多少有点赛瑞巴斯的意思了。对于这起事件,网上还是有不少浪漫演绎,而且写的还很惊险。不过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原则来尽量真实的还原这个故事。
在确定刺杀目标之后,团员们首先开始观察王竹林的生活规律。但是这个大汉奸不亏是在社会上混迹已久,非常狡猾,完全无法捕捉他本人的行动轨迹。不过团员也并非毫无收获,牢牢记住了他牌照“423“的“斯蒂庞克”(不是)。
1928年12月28日晚上,“423”停在了天津丰泽园饭店的门口,而参与行动的团员们紧随其后。这次“杀奸团”还是派出了之前的四名团员,不过改为让祝宗梁和孙湘德担任枪手,而孙若愚和宋长富负责掩护。
当晚饭局已毕,王竹林被其他汉奸众星拱月地送到门口,正在一一客套告别的时候,祝宗梁和孙湘德两人突然从一旁冲出,二话没说,对着王竹林“啪!啪!啪!啪!”连开七枪!王竹林当场死亡!于此同时,负责掩护的孙若愚也在外围“啪!啪!”放了两枪,分散人们注意。之后,几人趁着晚上混乱,按计划跑道隔壁的小胡同蹬上自行车,穿行撤退。
毫无疑问,这次刺杀的成功,给团员们巨大信心。后经法医验证,当晚王竹林身中多枪,最后因“脑后右近上系枪弹透出皮肉向外,致命。”终结了他罪恶的一生。有意思的是,日伪政府完全没想到这么一起成功的刺杀案件能是一群十八九岁的学生做的,反而把怀疑重点放在了我党人员和国党“蓝衣社”上面,也给“抗日杀奸团”继续活动来了个“大开方便”。
3、刺杀程锡庚
3、刺杀程锡庚
在成功刺杀王竹林之后,“抗日杀奸团”就将“一号目标”锁定在了汉奸程锡庚身上,而如果说前两次只是“小试牛刀”,那么这次刺杀,不仅成为“抗团”最成功的一次行动,也是对抗战时局贡献最大的一次。那么,这个“程锡庚”到底有多罪大恶极呢?
汉奸程锡庚
程锡庚,江苏人,18岁毕业于南京江南高等学校,并担任民国海军部秘书。后被官派英国留学,之后又相继取得法、美两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研究会秘书,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上任中国代表团秘书。1923年任财政部秘书、全国财政讨论会专门委员。1928年前往巴黎办理退还庚子赔款。1934年任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截止到此,似乎还是一个蛮有前途的技术官僚。但是,就在他在财政部任上的时候,他还担任了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的秘书。而这个王克敏,就是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并称“民国四大汉奸”的历史罪人。
大汉奸王克敏,坏得都带相儿了
早在王克敏青年留学日本期间,他就已经是清政府在学生群体里的“密探”,成为人群中的“告密者”。辛亥革命之后,虽然一度“失业”,但是他跑到法国认识了不少“金融大亨”,开始了自己的买办生涯。这个时期的王克敏非常有钱,财力超级雄厚,大把撒币,很快就在北洋政府找到了关系,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并最终在王士珍内阁担任财政总长,登上了“部级”大位。
但你不要以为王克敏只是通过卖官鬻爵上的台,他本人还有一项“绝活儿”,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过目不忘,记忆力极为惊人(这可能是他早期告密时锻炼出来的),甚至能背诵银行账本。此外,他人品也是出名的“次”,人人都知道他善于投机、贪腐无度,在北洋内部被人蔑称为“钱鬼子”。不过,随着王士珍的倒台,虽然恋恋不舍,但王克敏也只能暂时低调下来。
不过日寇又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抗战爆发后,因为需要成立伪政府的原因,日寇纠结了不少北洋余孽,王克敏自然也想从中渔利。不过,就连日本人都知道这个人不靠谱,更想找像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这种德高望重的元老人物。不过这三个人都在这时候不约而同的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尤其是吴佩孚在面对日寇胁迫时尽显民族气节,确实是条汉子。所以,在“邀请”大人物未果的情况下,日寇只能退而求其次,让王克敏成为伪政府班子的一员。
既然再次出山,那还是自己的老班子工作更顺利。于是王克敏自然而然的叫上了自己的小弟程锡庚,并合力为日寇成立了一家名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机构。
要注意,他们虽叫“银行”名,但不办银行事,而是专门给日寇的搜刮战争资金。就和后来老蒋的“金圆券”一样,他们也发行一种“联银券”,并强制要求群众和企业按照1:1的比例兑换,再用“征”来的法币去外资银行套外汇购买军火。这不仅让沦陷区的家庭遭重,也对沦陷区的工商业遭受重大打击,甚至被摧毁。
一文不值的废纸 ,冥币都比它有用
此时,程锡庚就担任这所“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天津支行总经理。再为日寇搜刮钱财的同时,程锡庚也在市场上狐假虎威,对那些抗拒的爱国实业家、银行家都进行了逼迫、抢夺,甚至镇压。据资料说明,爱国金融家胡仲文,当时虽然还在担任四行储蓄会的副总经理,但家中已经被逼的非常窘迫。不过即使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胡仲文和他的好朋友、天津盐业银行的总经理陈亦侯,还是一起守护住了一件重要国宝——不过这里咱们按下不表。
说回程锡庚,此时他也惴惴不安。此前,军统已经安排特务在北平对王克敏执行过一次失败的刺杀,这也给身在天津的程锡庚提了一个醒。因此,他平日深居简出,非常小心,不过还是因为自己的一个爱好,最终被“杀奸团”抓住机会——那就是看电影。
或许因为早年留学欧美的原因,程锡庚本人是一个电影迷,而天津的电影行业早就非常发达,甚至很久以前,就可以和美国同步上映好莱坞大片了。
其实,近代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就在天津,即1906年开业的“上权仙电戏院”。后来《大公报》给这种艺术起了一个“学名”,就是“电影”。到1920年代,天津已经有大大小小的电影院30多家,这里面就有程锡庚特别喜欢的“大光明电影院”。
这上面确实是“上权仙”,而不是“权仙”,所以随便百度的故事都不太可信
这家“大光明电影院”目前依然“健在”,虽然已经停止运营,但在当时可是天津首屈一指的高端电影院。它位于海河边上,最早是一个仓库,紧挨着天津传统的商业区“小白楼”。后来,这里被“新新影戏院”的经理韦耀卿看中,于是他又找到一名英籍印度商人泰莱悌(这个人也有很多故事,但是按下不表)贷款,打造成一家名为“蛱(jia)蝶”的电影院。不过,韦耀卿可能有点操之过急,导致还不上款,尤其是找泰莱悌贷的还是高利贷,最后只能被泰莱悌收购。
大光明的盘活方案还没有出
其实,当时影院周围的土地都已经是泰莱悌“泰朗普”的囊中之物,作为一名成功的高利贷商人和房地产开发商,很有可能想借着这家影院,给自己的“大盘规划”做一个商业支点。于是,他再次升级了影院的装修,还真正实现“全球同步”,并把影院改名为“大光明影院”。
在那时候可没有什么汉化组,因此主打“全球同步”的大光明影院播放的片子全都没有中文,而这也成了很多拥有留学背景的达官显贵们的社交主场。什么黎元洪、张勋、潘复、靳云鹏,都一度是大光明影院的VIP中P,而程锡庚当然也是影院VIP中的一员。
其实,“杀奸团”此时还是很难把握住程锡庚的行踪,不过和刺杀王竹林一样,团员们还是将程锡庚的车牌号牢记于心,做好准备,随时找机会行动。而就在1939年4月9日下午,刚刚放学的祝宗梁、袁汉俊、孙惠书、冯健美四人正蹬车回家,在路过大光明影院门口时相当偶然地发现一辆牌照超级熟悉的小汽车——不用问了,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立刻行动!几人简单一商量,决定留下孙惠书、冯健美看守目标,祝宗梁回去取枪,袁汉俊回去喊人。
不过多一会,团员们又在影院门口集合,并且分批买票入场。这您可能要问了,影院这么大,黑灯瞎火的怎么能找到程锡庚?万一误杀怎么办?确实,大光明影院最为天津最高端的影院之一,里面有三层共900个座位!不过,像程锡庚这样的大人物,势必要有自己的VIP区,这个区域就是影院的三楼。
不过,即使把目标锁定在三楼还是不够。因为这里并不是包房,依然是一个开放的VIP区域,每个人都是头冲后,还是无法准确辨认出程锡庚的位置。不过要我说,学霸就是学霸,您可别忘了,“杀奸团”的团员本身都是南开、耀华的学生(这两所学校至今都是天津最顶尖的中学之一,培养出很多两弹一星元勋,其中南开还是周、温两代总理的母校)。担任枪手的祝宗梁脑筋稍微一转就走向了楼层服务员,告诉说自己要写一个“PPT”。
当然“PPT”是个玩笑了。真实的情况是,作为一家高端的影院,院方深知各路VIP日常工作、应酬繁忙,在观影中难免有人外找。因此影院有一个玻璃框,每当有人外找的时候,放映室就在玻璃框上写下“某某人外找”的字样,放在放映机前,这样就能不打断别人观影的同时达到通知本人的效果。因此,祝宗梁利用的就是这个机制。
当屏幕上打出“程经理外找”字样的时候,我想程锡庚此时已经意识到暴露了,但是人的下意识还是很难控制。虽然坐在一旁的太太拉了他一把,但是黑暗之中还是闪过了一个欠身的背影——就这么电光火石的一刻,少年们敏锐的目光就瞬间锁定了目标。
既然找到了程锡庚的位置,为了确保行动成功,祝宗梁悄悄摸到了程锡庚背后的一排,而另一位被喊来支援的刘友深则堵住了楼层出入口,一呼一吸之间,就等待着一个最佳时机。
要我说,这天就是该着程锡庚毙命,为什么呢?如果当时上映的是《廊桥遗梦》,说不行他还能捡回一条狗命。可是天意难为,这天上映的片子叫《为国干城》,是一部战争片!就当人们被银幕上“枪炮齐名”深深吸引的同时,坐在后一排的祝宗梁果断抬手,朝着程锡庚的头部“啪!啪!啪!啪!”连开四枪!大汉奸当场死亡!一旁的太太看见之后惊声大叫,但是周围人却都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而这也就给了祝宗梁完美的撤离机会!
现场马上就混乱起来,而祝宗梁此时已经跑道楼梯口,但一旁突然窜出一个外国大汉一把抱住了他,祝宗梁想都没想“啪!啪!”照着大汉的肚子连开两枪,随即放倒。而此时又有一名外国大汉冲过来拖住了他,而这回祝宗梁可已经没有子弹了,两人只能顺着楼梯扭打起来!这是,负责在接应的袁汉俊手里有枪,只得一枪就放到了那名纠缠的外国人。随着这后来的枪响,整个影院一二三楼都乱成一锅晋西北了,几个人也就顺势混在人群中挤出大门,没来得及蹬自行车,而是迅速乘坐黄包车各自离去。
由于开枪时黑布隆冬,成没成功团员们也不敢确定,直到报纸上说大汉奸程锡庚头、颈各中一枪,当场死亡,大家才长出一口气。而在楼梯间第一个抱住祝宗梁的是一个“白匪”, 叫满索罗夫。他可能也是日寇的帮凶,腹部的两枪把他的肠子前后打了八个洞,但是居然没死!另一个则是瑞士人(一说瑞典),叫格拉萨。这个哥们就是个纯路人,本来准备看完电影就上船回国,结果死在这儿了。因为报纸报道的关系,这起刺杀事件也给全国当时的抗日氛围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好像是《大公报》的新闻,当时《大公报》好像撤到了大后方,但撤退之前确实是在天津,是由英若诚的祖父创办的
同时,在和这两个外国人扭打中,祝宗梁的手枪也被遗落在现场。幸运的是,这次他用的是一把木柄新枪,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而伪警察局也随后发布了一个嫌疑人的通缉令,说嫌犯是一名“有一身着咖啡色西装少年,年约二十余岁,身体瘦小”。而这反而另祝宗梁心中暗喜——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注重全面发展的学生,身材练得很壮实高大,这个通缉令显然只能通缉到空气。
————————————
据不可靠资料显示,后来祝宗梁前往香港,后又辗转前往上海,继续从事地下抵抗工作,还参与谋划过川岛芳子的刺杀行动。期间,他在上海不幸被捕,面对日伪的严刑拷打拒不承认,趁着敌人不注意还企图吞铁片自杀,最后因为实在没有证据侥幸释放。解放后,祝宗梁留在上海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80年代开始,在上海市政协工作;90年代退休之后,祝宗梁开始在家撰写关于“抗日杀奸团”的回忆录,还曾经写信给广电,委婉地对“抗日神剧”提出过改进建议。最后,老人家于2020年在上海去世,享年100岁。
祝宗良青年时期照片,年代不详
这位同是参加刺杀程逆的孙惠书,她的父亲是“抗日名将”孙连仲
这位也是参加刺杀程逆的袁汉俊,他掩护祝宗良顺利撤离,但1943年不幸被铺牺牲,年仅26岁
这是一张聚会照片, 很可惜这张图没有全部标出人物的名字,但是右侧“冯健美”,就是参与过刺杀程逆的团员
祝宗良晚年接受央视《五大道》专题片采访
据说,祝宗梁爷爷晚年撰写回忆录时经常感叹,能活到解放后的同志实在是太少了,很多人连名字都忘了。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事情尽量补充整理出来,虽然它原本只是工单上的一个活儿,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儿非常有意义,尤其是看完《南京照相馆》之后。所以,如果你看到最后,我希望你也能自己去发现这些被藏在时光中的热血,受不受激励不重要,重要的是讲给下一代人听。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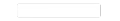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29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