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译按」
本文写于2007年,那时诺基亚手机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还有近40%,而第一代iPhone则刚刚发布,大多数都人无法想象,那块触摸屏的将会掀起一场影响多么深远的交互革命。设计,正在从「造物」转向「编织看不见的服务网络」。
正是在这样的技术躁动期,休·杜伯里(前苹果设计师)和保罗·潘加洛(美国控制论学会现任主席)合作撰写了本文。他们尝试用控制论(二阶控制论)解释一个根本问题:当设计对象从桌椅和海报变成操作界面和软件系统时,设计师需要怎样的新语言?毕竟如今的我们在智能设备上点击的每一个按钮,背后都是是数百个子系统的精密咬合。
面对这样的情况,控制论提供的不是冰冷的公式,而是一套理解复杂系统的「思维框架」。例如在本文中得到引申的「必需变异度」概念,就可以解释为何推荐算法必须保持适当随机性:因为系统需要足够「弹性」抵御用户兴趣漂移,但又不能失控到推荐无关内容。
那么,用控制论视角下的「系统」和「反馈」分析服务设计,是否意味着将人视为可操控的部件?毕竟这也是控制论曾经遭受过的质疑。
当作者强调「设计即政治」,呼吁用「会话」取代单向控制时,便划清了与行为主义的界限——真正的系统思维,是让用户与算法在「二阶会话」中共建目标。而非像Meta、Tiktok等饱受批评的算法沉迷:它们的反馈回路是封闭的,没有会话,用户的赞和观看只能加固信息茧房,却从未真正参与系统进化。
控制论从未承诺完美的控制,它真正的启示是:承认系统的自主性(autonomy),在会话中保持敬畏。从而帮助设计师在效率与人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当我们谈论「系统思维」时,或许该重温文中的隐喻:观察亚马系统逊就像通过钥匙孔窥视凡尔赛宫——我们永远无法掌控全景,但至少可以学会与喷泉的水流声共处。
大目妖 2025年5月23日
休·杜伯里 Hugh Dubberly
休·杜伯里 Hugh Dubberly
1958年出生。设计师。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曾在苹果公司管理跨职能设计团队。期间,他与人合作制作了一部名为 「Knowledge Navigator」的技术预测影片,预示着互联网将出现在便携式数字设备中。在苹果工作期间他还在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担任计算机图形学系的首任系主任。由于对出版业在互联网上的发展前景充满了兴趣,他随后成为《时代镜报》的界面设计总监。之后,他加入网景公司,担任设计副总裁,负责管理网景公司门户网站的设计、工程和制作团队。2000年创立了Dubberly Design Office。
保罗·潘加洛 Paul Pangaro
保罗·潘加洛 Paul Pangaro
1951年出生。美国控制论学会现任主席。卡内基梅隆大学建筑学院计算设计访问学者,此前曾任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学院(HCII)的实践教授。潘加洛的工作探索会话在人与人、机器互动中扩大人类能动性的作用。他在控制论、系统、会话理论、设计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其工作方法的基础。保罗和休·杜伯里共同主持了「未来设计教育计划」的系统工作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保罗坚信,21 世纪的设计师、建筑师和技术专家必须全面接触复杂系统,这些系统包括技术与人性、社会与正义、气候变化与地球健康等纠缠不清的领域。保罗正在与美国控制论学会一起发起#NewMacy倡议,以恢复和修订控制论诞生时著名的梅西会议(Macy Meetings)。该倡议吸引了跨学科、跨时代的国际参与者,致力于应对上述复杂的系统级挑战。
以下为正文部分,共约9,500字
控制论与服务工艺:行为导向设计的语言 Cybernetics and Service-Craft: Language for Behavior-Focused Design
控制论与服务工艺:行为导向设计的语言 Cybernetics and Service-Craft: Language for Behavior-Focused Design
休·杜伯里 保罗·潘加洛
Kybernetes, January 19, 2007, v9
摘要本文认为设计实践已从手工艺(hand-craft)转向服务工艺(service-craft),服务工艺体现了设计实践中对系统的日益关注。文中提出控制论是理解动态系统的实用框架的根源,其中包括具体的互动、更大的服务系统和设计活动本身。表明第一代和第二代设计方法的发展与第一代和第二代控制论的发展是平行的,特别是在以下两方面:将设计置于政治领域和将系统定义视为被建构的。本文建议将控制论作为广义设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键词:Cybernetics, design, design methods, hand-craft, interaction design, politics, rhetoric, service, service-craft, service design, system
01 控制论与设计之间的联系史
01 控制论与设计之间的联系史
控制论对设计思维的影响可以追溯到50年前*。然而时至今日,控制论在从业设计师中仍然几乎无人知晓,在设计教育或设计理论讨论中也无人提及。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诺伯特·维纳曾在乌尔姆造型艺术学院(HfG Ulm)任教。 乌尔姆要求学生选修控制论课程。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人工科学》一书中指出了控制论与设计的关系。 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在他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中推荐了控制论书籍和设计理论书籍。
设计师对控制论的早期兴趣伴随着控制论在流行文化中获得的短暂关注。第一代控制论思想影响了第一代设计方法*思想,第二代设计方法*则与二阶控制论有许多相似之处*。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设计方法运动的两位创始人布鲁斯·阿彻(Bruce Archer)和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在他们的设计著作中明确提到了控制论。里特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的设计方法课程中融入了控制论。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1972年,霍斯特·里特尔在《论规划危机:「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系统分析》(On the Planning Crisis: Systems Analysi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中提出了第二代设计方法。 他强调了保持客观设计观的难度,并将第二代方法描述为一个没有专家论证的过程,其本质是协作和政治性的。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在1972年的一次演讲中,海因茨·冯·福斯特提出了二阶控制论。 他指出了观察者在描述系统中的作用,也强调了保持客观观点的难度。
控制论和设计方法运动都未能引起广泛的兴趣。其中一个原因是,两者最初的实际应用都很有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走在了时代和流行技术的前面。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特别是在设计领域,控制论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罗斯·艾什比将控制论对行为和复杂性的处理列为「控制论的独特优势」*。这两个主题越来越受到设计师的关注,尤其是那些设计「软」产品的设计师,即那些从事界面设计、交互设计、体验设计或服务设计的设计师。在这些领域,设计师们关注的是「行为方式」(ways of behaving)——一件事物的作用与其本质或外观同等重要——在这里,控制论可以帮助设计师。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罗斯·艾什比(Ashby, W. Ross),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Chapman & Hall,Ltd.,London,1957年。
02 设计向服务工艺的转变
02 设计向服务工艺的转变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设计实践* 的发展轨迹一直是从物体(object)到系统(systems),再到系统集群(communities of systems)。设计实践从注重手工艺和形式,到越来越注重意义和结构,再到越来越注重互动和服务——我们称之为「服务工艺」(service-craft)。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虽然设计与建筑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建筑实践有其独立的历史,我们在此不再赘述。
服务工艺包括服务系统的设计、管理和持续开发,也就是提供服务的连接触点(connected touch-points)。连接触点是指参与者亲自或通过通信网络与服务提供商或机器产生互动之处。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其网站、值机处、空乘人员和座位就是众多连接触点中的一部分。 谢利·埃文森将服务描述为「参与者穿过一系列连接触点时的体验」*。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谢利·埃文森(Shelley Evenson),《The Future of Design? Designing for Service》,在Emergence Conference: Service Design会议上发表的演讲,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2006年9月8日。
对一些人来说,服务仍然意味着琐碎的工作,例如洗碗。然而,服务系统却处于消费电子产品的最前沿,例如苹果公司的 iPod-iTunes-商店系统或任天堂的 Wii-online 服务。服务系统也是电子商务的定义本身,如亚马逊、eBay或谷歌。
《连线》杂志前编辑凯文·凯利说得好:「……商业产品最好被当作服务来对待。 不是你卖给客户什么,而是你为他们做了什么。重要的不是某样东西是什么,而是它与什么有关,它能做什么。流量比资源更重要。 行为至关重要。」*。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凯文·凯利(Kevin Kelley),《失控》(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William Patrick Books,1994年,第27页。
如今,设计实践的前沿越来越多地涉及团队(通常包括许多设计专业)合作开发互联系统,以及团队合作开发服务工艺。
传统设计实践与新兴设计实践之间的区别可以概括为:
当然,手工艺并没有消失,服务工艺也没有脱离手工艺。手工艺在服务工艺中发挥着作用(正如在开发软件应用程序时,写代码仍然是一种手工艺)。服务工艺侧重于行为,但它又以人工制品来支撑行为。服务工艺需要团队,而团队依赖个人。服务工艺不会取代手工艺,相反,服务工艺会在手工艺的基础上扩展或建立另一层工艺。
03 需要新的设计语言
03 需要新的设计语言
服务工艺是在更大的变革背景下出现的。向知识服务型经济的转变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兴起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二者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彼此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还在继续加速。随着传感器的普及,另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例如,苹果公司的 iPhone将包含至少5种传感器:摄像头、麦克风、距离传感器、动态传感器和触控传感器(也许还有 GPS)。越来越多的东西都有了互联网地址,例如,很快你就可以通过谷歌找到自己的车钥匙了。
这些变革为新产品、新业务和新型人类活动创造了机会。它们为新的设计实践领域创造了机会,但对于制作单个物品的工匠来说高效的设计方法,并不能适用于开发服务系统的团队。为了利用现在的机遇,设计师必须开发新的工具、新的方法和新的语言。
服务工艺需要新的语言——手工艺中没有的语言。服务工艺对新语言的需求至少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服务工艺是在团队中进行的。每个团队成员都希望知道自己的期望和他人期待的回报。沟通(Communication)是关键。必须向团队中的每个人明确说明流程、目标和对策。设计师需要新的语言来相互交流复杂的项目。手工艺没有这样的语言。
其次,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物质的。比尔吉特·马格指出,服务是在交付点制造出来的。* 其本质与其说是实体,不如说是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服务是有生命的。反馈和对话(会话)显得尤为重要。设计师需要新的语言来帮助他们讨论行为。手工艺没有这样的语言。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比尔吉特·马格(Birgit Mager),《服务设计:综述》( Service Design: A Review),科隆国际设计学院,科隆,2004年。
第三,系统往往在同一时间只能显示几个方面特质。理解整个系统可能会很困难。在服务工艺中,设计的最终目标无法被直接或完全看到。它必须总是被部分地观察到,通常只能通过代理或中介的方式。试图理解构成亚马逊等在线服务的系统集群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无处立足,无法获得完整的视角。通过网络浏览器观察亚马逊就像通过花园围墙上的一个门上的钥匙孔观察凡尔赛宫一样;你能感觉到几个部分,但不容易掌握完整的结构。至少对大多数参观者来说,喷泉的复杂管道几乎是看不见的。更为棘手的是,电子系统变化频繁。设计师需要新的语言来表现动态系统。手工艺没有这样的语言。
一种思考生命系统的语言对于设计实践变得至关重要,至少在服务工艺领域是如此。
学习一门新语言可以扩充我们的词汇库。新词可以让我们思考新的想法。更多的词汇可以让我们做出更细致的区分。我们的思维和交流变得更精确——我们变得更有效率(efficient)。我们可以在更深层次上工作,承担更复杂的任务——我们变得更有效力(effective)。 我们对工作和自身的看法更加一致——我们变得更加整合(integrated)。
- 控制论是设计新语言的源泉
40 年前,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在《形式综合论》(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一书中描述了建模在设计实践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的10年中,设计实践的大部分都依赖于建模。设计师们已经开始发展讨论行为的语言——理解动态系统和可视化系统信息流模式的方法。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形式综合论》(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年。
如今,在设计实践中发现的大多数模型都非常具体地针对手头的情况。设计师们很少把他们正在建模的情况看作是更大类别的一个例子,因此也很少借鉴更广泛的框架作为建模的基础。可以肯定的是,设计人员已经形成了一些建模惯例,如网站地图、应用流程图和服务蓝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建模的惯例在设计实践中仍然没有得到广泛的分享或明确的定义。
在设计话语中,大多数框架都是从社会科学和符号学中「精选」出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设计师并没有为他们的建模建立坚实的基础或有组织的系统。理查德·布坎南在修辞学框架内对设计的表述——「作为修辞的设计」——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理查德·布坎南(Richard Buchanan),《设计与新修辞学:文化哲学中的生产性艺术》(Design and the New Rhetoric: Productive Arts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Philosophy and Rhetoric,Vol. 34,No. 3,2001年,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笔者们提出,控制论是设计实践框架的另一个丰富来源,与社会科学、符号学和修辞学类似。我们还建议把控制论作为一种语言——一种自我强化的系统,一种系统的系统或框架的框架,来丰富设计思维。
04 为我们的设计建模的控制论框架
04 为我们的设计建模的控制论框架
多数设计实践都能归结为两个模型:一个是现状模型,另一个是理想状态模型。亚历山大指出,需要从具体表现的复杂性中抽象出现状的本质。对现状进行抽象可以让我们更容易考虑有意义的改变,找到我们可能更喜欢的替代方案。亚历山大还强调,需要让模型可见,为我们自己和他人提供分析和讨论的表征。*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 同上。
控制论为理解和改进我们设计的事物提供了概念框架。
控制论的核心是一系列描述动态系统的框架。这些框架分别为试图理解、管理或构建动态系统的任何人提供了有用的模型。当设计从手工艺转向服务工艺时,这些框架共同提供了设计所需的大量新语言。
在我们的教学和实践中,我们发现七个控制论框架特别有用。
1.一阶控制论系统
一阶控制论系统能够检测和纠正误差;它将当前状态与期望状态进行比较,采取行动以实现期望状态,并测量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恒温器-加热器系统就是一阶控制论系统的典型例子,它能将温度保持在设定值。
一阶控制论系统为描述简单互动提供了一个框架。它引入并定义了反馈。它将互动定义为信息在系统及其环境中不断循环流动。它将控制(control)定义为系统保持与其环境的关系。它形成了目标、活动、对策和干扰相互关联的一致性,彼此相互意指。
该框架对于设计人员思考界面问题非常有用。它为模拟人类与工具、机器和计算机之间的基本互动提供了一个模板。它还为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互动或计算机网络上运行的进程之间的互动建模提供了模板。
2.必需变异度
罗斯·艾什比对「必需变异度」(requisite variety)的定义为描述一个系统的极限提供了一个框架——在什么条件下它可以存活,在什么条件下它会衰败。例如,人类的变异度足以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调节体温;如果我们太冷或太热,就会很快死亡。
该框架非常有用,因为它迫使设计者在描述系统时更加具体。它为与目标、执行器和传感器相关的对策提出了明确的范围、分辨率和频率定义。该框架还有助于讨论目标的有效性。我们在设计系统时应该承受多大程度的干扰?系统的额外变异度的成本是否与干扰的额外变异度的概率相匹配?
3.二阶控制论系统
二阶控制论系统将一个一阶控制论系统嵌套在另一个一阶控制论系统中。外层或高层系统控制着内层或低层系统。控制系统的行动设定了受控系统的目标。增加更多层次(或「阶次」)重复了嵌套过程。
二阶控制论系统为描述嵌套系统更复杂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框架。该框架为人类与设备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精密的模型。一个有目标的人采取行动,为巡航控制系统或恒温器等自我调节设备设定目标。
该框架还可用于复杂控制系统的建模,如GPS引导的自动转向系统。它也适用于生态、组织或社会控制系统的建模,例如保险公司、疾病管理机构和病人之间的关系。该框架还为「用户动机」(user motivation)的讨论提供了一种建模方式,在软件和服务系统的设计过程中,「用户动机」经常会影响到目标的层级结构。
4.会话、合作与学习(参与式系统)
戈登·帕斯克将会话(conversation)定义为两个二阶系统之间的互动。* 该框架区分了关于目标的讨论和关于方法的讨论,并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或温贝托·马图拉纳所说的「行动的互感协调的互感协调」(the consensual coordination of consensual coordination of action)——提供了建模基础。它还区分了自身导向(控制)和他者导向(沟通)。帕斯克在讨论协作和学习时也使用了该框架。 迈克尔·乔根(Michael Geoghegan)诙谐地说:「老鼠教猫……当然……猫也会教老鼠。」*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Introduction”,Soft Architecture Machines,(by Nicholas Negroponte),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5年。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迈克尔·乔根(Michael Geoghegan)和皮特·艾斯蒙德(Peter Esmonde),Notes on the Role of Leadership and Language in Regenerating Organizations,Sun Microsystems,Menlo Park,California,2002年。
该框架有助于为更大的服务系统建模,而交互设计的许多产品就位于其中。它为开始模拟社群、交易和市场,以及谈判、合作和协作等互动提供了基础。
会话框架提出了一种理想:两个二阶系统进行协作。将这种人-人互动模型与典型的人机交互模式进行比较,会发现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今,典型的人机交互框架可以最好地描述为一个二阶系统(人)与一个一阶系统(设备)的互动。设计二阶软件系统来理解用户目标并帮助其形成目标,为人与计算机的合作了一种新方式。*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保罗·潘加洛,“Participative Systems”,a present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pangaro.com/PS/
5.生物成本
生物成本(Bio-cost)的概念源于作者与迈克尔·乔根之间的对话。 我们将生物成本定义为系统为实现目标所付出的努力。*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迈克尔·乔根,同上。
该框架有助于评估和比较现有的和待提议的互动方法。也许可以测量生物成本,从而使「易用性」的概念更加具体。我们推测,生物成本框架可能有助于开发用于评估软件可用性和服务质量的关键绩效指标(KPI)系统。
6.自创生
弗朗西斯科·瓦雷拉、温贝托·马图拉纳和里卡多·乌里韦提出了「自创生」(autopoiesis)或「自我制造」(selfmaking)的概念,用以描述系统维持自身和实现自主性的过程。*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里卡多·乌里韦(Ricardo Uribe) “Autopoiesis: The Organization of Living Systems, Its Characterization and a Model” Biosystems,Vol. 5 (1974),第187–196页。
该框架对于讨论组织和社群——它们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自我维持——非常有用。它为组织设计者带来了希望。 (作者意识到,对于社会组织是否适用于最初的、严格的生物学意义存在分歧;但我们认为,无论如何,自创生概念都是应用于设计的一个独特而有力的隐喻。)
7.进化
迈克尔·乔根指出,「所有的进化都是共同进化。」* 种群随着环境的变化(干扰)而变化。相应地,新的种群的新行为方式,也会引起环境的变化。当然,作为一门科学的起源,自然选择(或自然毁灭)进化论的观点是先于控制论的,但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待进化论,则扩展了该早前框架的范围和价值;例如,必需变异度可以被视为进化的机制,而突变则是变异度的变化。此外,从控制论的角度来描述进化论可以加强控制论框架,使其具有某种完整性。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迈克尔·乔根,同上。
该框架对于讨论服务和企业的进化以及创新过程都很有用。一些著名的设计思想家,如约翰·莱茵弗兰克(John Rheinfrank)和奥斯汀·亨德森(Austin Henderson)*,已经开始讨论为涌现行为和进化而设计的问题。设计实践的产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他人的使用和自己的设计而不断进化,这仍是一个新观点。我们相信,该理念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并成为设计领域的主要趋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建立进化模型的框架将非常有用。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作者与被引用人之间的讨论。
这七个框架在很多方面都很有用,例如:分析现有系统;比较起初看似截然不同的系统;辨别并组织互动模式;以及评估所提出的设计是否适合其环境。这些框架适用于多种尺度:人与设备之间的简单互动;组件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人与人之间通过设备或服务的互动;人与企业之间(C2B)和企业之间(B2B)的互动;以及市场内部的互动。
这些框架还为设计提供了一种展望未来的方法,并提出了设计实践——软件应用程序和服务的开发——可能从中受益的研究类型。对于设计研究来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能对用户目标建模的系统、能帮助用户建模并明确自身目标的系统、能促进参与的系统、自组织系统以及能不断发展的系统。
05 为我们如何设计建模的控制论框架
05 为我们如何设计建模的控制论框架
上一部分介绍了控制论框架在设计实践中的应用。它强调使用这些框架来模拟现有的情况,并想象理想的情况。该部分的重点是使用控制论框架来为我们的设计建模。本节的重点是使用控制论框架来为我们如何设计建模——即为设计过程本身建模。另一种方法是对设计过程进行设计,即使设计过程适应其环境。在这里,控制论框架同样可以派上用场。
控制论为理解和改进设计过程及其结果提供了概念框架。
我们在上一节中介绍的七个框架也可以为设计过程建模:
1.一阶控制论系统
设计是一个控制论过程。它依靠一个简单的反馈循环:思考、制作、测试(用沃尔特·休哈特的话来说,就是「计划、执行、检查」)。* 它要求在循环中不断迭代。 它通过创建精确度越来越高的原型来改进事物,向目标靠拢。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沃尔特·休哈特(Walter Shewart),Statistical Method from the Viewpoint of Quality Control,1939年。
用赫伯特·西蒙的话说,「设计就是设计行动方案,目的是把现有的情况转变为理想情况。」* 艾伦·库珀称这一过程为「目标导向」*(goal directed)。当我们进行设计时,我们试图实现目标,通常是将我们希望使用我们产品的人的目标形象化。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9年。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艾伦·库珀(Alan Cooper),The Inmates Are Running the Asylum: Why High-Tech Products Drive Us Crazy and How to Restore the Sanity,SAMS,1999。
作为反馈过程的设计模型同样适用于传统手工艺模型或新型服务工艺模型的设计。在这两种情况下,设计者都依靠反馈。不同的是他们的原型的性质,以及他们将目标与产品分开表述的程度。
2.必需变异度
设计团队、产品开发团队或整个公司(以及单个设计师)都具有变异度,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可以带到项目中的技能和经验。我们可以根据团队或个人带来的的变异度来评估他们是否适合完成某项任务。团队是否具备成功完成任务所需的变异度?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任务的目标和可能出现的干扰。
3.二阶控制论系统
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描述了一个他称之为「自我引导」(bootstrapping)的过程,其中涉及三个嵌套的控制论系统。第1级是「基本过程」(a basic proces)。 第2级是「改进'基本过程'的过程」。第3级是改进「改进'基本过程'的过程」的过程。
这是一个例子:约翰的团队负责生产一个新的小部件——这是1级流程。约翰开始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周五下午的啤酒聚会),让他的团队讨论问题——这是2级流程。他们在会议上提出的想法得以实施,从而降低了小部件的缺陷率。管理层要求约翰分享他的改进之处,并决定要求全公司每周五下午举行啤酒聚会——这是3级流程。
约翰·莱茵弗兰克(John Rheinfrank)指出,在创建持续的质量管理和建立真正的学习型组织时,需要三个层级的系统。*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作者与被引用人之间的讨论。
4.会话
设计是设计师与客户、设计师与用户、设计师与自己之间的会话。设计涉及目标和方法的协调。
从会话的角度来构思设计具有广泛的意义,它挑战了设计者作为专家的角色,而将其塑造为促进者(facilitator)。 (关于这个观点的更多信息,请见后文。)
5.生物成本
罗伯特·波西格曾雄辩地论述过「精力陷阱」*(gumption traps),即人们丧失维持高质量工作所需的能量的方式。精力陷阱是设计过程中生物成本的来源。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罗伯特·波西格(Robert Pirsig),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 An Inquiry into Values,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New York,New York,1974。
*译注,「精力陷阱」这一说法出自《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通常由于一些琐碎且不相关的问题所引起,使得开发者在解决一个简单问题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一些不相关的问题,从而感到沮丧和挫败。
6.自创生
设计专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如何才能对设计实践进行持续的学习。近年来,一些大学已经开始授予设计学博士学位,但设计研究还很年轻,相对来说尚未成型。维持其发展所需的反馈系统尚未建立。设计人员需要一个自我维持的学习系统,其组成部分可以自我创造和自我再创造:课程必须包含「实践」,同时还要获取学习的过程,并维持已经存在的过程。七种控制论框架的内在机制是让设计界和支持设计界的机构(学校、咨询工作室和企业设计办公室)明确了解这些活动的机制。
7.进化
设计人员也缺乏改进工具和流程的工具。进展缓慢,创新不多。全球化可能会给当前的环境带来压力,迫使我们进行更快速的变革。
06 建构主义观点——设计即政治
06 建构主义观点——设计即政治
设计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反馈回路,不仅仅是一个自我引导过程,甚至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会话。考虑到二阶控制论的设计方法必须将设计牢牢扎根于政治之中。它将设计视为共同建构(co- construction),不仅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而且就问题达成一致。它承认霍斯特·里特尔所说的设计师与客户之间「无知的对称」*。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On the Planning Crisis: Systems Analysi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Bedrifts Økonomen. 8 (1972): 第360–396页。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译注:无知的对称,symmetry of ignorance,里特尔认为解决问题所需的知识分布在许多专家身上。因此专业性和无知对称地分布在参与解决问题的所有专家身上,没有人因为自己的专业地位而知道得更多。此处是只设计师与客户都有自己的专业盲区。
对里特尔来说,设计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团队在确定设计内容时所涉及的众多问题。他的这一观点促成了创建基于问题的信息系统(IBIS)的早期工作,这为设计原理的最新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该研究仍是一个持续探索的领域。*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 “Issues as Elements of Information Systems”, Working Paper No. 131. Berkeley: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年。
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指出了用客观术语定义系统的局限性。冯·福斯特问道:「观察者的作用是什么?」*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Disorder/Order, Discovery or Invention”,in Disorder and Order,Proceedings of the Stanfo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Paisly Livingston (Ed.),1981年。
霍斯特·里特尔指出了用客观术语定义设计的局限性。设计者经常把他们的工作描述为解决问题,但里特尔问:「这是谁的问题?」他指出,问题的框架是设计过程的关键部分。他认为,就问题的定义达成一致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还指出,有些(「棘手的」)问题是无法达成一致的,例如,在现代,为巴勒斯坦带来和平或建立全民医疗保健。*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和梅尔文·韦伯(Melvin Webber), “Dilemmas in a General Theory of Planning”,Panel on Policy Sciences,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4 (1969): 第155–169页。
里特尔还指出,如果设计是政治性的,那么论证(argumentation)就是一项关键的设计技能。他是一位具有物理学和运筹学背景的设计理论家,受到控制论的影响,认为设计不是客观的而是政治性的,因此他根植于修辞学。里特尔的结论与具有人文学科背景的理查德·布坎南如出一辙。这一联系非同寻常。\
07 呼吁课程改革
07 呼吁课程改革
我们的文化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不亚于孕育了设计行业的工业革命。向知识服务型经济的持续转变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深刻改变设计实践。
设计教育工作者需要应对这些变化。
控制论可以帮助设计师理解他们所面临的复杂新世界。控制论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为设计提供信息:1)为人与人、人与机器或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建模;2)为发生大量互动的大型服务系统建模;3)为设计过程本身建模。
随着控制论和设计方法运动创始人们的离世,* 他们所习得的许多知识可能会被后人遗忘的风险也在增加。这将是一场悲剧。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 戈登·帕斯克于1996年去世;海因茨·冯·福斯特于2002年去世;霍斯特·里特尔于1990年去世;布鲁斯·阿彻于2005年去世。
我们敦促设计教育工作者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设计教育方法,采用系统的观点,在教学中融入控制论的语言和修辞。
扩展阅读
扩展阅读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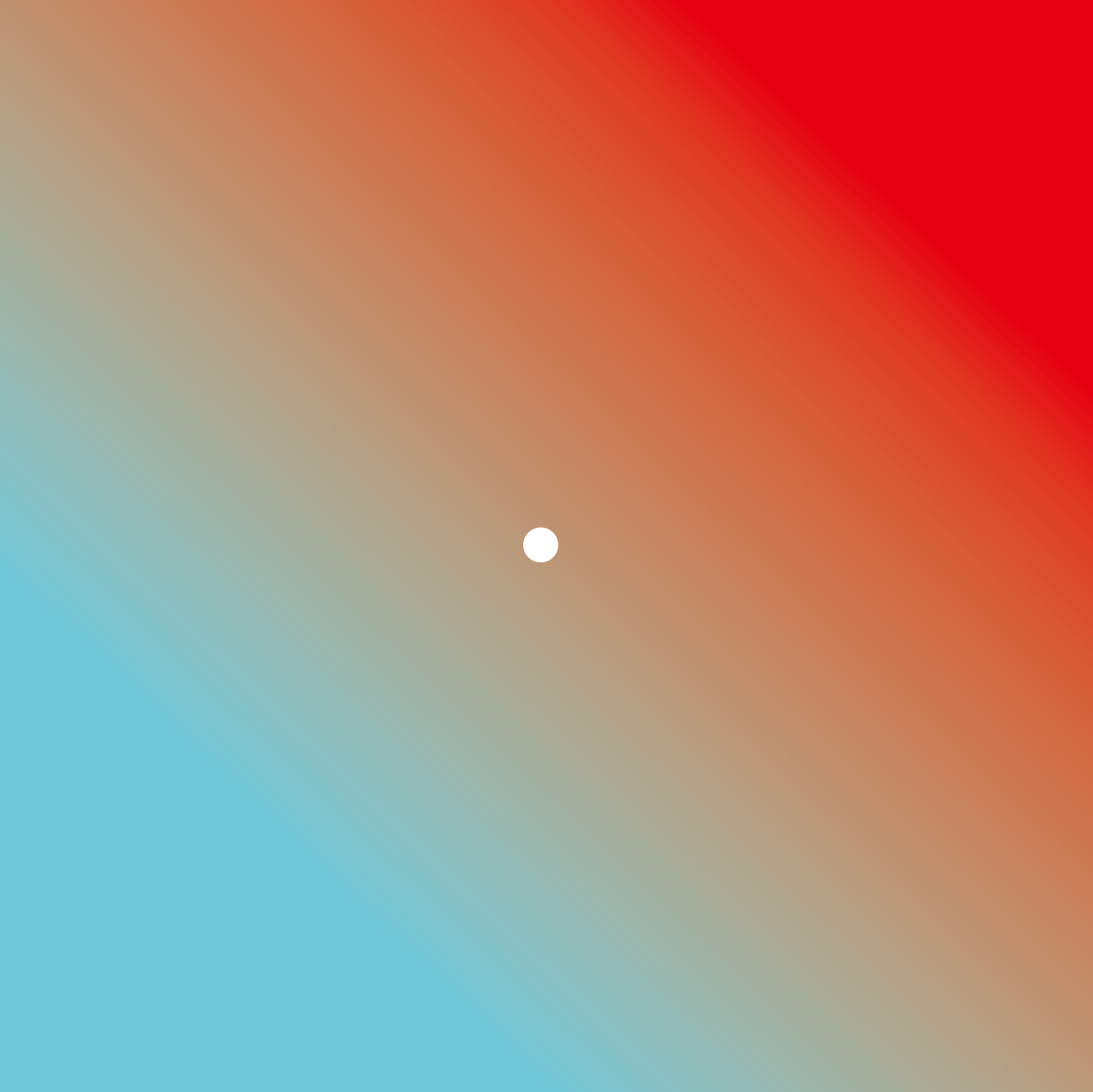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