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一、 2006:雨幕
一、 2006:雨幕
读小学时,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经常被父母带到医院。
虽然印象里小时候的自己确实没少感冒发烧,但那段时间倒不是因为这些毛病,而是视力在下降的同时又到了换牙的年龄。先是有那么几颗顽固的牙不愿意掉落,然后又是新长出的牙总有些歪斜,于是我就这么熟悉起了去往儿童医院的公交车。
比起换牙,反倒是近视的问题让我更头疼一些。
低年级的学生会有老师的定期家访,而那段时间老师总会提到我上课的时有眯着眼睛看黑板的习惯,要家长注意一下我的视力。偏偏当时有什么“假性近视”的说法,家里老人认为“早早地戴上眼镜,以后视力就没有恢复的可能了”不愿意早配眼镜,反倒是让我作业写完之后对着窗户外面,漫无目的地“远眺”个十来分钟。
老人们想出的另一个办法,是用能不能看清电梯轿厢里的广告来判断我究竟需不需要戴眼镜。那段时间里,超市促销的广告变成了辣椒酱,又变成了麦当劳的新品。广告的字号虽然越变越大,但家人却总能找到几行小字,考验我到底能不能在不眯着眼的情况下把字读出来。某天外婆找出一行诸如“图片仅供参考”的小字让我读的时候,我也只能摇摇头表示自己看不清了。
大概是在那之后的某个周末,一家人围在一起看电视剧的时候,大概是电视剧演到了相似的情节,外婆忽然地说了一句“我真想把自己的眼睛捐给他”——不用说,这其实指的是我。
意料之外的尴尬被大人们熟练地岔了过去,好像只是每天发生过的无数个会被遗忘的片段一样。但确实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改变。过后几天和爸妈提到有颗牙又开始松动起来的时候,爸妈突然一致同意等到周末的时候就去把这颗牙拔掉,顺便配一副眼镜。
——其实那颗牙倒也没有多碍事,可能拔牙才是顺便要去做的事也说不定。
坐电梯下楼的时候,爸爸指着电梯里刚换上的麦当劳广告,问我这是什么。
记得那是吃的时候要拆开调料粉,把它和薯条混在大纸袋摇匀了再吃的薯条。换上这份广告以来,我已经被问过好几次上面的内容,所以回答得也有些心不在焉。
“配完眼镜,我们就去吃这个吧。”
配眼镜的过程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用来测试近视度数因为需要更换镜片,架在鼻梁上实在是有些太沉。加上第一次戴眼镜时还不适应镜片,走起路来实在是有些头晕。拔牙的过程则是连这些细节也没留下,只记得麻药有一股浓到发苦的草莓香精的味道。
“那副眼镜,今天不拿走吗?”
“今天不配眼镜。过两天我们去眼镜店配一副好看的。”
“这个棉球还有多久可以吐掉?”
“医生说要半个小时吧,那今天是吃不上薯条了,等到配眼镜那天再说吧——你看,外面的雨多大。”
我看向医院的落地窗外。或许是因为刚配好的眼镜又被摘下,眼前的小雨细密得像是青灰色的纱帘,激起的水雾让远处的高楼大厦蒙起一层白色的轮廓。
我也点点头。其实自己并不是那么想吃薯条,我这样想。
——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我和爸爸坐在穿行在雨雾中的公交车的情景。南方的夏天,下雨总会被埋怨成“下开水”,但那天的雨像是秋雨,让人心情畅快但又隐约勾起一些遗憾。被雨幕笼罩的道路显得有些陌生,公交车也谨慎地放慢了速度。远处的立交桥像是通向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
——不,也许真的通向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也说不定。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类似的雨幕,也再没有仅仅因为下雨,就感到城市和周围的世界能够那样陌生了。或许正是因为没有眼镜,才能看到那样细密的雨雾吧。
模糊的雨和模糊的记忆一起留在了2006年。
轻松惬意的儿童时代。没有和大人一起完整看过的电视剧、同学之间的勾心斗角、隔着门听到的外公外婆回到老家前与父母的争吵、报纸中的“钉子户”、“超越保八”之类的看不懂的名词。只要隔着回忆的雨幕看回去,它们就会显得如此模糊。也没有人会指责自己把事情看得如此模糊。
2006年,小学时代的故事。
二、 2010:被挥霍的午后三点
二、 2010:被挥霍的午后三点
初中时代总有一些当时看着让人觉得矫情的语文阅读题。很庆幸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其中不少文字还是那么矫情。
但有几篇文章的内容我还记到现在。譬如有一篇文章写,午后三点是一个过于美好,以致于人们永远记不起来那个时候自己在做什么的时间段。
——现在想想我大概就是被这篇文章害了,直到现在还会不自觉地注意自己在那个时间在做什么,而且总是拿不出来能够反驳这篇文章的例子——特别是在读初中的时候,课上讲了什么哪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何况也谈不上“美好得让人记不住”。
另一篇文章的内容我记得更清楚一些,题目应该是叫《生命是用来挥霍的》。作者说“挥”是一个有动感的字,“霍”则显示出一种潇洒。作者用的大概是《海上钢琴师》还是哪部电影的例子,从那以后我就记着这部电影,想看看“挥霍”到底要怎样变成有正面色彩的句子。
可惜初中的时候是没看成这部电影。真到了运动会之类的场合,广受大家欢迎的还是变形金刚这样的大片——现在想想自己听Linkin Park的习惯也是那个时候不想显得太落伍才养成的,没想到一直听到了现在。
老师们——特别是有一些审美理想的语文老师——对于我们的审美多少是有些痛心疾首的。但大部分时候老师拯救我们审美的尝试往往会变成她口中的“对牛弹琴”。
“你看看现在的学生,我给他们讲了一节课的《红楼梦》,他们竟然一点感受都没有?”
“啊,啥感受,我也没感受。”
——说这话的是我们教物理的班主任。大概是语文老师觉得我们在艺术上的审美实在无可救药了,语文老师后来就不太和我们讨论艺术啊、审美之类连她自己也讲不清楚的东西。
后来大概是某个周五午后三点——就当做是我为了让这段回忆比较切题而故意回忆的时间吧——语文老师神秘兮兮地给班级的电脑拷来了一部电影。是阿米尔·汗主演的《三傻大闹宝莱坞》。老师有没有在看电影前就向我们大谈特谈她的教育理想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回家以后,做老师的妈妈确实看得非常感动,按着我讲了不少她的教育理想。回到学校才知道,大家以及不少家长的感受也和我家的情况类似。
——爸爸是那个例外,他到现在还觉得这部电影的名字“傻得冒泡”。
总之大概在那一周,或者之后的某一种,我们的一篇周末作文就是对这部电影的观后感。我们应该写得还是很满意的,因为那之后语文老师没少把这个成功作为自己理想实现的证据向其它老师炫耀,毕竟其他学科也很少能有布置电影观后感的机会,传播教育理想的任务似乎当仁不让地就该由语文老师承担。
只是在那之后不久,语文老师就请了一个太长的病假。最早是由隔壁班的语文老师代班,后来变成了一位上了年纪,带着过于浓重的河南口音的特级教师来给我们上课,老师们都尊称他一声“L特”。上课举的例子也变成了《夜走灵官峡》、《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样的老课文。这位老师上课没有架子,知识点讲的也清楚,虽然只教了我们大概半年左右,但却意外很受我们的拥护,之前那位年轻老师的理想就这么慢慢地被我们放到一边了。
等到原本的老师回来后,我们也升入了毕业的年级。语文老师还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比如让我们每周在一个作文本上练笔一样地随便写上一千字,既不要求是完整的作文也不要求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只要写够字数就行。
这样的规则持续了一段时间,大家就开始叫苦不迭。初中作文似乎是六百字合格,这也就是说这个任务相当于变成了每周要写接近两篇作文的量——而且因为大家写的主题都不一样,老师也不会给什么批改意见。真有了要写作文的时候,这个任务就更是变成了纯粹的负担。
后来有一次收作业本的时候我问舍友:“你这礼拜写啥上去了?”
“我把那几只三菱笔的日语说明抄上去了,反正她也看不懂。”
“字数够吗,我是抄的水浒传的座次表。”
其实这种作业又怎么会有合格和不合格的区别呢。只是老师在练习册之外想到的一种锻炼我们的思路罢了。好像也是在这次收作业之后,老师再也没提过每周还要再完成这个作业。
就像是无数灵光一闪之后的沉寂,初中时代的精彩故事也有讲完的一天。潇洒地挥霍了一段时间过后,过去的快乐就像那个空洞的“午后三点”一样溜走了。午后三天仍旧每天都会来到,真要认真记录的话,也未必不能记录下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想了什么。但这个时间点究竟有多么美好,却真的像那篇文章一样记录不下来。
被潇洒挥霍的时间、操场上刚割过的草的芳香、跑道上拖着轮胎跑步的身影、和老师们一样笃信着理想,却在长大后发现当时的自己和当时老师一样,说不清自己那么相信的理想是什么。
2010年,中学时代的故事。
三、 2023:八月
三、 2023:八月
能够在这个时间还是学生,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因为知道身边的老师同学,以及留在家里的父母都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所以我也说服自己相信着。但终究不能时时刻刻都相信自己配得上现在的学历,所以偶尔还会感到缺乏自信。
——特别是在宿舍的时候,这种心虚总会趁虚而入。或许是宿舍西晒的原因,它就像是下午的太阳,或者冬天的大风一样,能够轻而易举地穿过上了年头的阳台门窗。
学校虽然声名在外,但不知道为什么宿舍环境反而不如中学。和舍友吐槽过几次以后,就连吐槽的动力也没了。躺在床上,发现就算是天花板上都有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已经发黑的污渍,只能咕哝一声,不舒服地挪成侧躺的姿势。
也不知道之前几代学生是怎么在宿舍生活的。桌面上有一个巨大的木头书架,却没有预留容纳哪怕是笔记本的空间,更不要说显示器了。听已经在这间宿舍住了四年的大哥说早在他住进来的时候,两个书架就已经这么立在书桌上了。这倒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书架的各层已经以一种相当危险的角度弯了下去。和这一点比起来,书架上和天花板那如出一辙的污渍都显得没那么让人难受。
可能是宿舍大哥也觉得宿舍的环境不太适合学习,又或者是宿舍大哥的专业让他离不开实验室。总之在某个下午,大哥回到宿舍发现我正在对着文献材料大发牢骚时,大哥颇为真诚又似乎带点同情地问我:“你们没有自己的工位吗?”
我哑然失笑。要是真能给我们配一个工位,就我这个一边看文献一边闲不住嘴的习惯,恐怕照样要被人赶回宿舍看书的吧。
在宿舍自习想要休息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何况宿舍大哥常年留守实验室,就算是外放电影也没人拦着。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到底能有多么散漫之后,我有时也会觉得“没有工位”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是没人唠嗑实在不适合看故事片——在微信上抓着朋友同学聊剧情实在是太唐突了,何况大家也很可能没有看过。想一想这种尴尬的可能性,想要和人聊天的念头也就自己消失了。
我大概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找来《八月》看的。如果不是因为《平原上的摩西》的评论提到了这部电影,我大概也不会知道这部电影吧。
如果是好看的电影,我一般可以在看过之后清楚地复述出剧情。对于那些特别好看,自己还坚信看懂了的电影,我可能还会产生写影评的冲动。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我会觉得自己并没有专业到那样的地步而仅仅满足于和朋友的闲聊,所以写出来的影评就会被我看得颇有分量——可能是担心心里的热乎劲过去之后就会发现这篇文章并不值得自己的如此重视也说不定。
但还有另外一些电影,自己明明觉得好看,也觉得从中咂摸出了一些味道,但却永远不知道应该从何下笔。《八月》就是这样。有篇影评颇为感慨地说“80后也到了拍属于自己的怀旧年代剧的时候了”,这么说来可能是我还没到那个年纪,非要去怀不属于我的年代的旧的原因吧。
但我确实有些从片中的小男孩里看到了我自己的朦胧的感觉。1980年代,改制的喧嚣和升学的压力纠缠在小朋友的暑假,但小朋友却完全读不出它的重量,任凭那些恍惚间改变了许多人一声的大事件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而自己还是那个挥舞着双节棍无忧无虑的小朋友。
除此之外,就是歌厅里的老年人唱起《海港之夜》的画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了吧。具有年代感的唱腔不知道从何学起,让人恍惚间回到自己的童年,在宴席上吃零食吃到耳朵发烫,并因此认定自己今晚回去以后一定逃不过一顿揍的日子。虽然从初中的时候就有朋友对我有过类似的评价,但心里总觉得自己既然不属于那个时代,恐怕是无论如何也学不到那种唱腔的,何况它也并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但自己又是多么喜欢这种不属于自己的年龄的感觉呢。
《平原上的摩西》也有这样一段情节。孤独地、融入不进家庭的傅东心旁若无人地唱起了《小路》。我的外公外婆会唱,妈妈会唱。而我也曾经在读书会的时候不经意地唱出过声响。
短暂的花期、预料不到的冰雹、朋友圈是青年学者离世的新闻、学校里是进入毕业季的同学的行色匆匆。
我知道我现在的忧愁或许是过于不合时宜,也太容易被掩盖了。但又觉得不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我又感觉自己的忧愁必须要用足够漂亮的方式传达出来。不然就像是鲁迅遇到乞丐时所想的那样,总感觉乞丐的姿态和语调可鄙。但我又像那个会不经意多想的鲁迅一样,总觉得自己不能那样可鄙,于是往往连有据可查的忧愁也说不出来,不然也不至于现在以这样混沌的方式表达一个自己都说不清起源的忧愁。
2023年,仍是学生时代的回忆。也是直到现在仍在重复的回忆。或许是从2006年就已经出发并且滑行到现在的回忆。或者启程于那片雨幕,或者启程于那些理想的喧闹。
但毕竟是真实的、不能丢掉的回忆。
(标题图为电影《八月》未采用的海报)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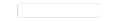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4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