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本系列旨在翻译Titus Burckhardt所著的Introduction to sufi doctrine。本系列为三大论集。
奥义的分支
奥义的分支
苏菲教义不是一种哲学,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人类的思维模式,它并没有被呈现为一种心理观点的同质发展。它必然包括许多观点,如果单独考虑它们的逻辑形式而不考虑它们都涉及的普遍真理,那么这些观点有时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正因为如此,一位大师可能会拒绝另一位大师的教义主张,而另一位大师的权威他仍然承认。
因此,例如,阿卜杜勒·卡里姆·吉利 (ʿAbd al-Karīm al-Jīlī) 的著作 Al-Insān al-Kāmil(《宇宙之人》)建立在伊本·阿拉比 (Ibn ʿArabī) 的教义之上,但拒绝了后者的说法,即神圣知识与每门科学一样,都依赖于其对象。他这样做是因为这种状态可能导致一种信念,即神圣的知识取决于相对的事物。现在,伊本·阿拉比将神圣知识指向神圣本质中主要包含的纯粹可能性,因此,除了术语之外,知识与其对象之间明显的二元性并不存在,他所说的依赖性只不过是可能与真实的基本身份的逻辑图景。【1】
【1.同样,根据奥利金的说法,神圣的预知与纯粹的可能性有关:它包括可能性,但并不决定它们,这就是为什么神圣的预知和人类的自由意志并不相互排斥。参见 Origen 的 Philokalia 关于命运的主题。】
苏菲教义包括几个分支,其中可以区分两个主要领域,即宇宙真理 (al-Haqāʾiq) 和与人类和个人道路阶段相关的领域 (ad-daqāʾiq),或者换句话说,形而上学和“灵魂科学”。不用说,这些领域并没有被划分为不可变更的各个部分。形而上学包括一切,但在苏菲主义中,它总是根据与精神实现相关的观点来设想。宇宙论是从形而上学衍生而来的,同时应用于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因此存在着宇宙振幅的心理学,就像存在着建立在与人的内在构成相类比之上的宇宙论一样。
为了把这点说得更清楚,有必要对这种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坚持。除了前面提到的 al-Haqāʾiq 和 ad-daqāʾiq 这两个领域外,还可以区分出教义的三个主要领域——形而上学、宇宙学和精神心灵学。这种区别对应于三元组:神、世界(或宏观世界)和灵魂(或微观世界)。反过来,宇宙论可以通过将形而上学的原则应用于宇宙来构想——这就是神在世界上的沉思——或者通过在宇宙和人类灵魂之间进行类比来构想。
此外,在其完整的发展中,宇宙论必然包含灵魂的宇宙现实,而没有任何精神心灵学可以将灵魂与宇宙原则隔绝开来。在宇宙的结构中,没有根本的断裂。就其自身方式而言,不连续性确实存在;它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没有弥合差距的统一原则,如果没有体现它的连续性的背景,不连续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因为在立场上,个体之间明显的差异性,他们各自意识中心的关系,只是他们独特的本质的标志,它“垂直地”超越了他们共同本性的“水平”平面。
至于一般个体意识与超越形式的智性层次之间的不连续性,它存在于意识的准物质层次上,它将其与处于形式层次上的其他意识“水平”联系起来,但同时也将其与它们独特的本质分开。
因此,根据事物的本质所采用或强加给我们的观点,现实是根据不同的连续顺序来看待的,只有形而上学才能包含所有这些不同的观点,并在宇宙的视野网络中赋予它们适当的位置。
宇宙学本身是一门分析科学,就该术语的原意而言,因为它将宇宙的每一个方面都归结为潜在的原则,归根结底,这些原则是主动和被动的两极,是塑造的“告知”原则,是可塑的质料。这些互补原则在初级统一体中的整合属于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不是宇宙学的领域。
刚才已经说过,苏菲心灵学并没有将灵魂与形而上学或宇宙秩序分开。与形而上学秩序的联系为精神心灵学提供了定性标准,例如世俗心理学完全缺乏的标准,该标准只研究心理现象的动态特征及其近因。当现代心理学自命不凡地宣称一种关于灵魂隐藏内容的科学时,它仍然局限于个人的视角,因为它没有真正的手段来区分将普遍现实与看似象征性但只是个人冲动载体的形式进行翻译的心理形式。它的“集体潜意识”与符号的真正来源完全无关;它最多是一个混乱的精神残留物,有点像海床的泥浆,保留了过去时代的痕迹。
对于世俗心理学来说,宏观世界和灵魂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在于通过感官之门到达灵魂的印象,但苏菲心灵学考虑了宏观世界和人类微观世界之间的构成类比。这种思想秩序例如占星术等学科,其象征意义被某些苏菲大师偶然使用。
苏菲之道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认识自己的方式,这与先知所说的话相一致:“认识自己的人(nafsahu)认识他的主”。诚然,这种认识最终适用于独特的本质,不变的自我(al-huwiyah),因此超越了任何宇宙学或心理学的观点,但是,在相对的层面上,就它涉及一个人的分裂性而言,关于自我的知识必然包括一门关于灵魂的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这门科学是一种宇宙论;最重要的是,这是对灵魂的始动因的歧视。
为了说明灵魂的辨别力是如何受到宇宙逻辑原则的启发的,可以引用某些非常普遍的灵感标准(al-wārid)来说明。然而,首先必须明确指出,这里所获得的灵感不是在先知性的灵感配给的意义上,而是在通常由精神实践引起的突然直觉的意义上。这种灵感的来源可能非常不同,但只有当它来自人类在时间之外的中心或来自“天使”时才有效,换句话说,它来自连接人与神的宇宙智慧的光芒。
当它来自精神世界时,它是具有欺骗性的,无论它一方面来自个人心理,还是来自心灵生活的微妙媒介,或者另一方面,通过来自亚人类世界及其撒旦极点的人类心理。来自天使的灵感,以及来自神的灵感,总是传达一种新的感知,它照亮了“我”,同时通过消解它的某些幻觉使它相对化。当灵感来自个人的心灵时,它代表着一些隐藏的激情,因此它有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并伴随着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自命不凡。至于来自撒旦极点的灵感,这些甚至颠倒了等级制度的关系,否认了更高的现实。
来自个人或集体灵魂的冲动不知疲倦地停留在同一个对象上——某种欲望的对象——而撒旦的影响只是暂时地利用了某种激情的诱惑:它真正寻求的不是激情的对象,而是对精神现实的隐含否定;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每次他的论点被摧毁时都会改变他的 “主题” 来破坏讨论。他争论只是为了给人带来麻烦,而激情的灵魂具有一定的逻辑连续性,因此它的冲动可以通过足够决定性的论证而被引导到合法的渠道,而撒旦的冲动必须简单地被拒绝。所讨论的三种趋势分别对应于重新融入本质、离心分散和“堕落”到亚人类的混乱中,它们在宇宙秩序中有它们的类比。印度教称它们为 sattva、rajas 和 tamas。
可能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多的苏菲书籍论述了美德,在美德中内识 (al-maʿrifah) 是道路的唯一目标,而对神的永恒专注是达到它所需的唯一条件。如果这些美德一定不能被忽视,那恰恰是由于任何意识模式都不能被视为在整体知识之外——或真理之外——又或任何内在态度都不能被视为具有某种独立性。“心之见”(ruʾyat al-qalb) 是对整个生命的知识。只要灵魂事实上(如果不是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否认真理的态度,那么心就不可能向神圣真理敞开心扉,而避免这一点就更加不确定,因为灵魂的领域(an-nafs)是一个先验的,由以自我为中心的幻象支配,而这种幻象本身就预设了一个盲点。【2】所有这一切都等于说,将神圣真理应用于灵魂的美德科学,直接涉及精神上的实现。它的标准非常微妙;它永远无法用道德准则来概括,它的固定只不过是范式。它的对象,即精神美德,是一种 “活生生的符号”,对它的正确感知取决于某种内在发展。现在,对于教义的理解来说,这不一定是正确的。
【2.同一个人总是对他的态度的虚假性有一定的认识,即使他的理性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古兰经》中说:“毫无疑问,即使人找借口,他也要意识到自己(或:自己的灵魂)”(75:14-15)。一个渴望实现神圣知识而又藐视美德的人,就像一个强盗想成为正义的人,却不归还他抢劫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菲方法在于保持灵魂对无限的流入敞开的艺术。现在,灵魂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即保持自我封闭,而这种倾向只能通过作用于同一平面的相反运动来补偿;这个动作正是美德。形而上学的真理本身是永恒的和静止的;美德将其翻译成“个人”模式。
精神美德不一定是直接意义上的社会美德,同一美德的外在表现可能会根据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某些苏菲行者通过穿着贫穷和破烂的衣服来表明他们对世界的蔑视;其他人则通过穿着华丽的衣服来肯定同样的内心态度。在这样的苏菲中,对他个人的肯定实际上只是对他所化身的永恒真理的屈服;他的谦卑在于他在不属于他自己的荣耀的一面中消亡。
如果苏菲美德在其形式上与宗教美德相吻合,那么它在沉思的本质上也同样不同。例如,对于广大信徒来说,感恩的境界是建立在对从神那里得到的好处的记忆之上的;它意味着一种感觉,即这些好处比所经历的痛苦更真实。在沉思的情况下,这种感觉让位于确定性:对他来说,存在于存在的每一个片段中的存在之繁盛比事物的界限要真实得多,一些苏菲甚至走得更远,因为对其他人来说,这只是对自己的痛苦否定。
可以说,精神美德是人类对神圣真理 (al-Ḥaqīqah) 的支持;它们也是那个真理的反映。现在,任何反思都意味着与其源头相关的某种倒置:例如,精神贫穷(al-faqr)是精神繁茂的反向折衷。真诚 (al-ikhlāṣ) 和真实 (aṣ-ṣidq) 是精神独立于精神倾向的表现,而高贵 (al-karam) 是人类对神圣宏伟的转变。【3】在这些“积极”的美德中,倒置在于方式而不是内容,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说是充满谦逊,而它们的原型是由威严和荣耀构成的。
【3.关于精神美德主题的最深刻的著作之一是伊本·阿里夫 (Ibn al-ʿArīf) 的 Maḥāsin al-Majālis。】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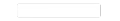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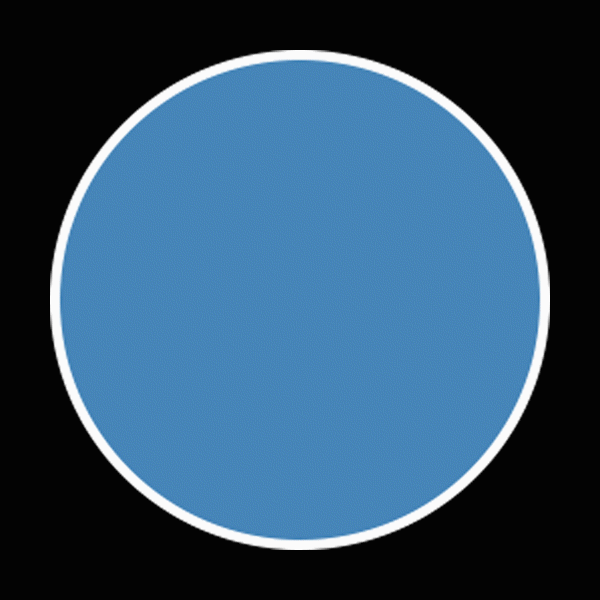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