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最近有好几件与此相关的“大新闻”。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一份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表示支持家长因未成年人在网游或直播平台一掷千金而向游戏公司申请退款,另一个则是两会期间有不少人大代表进行了相关的提案:比如建立网游分级制,通过人脸识别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行为和游戏时长等。
这些“大新闻”的出现,将应不应该进行以及如何进行未成年人游戏行为管控的讨论再次炒热。实际上,这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极为复杂、难以被盖棺定论的话题。因为它至少包含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等多个讨论维度。相关的实证研究与理论交锋每年都在更新。如果要全面展开讨论,恐怕几本书的篇幅都难以尽述。
不过今天我并不想讨论太多理念之争,而是想把目光聚焦在管控政策的执行层面。未成年人限制充值,限制游戏时长等听起来稳妥的举措到底为什么难以推进?其它国家又是怎样施行未成年人游戏管控的呢?
首先,我想和大家强调一个个人认为十分重要的原则:在订立法律法规时,其能否被有效执行才是至关(如果不是最)重要的。执行与立法如果出现大幅度脱节,那么讨论再多如何立法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甚至反而会降低法律的威严。
未成年人游戏行为管控领域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执法达不到立法的目的。很多人寄希望于不断地创立更严格的法律来倒逼执行,却不关注执法成本与执法层面的实际困境,这样往往会事与愿违。
这里我不妨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帮助大家理解,那就是未成年人去网吧的问题。从法律层面上看,我国禁止未成年人去网吧的立法进展非常快。01年4月发布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中,还允许8至18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定假日,也就是周末和节日(寒暑假不算)的每日8时到21时进入网吧,未满14岁要有监护人陪同。
这个规定乍看之下算是比较合理的了,然而在实际执法层面却不够严密,当时未成年人于非假日时段出入网吧完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种情形的恶果在仅仅一年后就被暴露了出来,几名未成年人于凌晨报复性纵火,在北京海淀区引发了25人死亡的“蓝极速网吧”恶性事件,震惊全国。
紧接着,立法与执法层面双双开启紧急应对模式。在执法层面,全国暂停网吧牌照下发,对黑网吧进行整治,并改善正规网吧的消防安全条件。立法层面更是快马加鞭,事件发生仅仅两个月后,国务院就出台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对网吧的开设、经营和管理进行了全面收紧。
这个于02年11月15日开始实施的条例,虽然后来经历了几次微调,但至今都是全国网吧管理领域的准则。其中21条明确规定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并且在31条中明确规定了,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由文化行政部门警告罚款;情节严重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执照。
那么这一严厉程度前所未有的新条例,在实际执行层面情况怎样呢?的确,从02年开始,很多大城市的网吧开始要求顾客在进店时登记身份证信息,但那时都是手动登记,基本上顾客只要写上个合格位数的号码就可以了,根本没有核验机制。当然,如果是北京五环内这样的地方,文化执法大队查的足够严,想钻空子的人就没法只靠报数就蒙混过关,但在城中村和五环外管理就相对宽松了,甚至有很多学生为了上网特意坐车去郊区,一个是便宜,一个就是查的松。
而三线以下城市里,大部分网吧老板都对青少年去网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是家长特别打过招呼的,不然根本不会理会。
记得09年左右,我去武汉旅游期间在城区上网吧,也没有查身份证,身边中小学生模样的玩家也有不少。这种执法不严的情况大概持续到了10年。之后,随着一代身份证逐渐被淘汰,网吧开机必须要刷有内置芯片的2代身份证,身份核验的问题才算是有了一个相对严密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到了10年那会儿,网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大部分人家都有了电脑(后来又有了智能手机),青少年去网吧上网已经不再是刚需。
回顾这段网吧管理历史,我们会发现,尽管我国从02年起就严格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但执行层面的脱节与疏漏,还是让其效果大打折扣。在很长时间中,法规执行严密的城区往往也较为富裕,家庭条件普遍更好,青少年家中的电脑普及率很高。而法规执行不佳的郊区与小城市,由于孩子们普遍家中没有电脑,网吧需求反而更加旺盛,这种执法需求和执法强度的矛盾,不得不说是一种倒置。
执法层面的疏漏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02年《管理条例》中有一条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每日营业时间限于8时至24时。”敢问从02年到现在,有哪个网吧严格遵守了这一条呢?哪怕是大牌的连锁网吧,不也都光明正大的有包宿服务,营业时间写的全天24小时吗?
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青少年游戏行为管控领域的“真问题”是如何执行,能否落地,而不是要不要执行。
比如至今已然推行了近13年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它的发展和实施历程又是怎样的呢?05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第一版《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其内容大致上就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0-3小时是健康游戏时间,3-5小时为“疲劳”游戏时间,超过5小时为“不健康”游戏时间。《标准》认为游戏收益是吸引玩家不断游戏的根本动力,因此只需要在游戏收益上做文章,据此给出了游戏必须3-5小时减半掉落,5小时以上0掉落并提示下线的规定。
05年8月开始,盛大、网易、九城等游戏公司开始进行防沉迷系统试验。07年7月要求所有电脑端网游实装该系统,但由于当时没有统一平台管理身份认证,且不同公司的执行标准也不统一,因此该系统的应用存在很大问题。比如有的公司规定一个身份证只能注册一个账号,有的则是无限制;有的公司可以验证身份证号和姓名匹配与否,有的随便填一个成人身份证都可以顺利过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管理部门又花了足足4年时间来完善核验机制。2011年7月China Joy举办期间,《关于启动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工作的通知》才正式下发,明确了公安部所属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需承担全国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工作,至此各家公司终于有了统一的实名制验证标准。但这时手机游戏还不具备安装反沉迷系统的条件,因此尚被排除在外。
不过哪怕到了这一步,管理部门也只是做到了识别注册身份证信息的真伪,未成年人只要找父母的身份证信息注册即可顺利规避。
9年过去了,手游也被拉进了实名认证的圈子,但目前也没有统一验证平台的搭建——因为没有一个平台可以接受来自全国游戏公司如此高并发的验证量。而抛开游戏内容本身的验证,也无形增加了游戏公司的成本负担,验证一条1毛5。而很多游戏公司吐槽,游戏内容本身就不是吸引小孩子的,花钱验证了1000条出现不了一个未成年人。而实际情况更为尴尬,每个在媒体上曝光哭诉无良游戏公司退款的孩子,都不是孩子拿自己身份证注册验证的。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问题所在了,网游实名制这项工作真的很难做,有资格掌握公民真实身份信息的,仅限于公安部门。单单是注册时的这一步验证量就已经很庞大了,需要企业与管理部门的长期努力、合作。这也就导致了实名制的弊端:游戏企业会因此掌握玩家的敏感身份信息,存在着泄密风险。何况,即便做到实名制,也不能将未成年用户完全挡住。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其它国家甚至根本走不到实名制这一步就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
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线下店还偶尔会要求顾客出示驾照或医保卡以购买部分游戏,但以steam平台为代表的线上平台兴起后,平台虽然也要求用户在查看包含血腥暴力内容的游戏时输入年龄信息,但却不会做实质性校验,仅仅有提示功能。
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种种分级制,其最大的功能在于提示经销商与购买者一款游戏可能包含的信息,而并不具备强制性。当然,不具备强制性不代表没有约束力,在媒体监督,行业自律,社会舆论等的综合影响之下,游戏是否进行了适当提示依旧会对游戏的商业表现产生巨大影响。
话有点说远了,回到身份认证这个话题。在其它有网络实名制的国家,青少年游戏管控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眼我国网游产业的“启蒙导师”,亦是网络实名制实施最早的国家——韩国的情况。在2012年之前,韩国是世界上仅有的法律明确规定的网络实名制国家。由于严格实名制的存在,韩国甚至可以出台“使用外挂就犯罪”的严苛条款。这也是导致早年间韩国游戏普遍反外挂能力薄弱的一个原因,因为在韩国用外挂真的有被抓的风险。
但在2012年底,韩国最高法院确认,网络实名制违反了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故废止了《信息通讯法》中的网络实名制规定。但韩国上网实名制的结束,不意味着网游实名制的结束。由于韩国的《游戏产业促进法》与《信息通讯法》是平级法律,所以网游依然需要实名制认证,但游戏企业不再有直接收集玩家身份信息的权力。原因是2006年、2012年,《天堂2》和《冒险岛》先后出现了千万用户级别的数据泄露事件,引起了民众的担忧。
为此,韩国网安部门紧急推出了i-pin认证制度,即韩国公民可以自行选择去韩国网安部门的官方网站注册身份证信息,获得一个i-pin码,再拿着i-pin码去游戏里提交,游戏公司再通过接入siren24等第三方认证平台,进行i-pin认证。这就等于加了二层防护,即便游戏公司泄露或者第三方认证平台泄露,也仅仅会泄露一个不可识别的i-pin码,而不是身份信息。
那么为什么韩国网游要那么特殊,在废止网络实名制的背景下依然“特立独行”?这就要说到11年时韩国一个颇为令人遗憾的社会事件:当时韩国某学校爆发了一起恶劣的校园霸凌事件,而整个社会的舆论并没有指向管理失职的学校,或者实施暴力的学生,而是莫名其妙地转向了游戏公司。数篇新闻报道坚称,霸凌事件的起因是受害者游戏玩得不好,受害者遭到歧视,才最终选择自杀,引发悲剧——游戏公司瞬间成为了暴风中心。
韩国政府也宣布,在继续维持游戏实名制的前提下,游戏主管部门文化体育观光部将开启严苛的限制消费制度,女性家族部则推出了游戏宵禁制。这次限制消费不仅覆盖了未成年玩家,连成年游戏玩家也被一并囊括。
2019年6月27日,文化体育观光部才终于宣布成年人限制消费制度废除。在此之前,韩国成年玩家每个月单款游戏最多消费不得超过50万韩元,即2800多元人民币。韩国的“土豪”们不知为此流过多少憋屈的泪水。青少年限制消费制度则延续至今,每个月最多消费7万韩元,即400元人民币左右。
这个韩国的青少年限制消费制度,也成为了去年版署发布的《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简称《防沉迷通知》的参考对象,不过我国的标准更严格,8-16岁每月充值最高200元。
而由韩国女性家族部负责的网游宵禁制度,其目的在于限制青少年在夜间前往游戏机厅和网吧,以免发生人身危险,而非完全禁止未成年人在夜间玩游戏(事实上也做不到),所以并不约束手机游戏。尽管如此,根据一名韩国议员的说法,还是有40%的青少年通过盗用身份证的办法继续游戏,宵禁对青少年夜间游戏时间的减少率仅为4.5%。
这个宵禁制度在被复制到国内时,也如限制消费制度一样被“加大力度”、“扩大范围”。《防沉迷通知》不仅将宵禁时间由韩国的0点至6点延长到22点至8点,还将手机游戏纳入到监管范围中。规定更为严格,执行中的困难更是不少。如果仍然仅以游戏注册实名制判断玩家是否是未成年人,那么就像老防沉迷机制一样,只需使用真实的成年人信息注册来规避监管。
而实际上,网络已经出现了各种成人账号出租、交易,甚至小卖部出现了“手机出租”业务。
这时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使用更严密的身份认证手段呢,比如人脸识别。这就又回到了执行成本与执行方式的问题上。
我们暂且抛开端游如何实现人脸识别的技术问题,单谈服务器压力。人脸识别和身份证信息识别一样,只有公安部有权来进行。那么哪怕只是在注册时进行人脸识别,其数据量之大就足以给本已不堪重负的公安部服务器造成巨大负担。如果还想实现“宵禁”,那么玩家就需要在登录时也进行人脸识别,这根本就不现实。况且,人脸识别的成本需要由游戏企业来负担,单次验证的成本就在0.5元左右(和移动支付不同,这个需要调用公安数据),如果要频繁进行人脸识别工作,游戏企业就会无力负担高昂的成本。
而且,如果出现人脸信息的泄露,那么,可能国内整个移动支付体系都会陷入危机。所以说,人脸识别这件事,最多也只能做到在注册时,要求用户进行一次人脸识别(事实上腾讯已经这么做了),指望依赖人脸识别实现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宵禁,根本不现实。这也是为何版署至今都没有强制各家企业推行人脸识别工作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不想,而是无法执行。
退一步讲,哪怕是所有现行网游都严格执行了实名制登录,那么青少年就没有游戏玩了吗?当然不是!
近两年火热的概念“超休闲游戏”,也就是没有付费入口,无需注册,仅有广告的微型手游在抖音大量投放,下载量惊人。没有注册和登录系统的游戏,怎么做身份验证?如果把超休闲也掐死,那在手机上装各种模拟器总管不了了吧,GBA、NDS、PSP那么多游戏,够不够玩?当年80、90后在学生时代,还没有智能手机,不也有不少人抱着电子词典玩个通宵吗?
我的一个好朋友是一所顶尖中学的老师,她说就算是游戏资源充足的现在,那些学生们在课间还是会十几个人围在电脑前玩扫雷。拼多多几十块就能买一个内置大量FC游戏的电子玩具,这又如何去管?
有一些人总是在期待,只要国家出台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就可以解决未成年人游戏的问题,却无视了近20年来我国在立法上早就“从重从严”的客观现实。在执行层面出现问题时,很多人直觉性地认为是立法不严,执行不到位,却忽视了很多规定执行的客观困难,对“严刑峻法”的合理性也缺乏反思。他们不断强调企业与政府部门在相关问题上的责任,甚至非常直白地唾骂与抹黑游戏本身,却忽视了青少年人的监护本质上还是家长的义务,孩子的健康成长根本上还是需要父母正确的引导和言传身教。
事实上,世界上大部分没有实现网游实名制的地区,都将青少年游戏管控的重点放在了家长引导层面上。日本游戏行业协会JOGA的官方网站上也给家长提供了异常实在的“防止未成年人氪金”操作指引:
- 信用卡放柜子顶层,不要让熊孩子拿到
- 多注意密码,没事儿勤改密码
其实国内也早就在推行类似的管理机制,拿腾讯已经运转了三年的“家长守护平台”为例,绑定信息后,家长可以通过该平台查看自己孩子微信号、QQ号的游戏登录情况,限制游戏时长和手段,实现远程管理。但又有多少家长愿意去学习和了解这样的机制,和孩子沟通,比较学习新事物哪里有一刀切地不让玩或者干脆不管来的简单?
逢年过节,我就会看到一些自家孩子年龄不大的亲戚,把手机交给孩子,让他们随便玩点游戏打发时间,不要来影响自己在酒桌、牌桌上热火朝天地社交。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总会想,到底是谁让游戏成了孩子的“保姆”呢?懒得应付孩子的时候,游戏是“好朋友”,想要孩子和自己沟通的时候,游戏又成了带偏孩子心思、离间亲子关系的“小人”,这是不是有点逃避责任呢?
此外,根据我的观察,越是对游戏不了解的家长,越容易采用错误的方法对待未成年人的游戏行为。对“无用”的娱乐行为的反感,对新事物本能的抗拒,对孩子脱离自身掌控的恐惧,最后都转化为对游戏的怒火,输出到开发者和管理者身上。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堵不如疏”的宝贵经验,早已被抛诸脑后。如此一来,我们虽有着世界上最严厉的电子游戏限制政策,但中国家长却还是常常在面对青少年游戏问题时感到束手无策,而我们的很多青少年也在步入成年后开始在游戏中报复性消费。
总而言之,要规范游戏市场,处理好未成年人与游戏的关系,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严格的行业规章,而是管理者、开发者和家长愿意真正正视游戏本身,客观认识游戏行业,用科学的方式考察、进而理解未成年人的心理需求。我们不能奢求这些深层次的改变一蹴而就,但我们希望在当下,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到相关法律法规在执行层面的困境,而不是总在立法层面大打嘴仗,进行价值观和立场的交锋。
历史一再证明,好的治理模式往往不是最严苛的,而是最符合人性,也因而最为高效的。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在管理未成年人游戏行为方面做得更好吧。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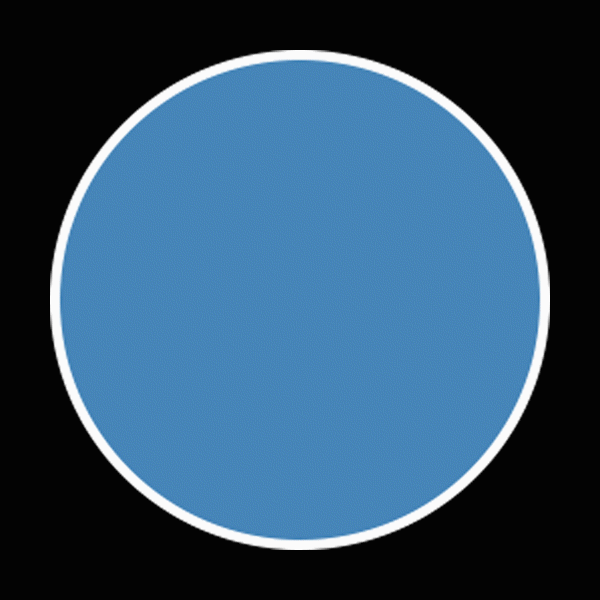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48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