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沙丘研究所是一个年轻的的独立组织,我们以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建筑学、城市学作为起点,创作一些文化、艺术方面的内容发布在网络平台上。沙丘的发起者是陈飞樾、李雅伦和任贝蕾,我们三个人在麻省理工和哈佛的设计学院念研究生。
取名叫沙丘,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两个字可以叫人联想到不断被形塑,也在不断形塑其他东西的流动景象。
虽然最近弗兰克·赫伯特的原著《沙丘》改编的电影快上映了,很多朋友和关注者也会问到这个问题,但其实我们取名的时候并非考虑到这一部作品。如果要为这个名字溯源的话,或许博尔赫斯的《沙之书》会是更适宜的参考。
“那本书像沙一样,无始无终。”虚构故事中,主人公每次翻开那本不可思议的小书都会落到一个不定的页数,看见不曾预料到的新文字、新插图。
互联网也具有一些“沙之书”的特征。因为信息无尽的流动和积累,这个虚拟世界会出现种种独特的地貌。它们不断变化;许多东西会施加影响或者形塑这些地貌。它们有些时候平淡、不可见,有些时候瑰丽多端,有些时候会成为互联网疆域中一片引人注目的奇观。所以在一片流动的大地上面,沙丘不断变动,不断被塑造,也不断向外界输出它的影响。
在尽量友善以及生活化的气氛中,我们分享一些知识和想法,这是我们从建筑学出发,发散到对于文学、艺术、哲学与各种当代具体媒介的理解。
建筑学如果不停向内卷曲,而圈内人每天又只求自说自话来寻求安全感,那这个学科就一定正在变成一潭死水。沙丘研究所能够在并不以建筑学作为重要拼图板的机核网内收获大家的阅读和关注,这很令我们开心。柯布西耶的那句话或许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启示:建筑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此前《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这篇文章,其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受建筑学训练的认知习惯。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中交互系统会引导用户从某一层进入另外一层。虽然是虚拟的,但这些界面同样是一种空间。于是从空间上出发,可以想象社交媒体里哪个环节更像是“街坊邻居门对门的拜访”,哪些更像是“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城市广场”,哪些是“私密的”,而哪些又是“公共的”。找到了这些原型后会发现,很多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时代的新东西或许本质上仍旧是人类早曾经历过多次的。我们在这些赛博空间中聚集、分散、交流、隔膜,或许仍然不过是挪用了我们在现实空间中曾经做的那些事情,只是变更了强度和速度。
不是所有造出来的房子就都叫建筑,也不是所有建筑都是造出来的房子。建筑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是指搞室内装修;建筑师不是模型工人,不是画图匠,不是软件工程师——虽然这些事情我们都得做——但是建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只是作为一门技术和手艺,是因为它对于学生提出一种知识素养上的要求,那就是要以空间的方式去思考问题,以空间的方式去认识世界。
我们相信一个扎根在建筑学中心位置的话题是“人与空间的关系”。我们也相信建筑学有它自主的力量,它不是哲学、语言学或者地产、规划局、政府领导和甲方爸爸的附庸——虽然在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扮演被动的角色——建筑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只是从别的学科那里攫取知识、搬弄概念,进行一些“建筑学特色”的化用,而是它自己作为一门自治的学科,一定也不断在给其他学科输出知识。
这种知识或许非常原始,但它是一项非常终极而深邃的原始话题,它询问的是人在空间当中存在的状态。这个话题无可替代,它也一定属于建筑学——当我们身处一种空间当中,我们会对自己身体周围的环境有所觉察,更会因为这种空间产生某种感受;当我们身处不同的空间,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语言对这种感受的描述在许多时候甚至显得苍白、无效和多余。写作者可以花很多篇幅去描述这种微妙的感受,这些文本或许让人看得云里雾里,但是一个人所需要的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进入那个空间。于是他就会明白:“啊,原来你说的是这样一种感受。”我们想说的即是,这种人类对于空间的觉察和感受,本质上也是一种知识。
在大多数时候,建筑是隔在我们和世界之间的那个东西,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中介去认识世界。海德格尔有过这样的表达:我们人类存在于世界的方式即为“栖居”,而人类的建造之物即是我们作为人之存在的体现。
“思想之音必须是诗意的,因为诗歌是真理的言说。”如果之前段落中的建筑学是作为一门理论学科,那么当它作为一门设计学科的时候,或许可以说,建筑设计就是以诗意的方式去预设人们将会怎样置于这个世界。
在专业课程之外,李雅伦有哲学上的背景,任贝蕾会对认知和交互方面有很多研究,陈飞樾对文学有强烈的兴趣。但是这显然并不代表建筑学的全部。所以我们想做的不是给建筑学下官方定义,也没有人能这样做,我们只是试图分享对它的理解和自身诚实的感受。
在中国古建筑领域,很多人肯定有比我们更完善的知识;我们三人也并未专攻建筑/城市信息模型,并不特别擅长于非线性造型和参数化的东西;在具体实践方面,我们有一些建成的小项目,但许多同龄人完全可能有比我们更深厚的实践经验。所以我们提供的是看待建筑学,或者用建筑学来看待世界的其中一种眼光。
我们想要尽量多提供原创而有趣的东西。
微信公众号是我们发起沙丘研究所之后首先运营的社交媒体,但几乎因机缘巧合投稿到机核以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收获了不少关注和阅读。当然,也像我们之前所表述的那样,机核最具魅力的还是其具备强烈在场感和社区感的交互强度。我们把知识或者说信息的完善过程看做不断渐进推动的“正题-反题-合题”过程,而文章投稿到机核以后,很多时候在评论区能够得到非常高质量的“反题”,这能够有益地帮助我们完善内容的创作。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把内容分为“沙丘词典”、“沙丘乐园”和“沙丘书言”和“其他”,但在机核上尚没有觉得有这个必要严格细分自己的内容。所以一般就把“沙丘词典”当做一个确实在不断更新的版块,其他部分就都以常规的文章形式进行投稿。
在“沙丘词典”(点击跳转)中,我们挑选一些设计、艺术领域高频使用的英语词汇,然后尽量对它们做出便于理解的解释。因为长期浸泡在建筑学中,我们三个人都观察到了一些中英语言上的差异,也体会到了不少两国教育问题上面侧重点的区别。因为种种这样的原因,不少英文舶来的“专有词汇”在中文建筑圈里面流通很广,但是大家并不对它具备相同的理解。我们因为自身的经历也心知肚明:一些同学根本不甚理解许多“新词”、“偏词”、“大词”,但是因为大家好像都口若悬河地谈论着它们,好像自己也就有这种义务去把它们挂在嘴边,或者至少用来装点一下自己的方案。因为种种这些情况,设计师在阅读和交流的时候常常望文生义或者鸡同鸭讲。
我们看重“语言”。我们希望在这个不清不楚、模模糊糊的世界里面,厘清一些词汇,搞明白一些概念,并且希望帮助逐步打造一个基本程度上的清晰度。文化上的活动以“语言”为地基,如果“语言”就是含混和粗糙的,很多文化上面的动作也就一定是含混和粗糙的。
就像之前所说,我们不希望给建筑学下官方定义。我们在做“沙丘词典”的时候也怀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无意去扮演某个绝对的权威,声称自己最中立、最客观,或者最面面俱到。而是说也像那个“沙丘”的比喻那样,我们在不断更新、扩充也不断回过头调整这些释义。
借助网络,读者也可以向我们提出补充和修正意见。这些我们都积极地采纳。
作为建筑学生,我们身边确实有很多同学朋友在转行或者寻求转行的机会,很多人也会说这是建筑学面临危机的体现。当然,“建筑学危机”这个话题肯定大过“青年建筑师转行”。“危机”这个问题放在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境下,应该需被给予不同的理解,它在理论与实践的两个框架下肯定也有很大的区别。对于经济增长打了一个寒噤的中国乃至全球,建筑学似乎无法很好地解决城市化进程放缓的问题,也无法根本性地治愈日益加剧的各种城市病。于是,年青一代设计师尤其感到前路未卜。
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讨论下,“危机”和“转行”牵扯到现在权力展现自身的媒介的转变。建筑和空间从前作为权力象征,拥有至高的地位,而现在它似乎正在逐步被一种快速更新并且不断增长的大众媒体所取代。
我们也无法忽视,仍然有很多人并不悲观地认为建筑学面临严重的危机,也不认为转行是一种逃避。这些建筑学面临的问题可以成为机会。从一个侧面来看,学科间明显的边界正在消解。不断有建筑师转行到地产、交互、媒体、人工智能等等方向,这些领域的边界因为这些人才的流动而被弱化;反过来,也正是因为这种边界的弱化,才容许了大量的建筑师得以快速转行。
上世纪60年代的一批激进建筑师虽然没有很多建成的作品,但是他们利用设计在政治文化上做的创新似乎是很多其他建筑师无法想象的。所以,如果真的要评判这个时代是不是建筑学的危机时期,或许还需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定夺。
沙丘研究所也是基于同样的跨学科的设计和研究成立的。在打破一些既定的学科边界和固有观念之后,设计更像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非某种具体的行为。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复合思维方式,它全面并且富有创造力。作为设计师,我们不断在研究和创作一些应该存在却尚未存在的东西。这种热情和动力不会消失,设计思维这种独特的方法对于任何工作都有很多意义。
再次谢谢大家的阅读和关注。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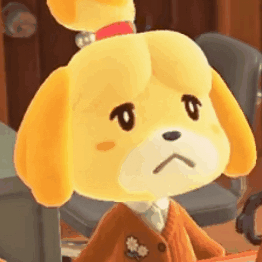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31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