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本文含有AI生成,请注意甄别
编注
近日,日本知名游戏设计师板垣伴信离世,享年 58 岁。其代表作有《死或生》(Dead or Alive,简称“DOA”)系列和《忍者龙剑传》(Ninja Gaiden)系列。
板垣因其“直言不讳”的性格受到游戏媒体的广泛关注。早年间,板垣因大肆抨击《铁拳》(Tekken)系列和原田胜弘本人,进而引发游戏媒体猜测两人剑拔弩张的关系。
2025 年初,原田胜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长篇文章,简要介绍了他与板垣伴信之间的真实情况。
本文由豆包 AI 进行翻译,笔者校对。为保证流畅阅读,文章格式稍有修改。
下面是正文。
前言
前言
嗯,我不确定你是怎么看待我和板垣先生的关系的,但可以告诉你,这很可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下面,我会大致梳理一下我和板垣先生的过往,并讲讲其中的关键事件。
不过,先给你提个醒:接下来要说的内容,本该是登在媒体访谈稿里的。我真心建议没耐心的格斗游戏粉丝现在就别往下读了。
不对,我要重新说一遍:这可是个郑重的警告。要是你只有普通人那般的耐心和常识,最好还是别继续读了。
非要读的话,你大概率会中途放弃,要么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要么就得忍受没完没了划屏幕的煎熬——哪怕你用的是 100 英寸高的竖屏手机也一样。
即便如此,我也已经省略了大部分琐事,只挑了些重要事件来讲。
我先把话说明白:我可是提前警告过你了。要是有人读完还敢说“太长了”,那我就先送你去见祖宗,然后再把你永久拉黑。
为什么?因为我早就说了:“别读这个”。
好了,我接下来要讲的事,都发生在过去的南梦宫(Namco)时代,和合并后的万代南梦宫(Bandai Namco)几乎没什么关系。所以,年纪小一些的朋友,还有在万代南梦宫合并后才入职的员工,就不用纠结这段背景了。
另外,要是有翻译错误,或者我没准确理解某些细节,也请多包涵——我的英语水平还停留在大学时代。
行了,该提醒的我都提醒了。你不该再往下读了,读了肯定会后悔。
初次接触
初次接触
那是 20 世纪 90 年代,《死或生》初代刚公布的时候。有一次参加游戏展,在返程的车站里,我碰巧遇到了世嘉(SEGA)《VR 战士》(Virtua Fighter,简称“VF”)团队的人 —— 他们后来成了世嘉 AM2 工作室的负责人。巧的是,板垣先生也在现场。
当时,《VR 战士》《铁拳》《死或生》这三个系列的核心人物碰巧聚到了一起,我们就决定趁这个机会,去新宿的一家居酒屋喝了几杯。
在居酒屋里,我和世嘉 AM2 的两位成员聊起了技术相关的共同话题,聊得很投入。那时候,南梦宫通过从世嘉挖来的工程师,和世嘉分享了一些动画控制技术。当然,没过几年,《铁拳》项目组就从零开始,独立研发出了自己的动画控制技术。
原田注:当时《铁拳》项目组积累的知识和基础技术,正是如今万代南梦宫人体动作开发技术的源头。有意思的是,很多万代南梦宫的员工都不知道这件事:在多边形时代,《铁拳》是万代南梦宫动画与动作控制技术的“鼻祖”。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显然不可能后来与樱井政博先生合作开发《任天堂明星大乱斗》(Super Smash Bros.)。
我和世嘉的负责人聊这些的时候,板垣先生听得很有兴致。后来,我们还聊了些和工作无关的游戏话题,关系也近了些。
有个瞬间,过了快 30 年我还记得:板垣先生跟我说,“原田先生,您这人很亲切,还挺风趣的。”那时候,板垣先生对我说话还用着敬语(当然,我对他也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对彼此都不算了解,关系也很正式,沟通时自然会透着股绅士风度。
板垣的“发现”
板垣的“发现”
在那次《VR 战士》《铁拳》《死或生》团队的人一起喝酒后,过了几个月,我又在另一个游戏活动上偶遇板垣先生。
他主动过来跟我说:“原田,你是早稻田大学的吧?我也是早稻田的,咱们在校时间有重叠,你得叫我学长。”
我回他:“就算我是学弟,咱们也没在同一时期上学吧?”
可他却说:“不对,我那时候天天忙着打麻将,花了七年才毕业。咱们肯定有重叠的时候。其实我还记得,上大学时见过你——你当时是帆船部的部长,对吧?”
没错,板垣先生早就把我的背景摸得一清二楚,还发现我是他的学弟。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以“学弟”称呼我,说话也用学长对学弟的随意语气,完全不用敬语了。
板垣媒体策略的开端
板垣媒体策略的开端
板垣先生不只是个游戏设计师或导演。更重要的是,他当时已经开始展现出作为制作人的才能了。
这是我在他离开特库摩(Tecmo)后,听他亲口明确说给我时,才彻底明白的事情。彼时,他就已经在认真思考,怎么通过营销和品牌建设,让《死或生》超越《铁拳》。
咱们再把时间往回倒一点。
那个时代,街机市场还很繁荣。世嘉和南梦宫是日本街机市场的两大巨头。它们不仅开发游戏,还在国内外运营自己的街机连锁店,在游戏发行和分销领域也占据了很大份额。
板垣先生很清楚,特库摩在营销和发行实力上,根本没法和这两家企业抗衡。于是,他开始探索媒体策略——不仅利用起纸质杂志,还用上了当时新兴的网络媒体。
别看板垣先生表面上情绪很外放,但他在分析资源和制定策略时,眼光却冷静又精明。在他的各种策略里,其中之一就是故意“碰瓷”《铁拳》,藉此吸引媒体关注。为此,他甚至会点我的名,批评《铁拳》的游戏设计之类的。
我得强调一下:这只是他众多策略中的一个,不是唯一的手段。
不对等的关系
不对等的关系
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媒体策略,《铁拳》项目组一开始都很困惑。
比如有一次,某本杂志用两页篇幅刊登了板垣先生的访谈,他公开批评《铁拳》,还点了我的名,语气特别激烈。在海外的杂志和网络媒体上,尤其是西方的游戏媒体,这种攻击更激烈,对《铁拳》和我的批评也更尖锐。
与此同时,南梦宫的上级却要求我保持完全沉默。换句话说,我被严令禁止以任何方式回应板垣先生的攻击。
这种“原田沉默,板垣攻击”的状态,大概持续了十年——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一直到 2005 年底《死或生 4》(DOA4)发售后,也就是 2007 年左右。
现在回头看,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板垣先生根本不可能建立友好关系。并且事实上,在那十年里,我也常在想:“板垣桑为什么偏偏盯着我、针对我呢?”
突如其来的“会面”
突如其来的“会面”
咱们把时间拉回 1998 年。有一天,板垣先生突然直接给南梦宫打电话,还点名要找我。
就像我之前说的,板垣先生当时已经开始实施针对《铁拳》的媒体策略了,也知道了我是他的大学学弟。当时我和他关系那么紧张,他这通电话让我十分困惑。
我小心翼翼地接了电话,他说:“你能来特库摩总部一趟吗?就你一个人来。”那感觉,就像中学时被不良学长叫到教学楼后面似的。
我当时还犹豫要不要拒绝,但最后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
我答应了他的请求,第二天一个人去了特库摩总部。到了之后,板垣先生亲自来接我,把我领进了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个被布盖着的东西,看着像街机机体。他像魔术师表演一样,猛地一把掀开了布。
罩布的下面是一台街机机体和 CRT 显示器,机体上展现出一样此前从未公开过的东西:《死或生 2》(DOA2)的开发版本——这款游戏后来在 1999 年秋天才正式登陆街机。“你是第一个看到这个画面的外人,”他说。
比起游戏本身,他这魔术师一般的举动更让我摸不着头脑。不过,他叫我来,主要有两个目的:
首先,他想让《死或生 2》的街机基板取得畅销。当时世嘉和南梦宫因为街机连锁店繁多,是街机基板的两大买家。按常理,他应该找南梦宫的销售团队。但他觉得那样还不够,想得到我这样的开发者的认可,认为只要我点头,南梦宫就会多买些基板。
其次,他还想测试《死或生 2》的表现,再看看《铁拳》项目组会有什么反应。要是我表现出不屑,他会认为《铁拳》技术更优;要是我表现出赞赏或不安,他会以此衡量 Team Ninja(忍者小组)与《铁拳》项目组的实力差距。
简单介绍完游戏概念后,他说:“来,试试看!”
在我按下开始键的时候,他直接坐到了我旁边,那架势好像马上要跟我对打似的。
在他无声的压力下,我选了“霞”开始游戏。刚玩了几秒钟,按了三次出拳键,他就问:“怎么样?感觉如何?”
我当时都懵了——才几秒钟,我能判断出什么啊?
我下意识地回了句:“玩着挺顺手的。”
我本来以为他会反驳“才几秒钟你怎么知道”,结果他却说:“看吧?我就说嘛,原田。”
那一刻,我是真的糊涂了:他是认真的吗?这难道是某种隐藏摄像头恶作剧吗?
公平地说,《死或生 2》哪怕是未完成版,在当时也已经展现出了很亮眼的技术水平。但他非要我立刻给出评价,还在我玩的时候不停地讲解,搞得我信息过载,脑子乱糟糟的。
后来,我从一位前 Team Ninja 成员那里听说,我走之后,板垣回到开发楼层宣布:“今天,我们赢了《铁拳》。”
我只是对他的做法感到惊讶,可他却把这当成了我被《死或生 2》的表现震慑到的证据。
板垣的分析与策略
板垣的分析与策略
后来,板垣先生跟我说,他当时对自己的媒体策略还挺有成就感的。
他对竞品采取的强硬态度,显然让媒体关注度大幅提升,尤其是在西方游戏媒体那边。他告诉我,这种方式在日本不太受欢迎——因为日本不喜欢对比广告,但这在海外却特别有效。
另外,板垣先生在一些人眼里,对世界历史和军事(尤其是二战史)很有研究。他甚至把《死或生》和《铁拳》的关系比作战争。
他认为,像要打赢一场战争,必须彻底侦察敌方的资源,所以他仔细分析了《铁拳》项目组的实力。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甚至挂着一张分析南梦宫《铁拳》项目组实力的图表。他从游戏职员表入手,仔细调查了表上每个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技能和业绩(之前提到的“发现我是早稻田学弟”,就是这么来的)。
他还分析了职员表上名字的排列顺序,发现了一个规律:每个部门排在最前面的人,不一定是核心技术人员,反而可能是擅长管人,或者已经不怎么做一线工作的资深员工。板垣说,我当时作为年轻的团队负责人,和这些规律不符——这让我成了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异类”。
他的判断是对的。
我很幸运,在当时就能和一群很优秀的人共事——其中有比我大十岁的前辈,还有被视为天才的导演和程序员。这些前辈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个被“宠坏着”的环境里负责游戏设计。他们经常会问:“原田,你想做什么?需要什么?我们都能给你搞定。”这种配置在行业里很罕见,也让我成为了那个“特例”。
后来,我们的竞争告一段落。有一次聊天时,板垣先生给我看了他那张分析图表,我当时就被它的准确性惊到了——上面准确指出了当时《铁拳》项目组里的核心人物。
看到那张表,我心里都有点发毛。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游戏行业还没有成熟的营销分析体系,但板垣已经对《铁拳》的销量数据和用户群体了如指掌。他利用这些数据制定策略:
- 媒体层面:直接对标《铁拳》,提升《死或生》的品牌知名度;
- 产品层面:避开和《铁拳》正面竞争,找出“《铁拳》没满足的需求”及《死或生》的技术优势,并为游戏制定独特方向。
这也是为什么《死或生》最终呈现出的玩法,以及瞄准的受众群体,都和《铁拳》不一样。
争斗结束之后
争斗结束之后
2008 年,在板垣先生离开特库摩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和他的关系还没怎么变——我依然觉得我们是对手。可他却又一次主动联系了我。他约我吃了顿饭,席间告诉我,他已经离开特库摩了。
吃饭的时候,他说了句让我很意外的话:“原田,你其实是我的战友啊。”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他是这么看待我们之间关系的。
他详细讲了当时的各种策略和想法,还明确说:
我从来没恨过你、恨南梦宫,也没恨过《铁拳》。相反,我很尊重你们。当时我对比了双方在开发、销售和发行上的实力,很清楚硬碰硬肯定不行。我只能用尽所有能用的策略。之前的事,对不起了。
接着,他话锋一转,问起了《铁拳》的策略,尤其是在制作、品牌和营销方面。我跟他讲了很多,但重点提了这一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就会去世界各地的街机厅,观察玩家怎么玩我们的游戏。我还见了很多街机厅经营者和分销商。大概在 90 年代末,我很快发现西方街机市场在急剧衰退——当时街机厅倒闭的速度快得吓人。这意味着,格斗游戏的战场正从街机转向家用主机。
更重要的是,“100 日元一次”(在美国是 25 美分)的价值也在消失——赢的玩家没那么想靠一枚硬币继续玩下去,输的玩家也不再担心浪费硬币。这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格斗游戏作为娱乐形式的价值认知。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调整了《铁拳》的策略,把目标放在让格斗游戏成为适合家用主机的产品上。
原田注:《铁拳》在这个品类里算是走在前面的——比如开发了《铁拳球》(Tekken Ball)模式,比《死或生沙滩排球》还早;还有 “铁拳力量” 这样的卷轴动作模式;以及超出常规格斗游戏范畴的预渲染动画和剧情战役模式。
除此之外我还跟他讲,随着街机的衰退,我是怎么注意到“社群活动”(尤其是在北美)兴起的:
- 初期:活动处于草根阶段,多是家庭小型聚会、大学礼堂或社区中心比赛;
- 后期:逐渐发展为酒店宴会厅、体育馆举办的大型赛事。
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些活动的潜力,开始在幕后支持这些社区。具体来说,我们会免费提供街机机体和基板租赁,负责运输和安装,偶尔还会给比赛优胜者准备海报之类的小奖品。
其实现在四五十岁的老玩家里,当时可能有人不知道我的名字,也不知道我是谁,但说不定有人记得,曾在活动现场看到我默默帮忙安装街机(那时候我连墨镜都没戴)。
那段时间,《街头霸王》(Street Fighter)系列在《街头霸王 3》之后进入了长达十年的沉寂期,再加上游戏市场重心转移,街机更加式微。即便其他格斗游戏系列陆续消失,我依然专注于两件事:
- 维持家用主机市场的活跃度;
- 守住亚洲街机市场的份额。
事实上,《铁拳》系列不断推出新作,不中断更新,同时用街机基板和内购获得的巨额利润来补贴主机版开发——这种模式居然一直延续到了《铁拳 7》,现在想想还挺不可思议的。这其中也包括对草根赛事社区(也就是格斗游戏社区 FGC)的支持,正是这些支持让我们的业务和开发得以继续。
当时,关注西方赛事场景发展的开发者其实很少,这点我很确定。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那些年里,在现场负责运送机体和基板,或者观察活动的日本开发者,经常只有我一个人。
虽然有各家公司的市场人员在场,但我很少看到其他开发者直接和这些社区互动。
这种策略让《铁拳》即便在街机市场的“寒冬”里,也能稳步推出带编号的新作。在《VR 战士》系列沉寂的同时,我们成功打入了西方市场,占据了不小的份额。
我当时觉得,要是我自己遇到困难,没人会来帮我,只有市场上核心格斗游戏社区这个“外部力量”,才是我唯一能依靠的。
我跟板垣先生说,这个策略我一直没对外说——没跟公司里的其他团队讲,也没跟其他公司的开发者提过,只是默默在做。
他听了之后很惊讶,说:“什么?开发者哪会做这种事啊!真的假的?你比我想象的还务实。”
看来,他对 70 年代出生的游戏开发者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我们都是待在办公室里,盯着屏幕没完没了写代码的人。
说实在的,写代码确实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到了 90 年代末,我会利用项目之间的开发空窗期,去世界各地跑。
和解
和解
通过这次对过往策略的交流,我和板垣先生多年的矛盾终于化解了。
这件事发生在 2008 年底。
从那以后,每年年底,我都会接到他喝醉后打来的电话,这慢慢成了一个惯例。
不过想想,最近几年好像没再接到过了。
(头图来源:X@Harada_TEKKEN)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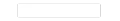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1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