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由一个预告片引起全民hype的勃勃生机以及流向改变
由一个预告片引起全民hype的勃勃生机以及流向改变
时间重新回溯到2018年一月,有这么一支发布在互联网上的游戏预告视频点燃了诸多国内玩家的热血。
预告中的内容,最开始为一副简单的水墨山水画,由一只雄鹰飞入冲散了水墨意境与实机质感的对立,随着镜头俯瞰陇间田野,掠过几只火箭,再去往黑夜中的铁甲雄兵,是焚于烈火中的洛阳城,被劫持的少帝,大腹便便的军阀,乖张暴戾的武将,然而镜头一转,除开飘落的桃花,标志性十足的蛇矛、偃月刀、长剑相接,随着镜头徐徐拉远,武器的主人们是于一群乡勇中富有国民性色彩的“桃园金兰三兄弟”,三人与那暴戾的武将的对决落幕在一声“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中。
极强的预告表现力以及富有戏剧性和商业性的IP使得这个项目在商业成果上喜人。其表现就是即使遭遇跳票延期,该项目依旧以首周超100万份的成绩抵达了CA内部销量最高的记录。这一成绩被内部视为“出圈”成功,证明三国IP的全球号召力,中国玩家贡献显著——毕竟,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单说“刘关张”这仨兄弟,就是很容易在国人内心中引起不同程度的波澜,甚至在次年国庆假期期间,玩家群体在社交平台分享游戏体验时衍化出 “放假在家只想匡扶汉室” 的梗。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可以说,本体发售的第一年是CA与中国玩家距离最近的“心贴心蜜月期”。 CA在该项目中别具一格的做出了近十年三国类游戏中富有开创性的游玩环节以及视角:诸如“间谍”系统,让玩家可以在势力发展的同时,在潜在假想敌中安插一根针,甚至可以让自己的间谍成为该势力的领袖,进而成为自己的附庸等操作;别出心裁的太平道刻画以及黄巾势力的设计,展现出对这一段历史上黄天势力的尊敬性。
然而,尽管本体热卖,后续DLC“八王之乱”、“命运分歧”销量惨淡,好评率低至39。这使得CA认为玩家对非核心三国内容(如西晋内战)兴趣不足,导致投入产出比失衡。
同时,CA一直以来的屎山代码的技术性问题也在同步暴露出:游戏底层逻辑混乱,尤其是五行系统、武将部曲机制等创新设计未完善,导致后续更新难度大;水战系统是全战系列多年的缺失,但CA未解决此问题;同时,CA未开放骨骼权限与配音加密,限制MOD深度优化,间接承认技术框架的不可持续。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再在游戏上来看:无双化武将破坏兵种平衡,这无可厚非,因为对玩家在单机中面对ai破局中是富有乐趣的,出现“三名将带兵无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战场策略和兵种研发的必要性;在依靠精锐武将破局后面对的简单化的内政和模块化的五行建筑冲击收入》地盘大了就要抓腐败的游戏情况,使得策略游戏从体感上就进入了某种重复的无聊中,且这一问题修复成本过高;不过这些问题无可厚非,也够我爽个400小时。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最后是在资源分配和公关上的问题:与《全面战争:战锤2》持续更新40余个DLC相比,而全战三国仅7个DLC便遭腰斩;好不容易与玩家达成一致后更新到官渡之战,却曾承诺推出“游牧民族DLC”并完善北方势力,而突然停更又背刺了该项目的拥趸,引发全球玩家联名抗议及Steam差评轰炸;CA内部明确将战锤系列视为“可持续盈利的奇幻线”,而三国作为“历史线试验品”而进行“战略性无限期搁置”。
追根溯源,全战三国是CA在历史与魔幻路线间摇摆的牺牲品。其商业成功无法掩盖设计矛盾,而CA选择“砍掉重做”而非“坚持修正”,站在CA的角度来说,是反映“实用主义”的决策,但站在玩家的角度来说,这个项目暴露了其野心,也昭示出其驾驭力的高开低走。
不过,假如说,仅仅是假如,如果我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抛去原先对于“一个尊敬中国原本文化”且会“积极响应玩家反馈,不断去把自己作品缺点修正的海外制作团队”的一个幻想,然后再同步锁定在“汉末三国”这一特定的历史节点上做的作品,我发现居然意外的和我国的一部作品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新三国》。
两种立项态度,却殊途同归的效果
两种立项态度,却殊途同归的效果
2010年, 曾有过这么一部标榜“还原历史” 的三国题材电视剧:《新三国》。从该电视剧编剧公开称“看不下去《三国演义》”,到该作品中频频出现了诸如“曹操在讨董时夸孙仲谋”、 周瑜终日哭诉“主公疑我谋反” 、“娶间谍的司马懿”这类富有厚黑特色的神人剧情, 所有政治斗争简化为“办公室宫斗”。而一边在标榜“尊重《三国志》”, 又将吕布貂蝉的感情戏用了10集去讲,又使用《三国演义》的桥段“空城计”,不在《三国志》中还原士族与寒门矛盾等当时的社会结构议题上创新与还原原格局。
可以说,这种对原典以及题材的轻视,其实像极了全战三国制作团队对于承认“更关注游戏性而非历史模拟”。加之核心受众之一的中国玩家因文化共鸣而支持本体,但DLC销量惨淡后遭遇制作团队的突然停更的背刺,这使得对于核心受众的主动远离。可以说,这两个作品的创作逻辑和受众反馈上存在显著相似性,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体现在文化理解偏差。两者均试图通过现代化解构(所谓的“游戏性”以及)降低理解门槛,缺乏对英雄气、忠义观、时代悲怆感的“三国精神”的敬畏而失败。
这使得全战三国将乱世史诗简化为“先通过联姻离婚来搞到可以无双的神将+拉满去省份涂色+种地叠威望”直到称帝再强行灭掉另外两家皇帝达成字面意思的三国统一,而丢失全战系列“宏观战略与微观叙事平衡”的基因;新三国用“职场宫斗+腹黑仁君与流氓政客的博弈”替代“天下之大,阴谋阳谋的英雄们互相合作与对立”的浪花淘尽英雄情怀,《龟虽寿》的英雄迟暮意境被庸俗化为家长里短。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可以说,全战三国是披着汉服的罗马军阀内战,新三国是穿着古装的现代办公室,其二者皆困于 “形似神离”的创作陷阱, 最终一起陷入了对原题材不尊重,但对商业尊重的“投机性折衷”。最终跨越时空文化步入 “形似神离”的黑夜。
不是“完美”的,却是近十年最具突破性的三国作品
不是“完美”的,却是近十年最具突破性的三国作品
那么,CA制作的《全面战争 三国》真的是那么糟糕吗?本身我准备写到这里就停止,可直到我重新看了下全体制作人员的合照以及CA内部两位总监Janos Gasper和Pawel Wojs的采访后,我才回想起,正如Janos Gasper所说,“《全面战争》系列”一直以来向玩家的承诺是让他们自由地重塑历史,并在此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体验历史事件。因此,该立项不能因为过多的脚本叙事而变成故事驱动的冒险游戏,从而丢失了沙盒游戏的本质。
到这里我才明白,原来在一个相对模糊的界定范围内,整个制作团队也有考量过自己一直以来的发展特色,进行取舍,虽然就着结果来说,不是那么令所有人满意。那么,我想,既然提到三国题材的游戏,除了我今天提到的《全面战争 三国》以外,我不由想到了另一个长期耕耘于三国题材的厂商,光荣,以及它的《三国志》系列。
在战争场面与战斗系统上,显然,《全战三国》最大亮点,是“万人同屏”的史诗级战场感。其即时战术指挥、天气系统、伏击战和兵种协同远超光荣《三国志》系列;而光荣有对于该题材有深耕40年的积累,在人物关系网(如“相性系统”)、事件触发(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和武将特性(统武智政魅五维)上更贴近《三国演义》,避免出现“关羽投降”“吕布被小兵暴打”等违和历史感的随机事件;在内政和外交上,《全战三国》的外交系统被赞为“全战系列最佳”,支持割让土地、联姻结盟、间谍渗透,动态关系网复杂,且具策略性;
这其实是代表两个制作组、公司、甚至是还原微小到最小单位的“个体创作者”上,对于一个创作题材所突出的核心不一致的情况,而已。核心优势对比便是:《全战三国》强于战场表现,《三国志》强于历史沉浸;策略丰富性各有所长;一个是本土化诚意,而《全战三国》则是全球性的一次突破。
那么,对于一个三国爱好者来说,若你在三国这个题材中追求战场沉浸与视听震撼,那么,《全战三国》是近十年最佳——它首次以3A规格还原冷兵器战争的磅礴,其战斗体验是任何一代《三国志》无法比拟的;若重视历史叙事与策略深度:《三国志11》仍是天花板——其相性系统、事件链和战棋玩法构建了更纯粹的三国宇宙。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所以,我可以得出结论: 你二家,若互相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所以,我可以得出结论:全战三国不是“完美”的三国游戏,却是近十年最具突破性的三国题材作品。它以全球化的制作水准激活了沉寂的三国游戏市场,而《三国志》的没落(虽然15代现在还渺无音训)恰恰反衬其成功。
是“凝视”还是“对话”?或许有更好的平衡
是“凝视”还是“对话”?或许有更好的平衡
行文至此,可以说,全战三国是英国人的三国,三国志是日本人的三国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两个对亚洲题材开发的游戏:《sifu》和《对马岛之魂》。前者是由法国Sloclap工作室出品表达出“道艺合一”的独立游戏,后者则是由美国Sucker Punch这一商业团队制作出富有“和式匠意”韵味的商业作品。
这两款作品都有一个与CA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欧美制作团队,且都制作亚洲题材的作品。而前两者得到不错的商业结果以及玩家口碑。
而我们把两个团队单独拉出来看,就会发现他们也都有在态度和行动上下足自己的心血,包括但不限——弱化意识形态输出:譬如刻意避免西方视角的价值评判,聚焦于“境”(场景)与“心”(角色成长)的亚洲美学统一。
Sloclap核心成员本杰明因痴迷白眉拳深耕中国武术十余年,武馆经历使其理解“武德”非虚概念,加之直接吸纳文化顾问意见,这使得《sifu》一招一式皆承载武术哲学,跳出复仇叙事,且呼应“武德”精神,体现习武之人对“道”的领悟高于“技”的层面。
而对于商业团队Sucker Punch来说,《对马岛之魂》则是以“黑泽明电影”为媒介嫁接东西方审美,而非强行解释日本文化,以及,创作期间多次赴日采风,精细还原镰仓时代风物诗(如春樱、秋枫、冬雪),并通过“风导引”“俳句创作”等系统,将神道信仰与武士精神融入玩法机制,加之不强制以欧美剧作逻辑来输出意识形态,更是被日本玩家赞为“最懂武士精神的非日游戏”。
那么,在我看来,创作题材、核心理念,又或是是否是商业团队还是独有游戏工作室,都不是决定作品商业结果以及文化口碑的绝对因素。 一直受经济的角度的叙事看来,商业公司都是“效率优先”的忠实拥趸,各行各业都是如此。然而,游戏界却是一个"不用那么符合全部商业逻辑"的行业,甚至是商业化了说不定反而掉入名为“效率优先”的陷阱。远有CA,近有打破了“商业=功利,独立=真诚”的二元对立的双头龙工作室(前十字星)。
在我看来,在游戏界,商业公司的困境在于“系统性妥协”:CA受限于全战框架与股东回报压力,将三国题材“工具化”,最终陷入文化拼贴;其失败印证了后殖民理论中的“他者化”生产——东方成为被观看,被凝视的客体。
而独立工作室的优势在于“主体性内化”:Sloclap直接去进入文化,这使他们的游戏成为文化转译的载体而非商品外壳。
那么,我认为,第三条道路的可贵:Sucker Punch用行动证明,商业团队若愿牺牲短期效率换取文化精度(如动态植被运算挤压贴图资源),并放弃意识形态预设与解构,亦可实现全球口碑与文化尊重的双赢;而双头龙则是以本土非主流文化为主,通过“初始猎奇 → 系统引导理解 → 文化共鸣”将中东文化从“被观察的他者”转化为“叙事主体”,并以游戏机制承载文化矛盾(绝对权力带来的混乱,与混乱中的道德)。
真正的文化尊重,不是搬运符号,而是理解符号背后的生命经验。而无论是否本土游戏来创作,而这作品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游戏作为“第九艺术”在全球化时代的责任:是选择成为文化掮客,还是甘当学徒?这将将反映出我们能否在数字世界中,保存那些正在被我们遗忘的精神“快乐老家”。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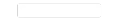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6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