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注:本文后段叙事部分包含剧透内容
我对于《光与影:33号远征队》的兴趣、其实只是始于某次游戏展上亮相的片段,片子里展现了一个从未见过之视听规格对回合制JRPG战斗场景,这就是我仅有的,但相当亮眼的第一印象。但时间过了很久,我也没继续关注,直到发售的时候,我才又想起来,所以我没看过任何其他的宣发,仅仅带着上述的印象,开始了游戏。
视频版
视频版
(包含更多发散内容,文章缩略到8000+字)
JRPG重绘
JRPG重绘
虽然本作“是法国制作组制作的设定于法国的作品,French RPG,但玩法系统和框架上也确实是一个纯正的JRPG。 虽说如此,但本作对于JRPG品类的清新尝试一点也不少,在这些Fresh Takes的加持下, 本作玩起来的感觉也毫不常规。
尤其是最值得注意的动作系统:本作虽然是一个回合制角色扮演游戏,但它对即时动作的要求程度,远超我玩过的任何其他 JRPG——甚至不夸张地说,不时透出 ARPG 会有的感觉。
一般来说,ARPG 主要的区分点就在于它极其注重即时反应。像 JRPG,之前也有像《如龙》系列那种”半即时制“,或是加入一些即时反应的机制,但往往都不重要,可有可无,可用可不用。而在本作的战斗系统中,即时的考量是相当重要的,它和传统的回合制构成了战斗系统的一体两面。
如果你不擅长即时反应,那本作的一些桥段,确实会让你觉得坐牢。不过这种设计也极大地加强了战斗中的临场感(Engagement),本作战斗比我玩过的任何其他 JRPG 战斗都更令人血脉贲张,不过,要是能有一键重开就更好了。
本作也是我目前玩过的 JRPG 里,地图探索做得最好的作品之一。这倒并不是说它的关卡设计有多么惊人——其实,它的关卡设计就是正常水平,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但也没有太多问题。
但是,相比我们习惯的很多 JRPG 的迷宫式地图,本作的地图探索其实更接近之前《龙腾世纪4》那种箱庭式的紧凑设计。当然啦,在箱庭这方面,我倒不觉得本作比作为ARPG的《龙腾世纪4》出色,但在 JRPG 品类里,我敢说应该是 T0 级别的探索体验了。
不过,本作的是世界探索其实也不一样,因为它采用了大小地图,大地图套小地图,在大地图上的体验不免让人想起《英雄无敌》或者是最近的《小缇娜的奇幻之地》,也有遭遇、世界Boss等,小地图里既包括简单的场景美景收集(类似《暗喻幻想》中的风景地点),也包括像《龙腾世纪4》那样的箱庭,甚至还包括爬塔和竞技场。
但很可惜,本作关卡完全不存在地图,而我实在无法相信一个箱庭游戏可以不做地图,对我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缺陷。
本作的探索体验还是层层加码,使用了技能门,也略微能给人一种银河城风味,但这一点处理的其实并不好,我们后面会讲。
本作的配装系统也是五花八门,这一点其实也和地图探索相辅相成。虽然地图探索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拿到一些没用的低级武器升级资源(因为本作的武器升级资源是不可升级的——所以到后期,很多素材基本就没有什么用了)而且武器也存在“一两个最优解”的情况,尤其是对于某些角色。所以这一点上确实还会有一些资源探索上的小垃圾情况出现。
但总体来说,因为本作有巨量的配装选项,所以导致即使你拿到了几个你不想用的武器,它们也一样有具有驱动力的词条可供解锁,一定程度上给收集癖缓解了”小垃圾“情况。这种优秀的探索驱动力设计我也在之前的《龙腾世纪4》鉴赏中提到过。
我也非常喜欢本作的符文设计,刚掉落的技能符文只能被一个角色使用,但只要练满熟练度,就可以以一种全队共享技能库的方式,任意角色都能够用灵光点来使用,装备驱动力很足。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经常把这款 JRPG(也就是本作)和《龙腾世纪4》这样的 ARPG 做对比,那就是因为我认为本作是融合了相当多现代 ARPG 要素的。
这些现代 ARPG 要素既包括《龙腾世纪4》那种箱庭式探索,也包括了一些来自魂系游戏的东西(毕竟魂系游戏也是 ARPG),就例如它们在战斗系统上设计出来的低容错率即时反应。
当然,本作并不是所谓的“JRPG 版只狼”(当然了这种调侃也是因为其极为严格的弹反判定,本作的判定其实基本是跟着声音来的,而不是”见“招拆招,某些时候还颇具音游感),因为大部分刁钻的 Boss 都只存在于支线任务里。主线其实并没有怎么刁难你(你也可以随时改难度)。
也没有坐火复活死亡惩罚,也没有特别过分的跑图刷怪等机制。甚至很多时候,在支线里你如果实在打不过,你都可以绕着怪跑把资源全部拿完然后直接走人也是可以的。而且主线基本没有什么刁难玩家的部分,这一点我觉得相当不错。
存档点也是非常便捷,基本每一场重要战斗前都有自动存档,而且还可以通过换装触发自动存档,大地图上也能随时扎营,一点也没有难为玩家。
那么再来说说数值系统,因为作为一个强数值的游戏。它的数值系统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我认为它也有一个好处:你支线打得多的话,主线就会变得非常轻松......
坏处是什么?坏处就是“感觉不太对劲”。比如说我在支线里碰到一大堆打不过的 Boss,结果我最后通关这个游戏的方式,是把所有我能打得过的支线全都清掉,然后才去打最终任务,但是......
我当时大概是 80 多级,我记得我的角色等级是 82 级左右。然后两刀就秒了最终 Boss。为什么是两刀?因为一刀下去,第一阶段直接被打到锁血,进入过场动画,然后第二阶段刚出来,又一刀秒杀......是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打不过支线 Boss,但你却能轻松打过主线 Boss。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数值问题:游戏里的伤害上限是长时间被锁定的,在第二章结尾前最多只能打出 9,999 的伤害。
那为什么会这么搞?就是因为它的数值系统本身有严重问题。我一般不太喜欢专门去探讨数值,但这个游戏确实让我感觉到明显不对劲。
举个例子:一开始你最多打出 9,999 的伤害,而很多支线 Boss 的血量动辄几十万、几百万。通关第二章后,游戏突然放开上限,你可以打出几百万、几千万的伤害。我记得我自己打出过的最高伤害是 2,000 多万,没错,就是两千万。也听说有朋友能配出更高的数值。
那在这种前后差异下,一开始拿着 9,999 去摸那些支线 Boss 根本没戏。但是游戏完全不告诉你有伤害上限,也不提示你第二章后会解锁上限。如果你不看攻略,根本不知道。
这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粗暴的设计错误。
它是一个完全可以被解决的问题。游戏明明已经有箱庭式的能力解锁系统: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些区域、能力是跟着主线推进逐步开放的。
那它为什么不把这些数值膨胀到离谱的 Boss 安排在后期才解锁的区域?相反,它把这些血量离谱的 Boss 安排在一开始就能自由进入的地图区域里,完全没有做任何引导或限制。
这就导致整个支线 Boss 和支线敌人战斗体验非常乱:All over the place,也具有相当大的挫败感。
这对探索体验实际上是减分的。尤其是像我这种习惯在推主线前尽量清完当前区域支线的玩家,会特别痛苦。一开始到处碰壁:去这里,打不过,回来;去那里,打不过,再回来;又换一个地方,还是打不过,再回来。
而这些地方,游戏完全没有设置能力墙或阻挡,都是默认可以进入的区域。
不过,话虽如此,当你过了第二章,解锁队友与伤害上线后,整个体验会好很多。地图探索也会变得顺畅许多。虽然仍有一些离谱的 Boss,但整体体验已经没有大问题了。这种情况下,膨胀的数值反而更能激励玩家去研究下配装,感受合理搭配后打出前所未有伤害的快感。
法兰西风情
法兰西风情
什么是法式风情呢?虽然法国在电子游戏中出现的频率并不算低,但也不算特别高的那一档。我们有过《刺客信条:大革命》那样以巴黎为背景的作品,但本作带来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巴黎。
游戏中的卢明其实就是正儿八经的法国首都——巴黎。在游戏里你能看到巴黎歌剧院、埃菲尔铁塔、巴黎凯旋门等真实地标的化用或重构,这些建筑作为游戏中环境和叙事的重要部分和视觉引导。
而且,整个游戏的氛围,无论是从视听体验,还是从叙事细节,甚至小到每一个角色的对白,比如说那些刷头精之类的角色对话,都带有一种我从未在其他游戏中感受过的、带着诙谐气质的风格——那种特有的浪漫与开放?
说到法式风情,大家可能脑中会先浮现出浪漫、优雅、带一点点轻松幽默感的意象,而本作则是将这一切贯彻得非常彻底。当你一脚踏上大陆,看到大陆上这些生物是怎么互动的,看到刷头精们如何闲聊打趣,看到巍民如何谈天论地,我都会有种感觉就是,这样的风格,这些东西,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写、这么演。
也许这些不经意间勾成基调,Tone的细枝末节,是根植于文化的表达方式。每个文化背景下的制作组,在制作设定于自己故乡的作品时,总会带出一种外人看来非常特别的东西,所谓的异域风情。这种文化特色,本作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比如游戏的名字——“Clair Obscur”,就是“光与影”或“明与暗”的意思。在绘画艺术里,这是一个最为基础的技法概念,用明暗对比来展现立体感与情绪张力。而在本作中,这一对概念贯穿始终,既体现在名字中,也体现在整个叙事结构与美术风格里。
再比如装饰风格:Art Deco在本作中无处不在,从服装到建筑、从街景到 UI,充满了法国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好年代的艺术气息。那种复古、雕饰繁复、金属光泽、几何图形构成的空间语言,带来一种既浪漫又肃穆的视觉感受。
美好年代(法语:Belle Époque,法语发音:[bɛlepɔk])是欧洲社会史上的一段时期,从19世纪末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结束,得因于科技进步和经济腾飞,突然扭转之前由于长萧条所带来的悲惨痛苦,进入一段繁荣快乐的幸福时光(特别是1896-1914年)。漂亮时代是后人对此一时代的回顾,这个时期被上流阶级认为是一个黄金时代,此时的欧洲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及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欧洲的文化、艺术及生活方式等都在这个时期发展日臻成熟。此时期约与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及爱德华时代相互重叠。
印象派在1860年代被认为是前卫的艺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漂亮时代的学院写实绘画风格由威廉·阿道夫·布格罗、约翰·威廉·沃特豪斯及弗雷德里克·雷顿等所代表。巴比松派则采用了外光画法的风格。新艺术运动 (Art Nouveau) 在1890年代中期成为欧洲主流的装饰设计风格。许多成功的作品,建筑于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 (维也纳分离派)、匈牙利、波希米亚及拉脱维亚,并很快扩散到美国及墨西哥。
人物的穿着,比如贝雷帽、水手衫,街头巷尾的鲜花装点……如果你以前玩过《生化奇兵:无限》,对里面那种梦幻的巴黎街区还留有印象,那么本作也绝对会带给你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
当然,除了这些,我还强烈推荐你用法语来游玩本作!
我自己完全不会法语,所以一开始我选了法语语音,其实是抱着试试看、反正听不懂无所谓的心态去体验的,刚进游戏那会儿确实觉得挺怪的,无论如何这对我而言也是一种陌生语言的陌生声音,没什么共鸣。但大概几个小时以后,我就完全沉浸了进去。
为什么呢?因为当陌生带来的怪异感褪去,就会发现,法语,真的很悦耳!很好听!
而且,这种“听不懂但好听”的语言环境,反倒成了一种奇妙的旋律。主观听感的部分我们先放一边,其实法语在欧洲也曾被广泛认为是最优美的语言。在历史上,古代英国贵族都以会说法语为荣,英语中很多复杂词汇其实就是从法语里借来的。
所以说,哪怕你不懂法语,它的发音也会慢慢让你隐隐约约感到熟悉。这种熟悉感和陌生感混合在一起,最终会变成一款法国制作的法式游戏独有的一种声景。这种声音,反倒成了我体验下来是整个视听体验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光与影:33号远征队》的音乐本身就非常优秀,法语语音再加进去,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搭配,因为游戏里的很多歌曲、很多对白(即使你用英语配音也会蹦出一些法语短词),原本就是以法语呈现的。如果配音也用法语,就完全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沉浸体验。
所以如果你打算认沉浸体验这法兰西的美好年代,我推荐请用法语游玩。
叙事与思索
叙事与思索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叙事——这一部分就可能会有一些剧透了,所以不想知道剧情的朋友可以跳过。
我不会在这边把它的剧情复述一遍,也不打算进行什么解读,但我想说一些我通关以后对它的印象,以及由它引申出的一些反思。这里的反思(reflection),并不是说对游戏设计的批判,而是基于它告诉我的东西,我有一些想说的话。
这些话不一定都是游戏本身讲的内容,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玩后感。
本作的故事一开始,看上去像是一个典型的末世预言类的设定,但实际上,它倒也并不是真正的世界面貌。这也是为什么,这期说文章的标题会叫做“人生如戏”。因为我觉得,这四个字就是最能概括本作叙事主旨的词。
它里面探讨了几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包括死亡、包括人生、包括意识、包括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包括艺术作品如何承载这个虚实界限、以及艺术作品,作为一个完全虚构的东西,如何既生于现实,却又模糊掉虚实的界限——我们又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找到我们所处的现”或虚构的位置。
这一大堆听起来很杂的主题,其实在本作中是揉成一个整体的叙事。它的叙事风格,可能乍一看比较晦涩难懂,但其实这种表达方式,正是大量法国先锋派和实验电影为人所知的手法。
你在游戏里可以看到很多比例的切换、色彩的隐喻:用不同色彩去代表不同时空、不同心理状态、不同维度的界限……这些东西,在本作中都有大量运用。
而且还有一点,是我从游戏里读到的一个明确的理念——我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
我记得在游戏里,有一段日志里是这样写的(我这里不引用原文,大意如此):
什么是好的艺术品?它是一面镜子。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角度。
好的艺术品是什么?它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出的,是你自己。
我欣赏一部艺术作品,无论是画、电影、音乐、文学、游戏,我之所以觉得它好,其实并不因为它的表,而是因为它和我之间产生了共鸣。这种共鸣,就是我最宝贵的感受。
我看一幅画的时候,其实我看到的并不是这幅画上的色彩和笔触、甚至不是上面的事物,最后欣赏到的、记在心里的、甚至影响深远的,是它在我身上反射出的东西。我看到的是它背后的所折射的我自己,它背后折射出的那个内心世界,那个...画界。
画界,在本作中是一个核心设定,但它并不只是游戏世界里的虚构术语。它其实代表着艺术作品本身:像我们之前聊过的游戏《Viewfinder》那样,它让你走进一张照片所展开的世界。而本作让你走进一幅画。这是一种将艺术具象化为世界入口的表现手法。你走进去以后,在那里体验到的可以是别人的人生,也可以是你自己投射到其中的想象与共鸣,最终其实是那个合二为一的虚构之人,一个融合了你现实意识,与虚构语境中角色的你,也就是像玛埃尔那样的你。
你走入一幅画界之中,每一幅画里都封存着一个人的人生。你在画中遇到的人物、听到的对白、看到的情感冲突,都是创作者的心血和读者(玩家)之间的交汇。你在玩这款游戏的过程中,其实你就在体验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你走进了他们的世界,但你也把你自己投射进去了。
像玛埃尔、阿莱西亚、维尔索等这些角色,他们都是如此。他们都是两种人生的交汇点,他们是“光与暗”的一体两面。“Clair Obscur”,这对词不仅是明暗对比,更是象征着现实自我投射与虚构语境下他者共鸣的边界。
我之前也说过,我认为游戏最根本的本质,其实就是一面镜子。任何文艺作品的根本,本质上都是一面镜子,它在我心中的评价有多高,无他,只看这面镜子够不够深,够不够亮,其他的一切,均是手段和手法。
虚实守卫
虚实守卫
接下来我们就谈谈“虚与实的界限”这一主题。游戏的马埃尔线结局,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马埃尔最终选择留在画界,接受并见证维尔索自然老去、逝去;以至于待了太久,已经即将失去自我,但之后她是否回归现实,并无定论。
可以把他和维尔索最后的对话,看作是两种人生观的对决。就像《黑客帝国》里的红药丸和蓝药丸。如果你已经知道你所处的是一个虚拟世界,那么你会怎么选择?是接受现实,还是继续沉浸其中?这两种选择的背后,是两种人生态度。我认为,没有哪种绝对对错,但每个人在不同的经历、价值观、人生节点下,做出的选择都会不一样。
维尔索是不会衰老的,他的生命被永远困在某个时间点中。他的记忆没有丧失,但他失去了对变化的感知。而这种对变化的失感,恰恰是人类意识与时间最核心的感受之一,这一点我也在之前对于《星空》归一的鉴赏中谈论过。
他困在了一个自身没有时间流动的世界,而这使得他的人生失去了感受的锚点。他见证了太多的生死,却无法真正体验自己的衰老和终结。这种永恒,其实是一种诅咒。最终,他想选择了解脱。而马埃尔的决定,则是拒绝,但也没有完全拒绝。是让他可以再次感受到生命的流动,但依然走完这最后一程,但在违背了维尔索愿望的同时,也以她自己的生命为风险代价。
我完全理解马尔为什么会想要留在虚拟世界里——因为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说,现实生活也不过是肉体在活着,而真正的精神的生活,不一定要依附于现实世界。
人类从来没有完全活在现实之中。我们自文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活在故事之中。故事,是人类最基本的虚构自我的方式。从口述神话,到诗歌、绘画、小说、电影,再到今天的游戏——它们的差异只是形式,本质上,它们都是人类为自己建构的另一个世界,一种精神能够寄托之处,一种对于麻木的反抗。
而如果一个人,现实中失去了对幸福的感知能力,他自然会加倍投入在虚拟的情感寄托中。这并不等于沉迷,而是一种替代性的存在方式。所以,我并不觉得这款游戏最后说的是大家不要沉迷虚拟世界,要回归现实这种老套的说教。
本作的叙事,想说的不是人必须回来,而是:虚与实的界限一直都不存在,但也一直都在,仅此而已,它想探讨的是这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本身,而非答案,或许根本没有答案。
我们的原色
我们的原色
那么,第三个主题,就是关于死亡的。
什么是真正的死亡?什么是真正的人生?
本作探讨了三个话题,我们前面说的虚实界限已经谈了,那么这个死亡就是最后一个重要议题。我们来看看画界里的人,他们是真的吗?
我认为,游戏给出的答案是:是的。
别看我之前一直在强调虚实的界限,说画界是虚构,现实是现实,它们之间有明确的分界。但是它同时也在反复强调:这些拥有外界记忆的、意识的、化界中的人,是有意识的,他们有情感、有生活、有决策、有挣扎。
我在这里讲的,不是说游戏 NPC 是不是真人这种字面意义——我们当然都知道他们只是代码、建模、AI行为。而是在说:
玩家在一个互动式艺术作品中、在一个虚拟世界里的投入,是否真实?是否属于你人生的一部分?又或者说,你操控的那个化身,在用你的意识、你的记忆去做决定、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活动的时候,纵使皮囊是模型,动画是文件,但,它是否其实也短暂地成为了你的代理人,一个活着的人?
我认为答案依然是:是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画界中,所谓的死亡,就是失去原色。而在现实世界中,死亡本质上也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只是没有抹煞那么“美好浪漫”灰飞烟灭成玫瑰。它可以由无数种原因引起,其中最极端的一种,就是当一个人彻底失去对人生的希望,选择自我了断的那一刻。
在游戏中,失去所有原色就是死亡,只剩下暗(Obscur)。没有光,就没有色彩,只剩下黑暗。而我们现实里认为的死亡,现在医学上也接受脑死亡这一标准。医学可以不再用心跳停止来作为死亡的判定标准,就是因为我们早就认识到,人的本体不在于肉体的活着,而在于大脑、在于意识、在于那组神经电信号所形成的连续性系统。一旦那个系统崩溃,哪怕你心脏还跳着,呼吸机还给你送着氧气,人也就彻底不在了。
这种意识的连续性,其实是我非常在意的一个点。在本作中也通过刷头精复活的圣河进行了展现。我也在很多作品里都见过这个话题的探讨,比如《SOMA》那款游戏、包括《辐射4》里的合成人议题、甚至《星空》里关于归一也都涉及到类似的探讨:决定一个人是否还是“自己”的根本,是他的身体,还是他的意识连续性、甚至是意识遭到重大变故后的连续性。
我个人倾向于后者。意识的连贯性才是真正定义你是谁的关键。如果你都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存在,那就意味着你的“你”已经不复存在了。哪怕你还活着,哪怕你肉体还完整,哪怕你还能活动,但如果你之前的一切记忆、感受、情绪、经验全部消失了,那么你还是你吗?
我是不能接受这种重置式生命的。比如说跟我说,现在可以让你年轻十岁,但代价是清除你所有记忆、情感、人生经验——那我是不愿意的。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在于体验与从体验之过程中得来的瞬间。
这个体验至上就牵涉到另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是结果派还是过程派。我自己,是一个极度无法接受结果派哲学的人。因为人生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死亡。没有一个人的人生结果不是死亡。而死亡的本质是什么?是彻底的消散。是所有的感情、所有的记忆、所有你看过的东西、听过的声音、体验过的喜怒哀乐,在某一刻全部灰飞烟灭,连黑暗都不会有,因为黑暗本身就是一种颜色概念,而死亡会消除一切概念。我们总会说死亡是永恒的黑暗,但其实不是。死亡不是黑暗,而是没有黑暗这个概念。是没有无这个词汇,是“没有‘没有’”。
那才是真正的 Nothing。
所以,如果是一个结果主义者,最终的结果就是 Nothing。你怎么想象,它都只是想象——而真正的结果,是连想象本身也不再拥有。这就是我为什么很怕结果派,所以我最终变成了一个体验派,也就是过程派。我认为人生的一切意义,都在于过程。
那既然是过程,既然无论现实还是虚拟都一样可能会消失,那么我们还执着区分虚实的意义到底在哪儿?
在这个意义上,你会发现,虚构世界里的事情,并不比现实世界里更不真实。你在游戏中的情感体验,你对角色的共鸣,你在结局时产生的震动感,这些都是真实的情绪,是你人生体验的一部分。
今天聊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非常发散、非常私人的反思。但也正是因为《光与影:33号远征队》作为一个文艺作品,像它所说的那样,像一面镜子一样,投射回了我。
总结
总结
总而言之,说了这么多游戏里的、游戏外的、有的没的、生的死的,回到游戏本体来看。
《光与影:33号远征队》是今年迄今为止最超乎我预期的作品,它带着法兰西美好年代的留恋、独特的文化价值、融合了动作与日式角色扮演游戏的战斗系统、独具巧思的构筑与探索体验滚滚而来,成了AA游戏再次席卷业界的一场巨浪。纵使存在一些不成熟的缺陷和略糙的边角,但独具一格的基调依然从美术、场景、音乐、对白与叙事中势不可挡地涌出,最终带来了一场美妙且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域冒险,更重要的是,其打造出了一面照向虚实的镜子。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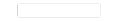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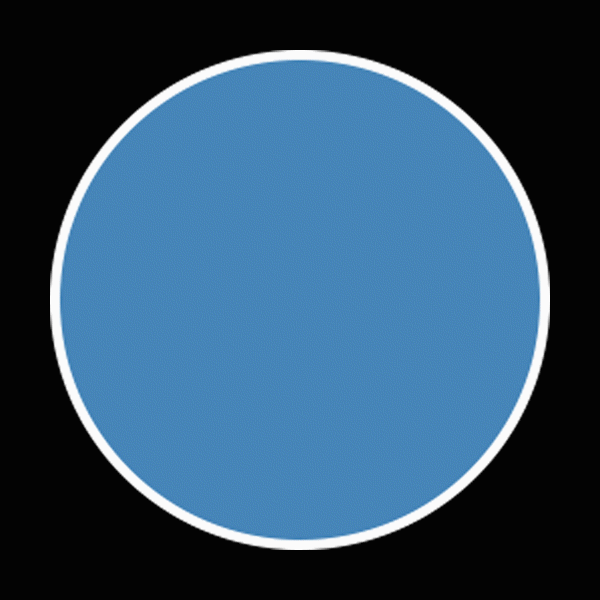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