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我本来并不认为「书单」是这么珍贵的东西。当然,在学术场域中,如果对某一类文献感兴趣,找一本质量还可以的综述或者专门研究,拉一遍后面的参考文献就行。
对于通俗的类型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在国内虽然不能说是没有,但是可以说是不成规模,也无阵地(当然有的中文系学位论文会写这种东西)。基本都是散落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更不会有专门的“文学史家”去梳理类型文学的文脉,供其后的创作者参考。
前一段时间,苦于没有新的日式恋爱喜剧可以读(这也和我没有日语阅读能力有关),于是找了Grok帮我开更为小众的书单。列出的十本书,并且有对应的卖点,值得阅读的地方。看上去不错。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经过我的事实核查,其中没有一本著作是真实存在的。
在这个意义上,用AI整合信息的努力是非常失败的。所以在这样信息时代,这种开列书单的工作竟然依旧是有意义的。
书单这种东西实际上非常个人化,是要将一系列关系牵强的东西构建联系,最终呈现为“清单”。
本篇书单:
冶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
陈渐:《西游八十一案:长安击壤歌》
周游:《麒麟》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倪湛舸:《莫须有》
冶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
冶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
出版年份:2022年
故事背景:唐朝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前一年)
本书我早有耳闻,不过因为起名、封面装帧设计都透露着一股野鸡味,会下意识认为怕不是什么历史擦边小说吧。
(我觉得读客的封面设计和风评要帮我背一半的锅。)
顺带一提。我在这两次所开列的“历史小说”,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历史为主线”,或者“以历史为基底的小说”。作者的典型特征是会依赖相当多的历史史料和较新的历史研究(社会史,物质文化史等)进行小说创作。而不是套一个时代的马甲,然后再用几个历史人物就算历史小说了。
话说回来,作者冶文彪的切入点是非常巧妙的。我们都知道,《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徽宗年间张择端所绘,画的是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徽宗年间的汴梁城繁华一时,但是这种繁华一角很快也要被时代的黑云淹没。北方女真崛起,攻击辽国,以徽宗为代表的宋廷带着机会主义的心态,想通过联金抗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在此过程中宋军的孱弱暴露在女真面前。最终在靖康之变中,汴梁城破,徽宗和钦宗被掳到北方。
也就是说,张择端所绘的汴梁城,虽然展现了大宋的繁华,但是同时这种繁华也仅仅是「最后的好时光」了。
那么该画卷所展现的其实是北宋繁华表相下的危机四伏。这便是冶文彪的《清明上河图密码》的切入点。全书共6册(日文本甚至分成了12册)。其中主角是「汴京五绝」,五绝各自代表了当时北宋的一个社会群体:士、农、工、商、兵。五绝每一人都在清明当日被卷入诡谲的案件,不得不各自应对。其中每一人都是从各自群体审视当时汴梁社会。而最终共同走向了靖康之变,汴梁繁华梦碎的大悲剧。
“我大宋从未如此富盛,有何可忧?” “方腊东南兴乱,岂非大忧?其罪虽当诛,其情则可恕。” …… 冯赛略一犹豫,随即奏道:“皇上请恕草民愚狂。这些年来,商法屡更、条令频换,商者手足无措,市井物价腾乱。国库日益富,而工商日益窘,竭泽之鱼,何可为继?” 梁兴也亢声言道:“军政废弛,荒于训练。为将者,视兵卒如仆役,任意驱使殴责,行如商贾,只知牟利;为兵者,衣粮常扣,营房常坏,温饱尚且难济,岂能扬武奋勇?强敌一旦入侵,百万禁军恐怕只如沙垒纸堡,奔逃不及,何可御敌?” 张用含笑扬声:“皇都艮岳奇,天下草木惊。宫中爱精奢,民间竞浮华。” 陆青也朗声道:“一纸括田令,万户尽哭声。朝为己田欢,暮因官税愁。” ——《清明上河图密码》
该小说第一册也改编成了电视剧,由张颂文主演,不过改编得不好。原著篇幅庞大,也很难有好的改编。(当然我个人觉得说不定改成角色扮演游戏会很好。)
本书的日文版译名为“824人的四次元事件簿:清明上河图密码”。全系列也是群像剧,不过我没有细数该系列是不是真的写了有名有姓的824人。
古往的画作中,从未有过如许多人,而且,其中绝大多数都只是寻常人。但再寻常,也都是人,哪一个不是活生生的性命?众生平等,同经了这场生死浩劫,性命便是性命,哪里有高低贵贱之别? ——《清明上河图密码》
陈渐:《西游八十一案:长安击壤歌》
陈渐:《西游八十一案:长安击壤歌》
出版年份:2024年
故事背景:唐朝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逝世前3年)
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帝王世纪》
本书是《西游八十一案》的最终章。陈渐的该系列推理部分始终难以令人称道(完全没有必要非常坚持唯物主义和本格推理),但是涉及到历史的部分都极好。
本册的时间线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西行结束,已经回到长安。不过故事的主角并不是玄奘,而是其俗家弟子王玄策(此人于史有征)。
“谶纬”是本作的历史线索,但这是一个现代人已经难以理解的概念。而本书所涉内容,即是以唐初谶语及其引发的史事为底本,构建起在唐太宗逝世前波诡云谲的初唐政局。而王玄策则被卷入其中。
《资治通鉴》中言,唐太宗李世民让太史令李淳风占卜,结果是「女主昌」,同时民间流传了一本谶书叫《秘记》,称:「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而太宗发现左武卫将军的李君羡的小名就是「五娘子」,同时他的官称和封邑均有「武」字,对此感到忌惮,于是将李君羡杀死,株连其家。
这个典故非常有名,因为其后该谶语在武则天时期被用于论证其统治合法性。笔者曾经在过去的文章中剖析过推理小说中「歌谣杀人」(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神话杀人」(如横沟正史的《八墓村》)的题材结构,这本就是推理小说的文脉传统。而本书则可概括为「谶纬杀人」。「谶纬」本身无法杀人,但是其构成了搅动政局的一股力量,各方势力各怀鬼胎介入其中,令案件变成了谜局。
王玄策恍然大悟,叹道:“我虽然破解了三篇谶语,却并不解其中深意。如今想来,张亮案中的卫州人刘道安也是认为自己应了刘氏之谶,怪不得陛下一定要杀张亮。而刘洎也是因为他既有强臣风范,又是刘姓,所以陛下也得杀他。” “不错,”刘全道,“大唐对刘氏防范之深历代罕见。贞观三年,长安有一无赖子名为刘恭,颈部长了块斑,像一个‘胜’字。刘恭炫耀道:‘吾当胜天下!’于是被捉拿下狱。另外,豫州都督刘师立你认识,他被猜忌之事你应当清楚。” ——《西游八十一案:长安击壤歌》
而这种构建谜局的巧妙之处在于其与历史题材的契合。这种案件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才可成立。
前文中所引的李君羡并非在初唐政局中唯一死于「谶语」的人,而本书将这几个案件巧妙地串联起来,而王玄策作为被迫卷入其中的「侦探」,读者得以从其视角,去勘破其中的真相。而在这些案件中被冤死的人们,作者也用另一种形式,令其怨念重返人间。
“你不懂。你们这些人把百姓视为牛马,不懂这斑斓世界有多么动人。”王玄策喃喃道,“上一场乱世杀掉我一家二百余口,让我一生一世都无法挣脱。是这座大唐让我重新睡得安稳,不再梦见刀光和鲜血,这个盛世是我,是皇帝,是魏徵,是秦琼,是刘兰,是张亮,是我的父母兄妹,是乱世中罹难的三千五百万人的尸骨共同堆叠起来的。我豁出命来守护它,就是守护这三千五百万人共同的梦想!去建一个盛世,那是我七天前的想法,如今我只想我儿子将来做一名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或者开皇这样的治世,斗鸡走狗纨绔一生,什么国家兴亡,民生疾苦,与他全不相干。” ——《西游八十一案:长安击壤歌》
周游:《麒麟》
周游:《麒麟》
出版年份:2022年
故事背景:清乾隆年间
与周游的新作《钦探》(上一篇文章已有介绍)相比,本作更加掉书袋。
本作颇有世情小说的韵味。差不多几个章节就是一个小的古典小说桥段,最后衔接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故事。本作虽有主角,但其形象并不突出。主角陶铭心算是一个乡村中的迂腐老儒,有儒家士大夫理想,但在现实中却显得左支右绌。他不愿与满清合作,但也同样不喜反满复明的八卦教。身为命运无法由自身掌控的「虫草」,一辈子都活在谎言中,但是最后却说,「这辈子都是假的,但麒麟,必须是真的!」
纪昀道:“皇上此举何意?就是要削咱们的脑袋:能想什么,不能想什么;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都给你规定好了。北京天桥耍猴的,地上画个圈儿,猴儿就不敢出来,就是这个道理。这次要于梦麟献麟,是和编书一个念头,皇上铆足了劲要教训汉人:你们不是整天就爱报祥瑞吗?那我就较个真,看你们怎么办!当然,看到于梦麟的名字,也让皇上起了兴头:你不是梦麟么?那正好,把梦见的麒麟献上来。” 陶铭心听得愤懑不已:“果然,什么崇礼尊孔,全都是装架子!” “不然呢!”纪昀也愤然,“听说了于梦麟的事,我赶紧面见皇上,建议教训于梦麟几句便可,不宜深究。但皇上不肯——他年纪太大了,很多事情已经糊涂了。他直接说,尔等撒谎了几千年,弄出五花八门的祥瑞糊弄君主,但朕是千古第一的帝王,谁也别想蒙骗朕。我退了一步说,麒麟确实有,但不可能抓到,还说孔子见获麟而绝笔。陶兄猜皇上说什么?他竟然说,孔圣人也是假的!听听,这是什么话?多年前在曲阜不跪拜,要给圣人加战马,现在又说圣人也是假的,真是疯了!我见话说不下去,就告退,皇上还不忘羞辱我:孔圣人算个什么东西?靠着孔圣人,宋朝赢了大金大元吗?大明赢了大清吗?” ——《麒麟》
文中的“麒麟”是一种政治符号,是一个弥天大谎。是儒家士大夫面对皇权希望维护的体面。
当然,要说本书完全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其实不然。本作其实是一个古典小说版的《楚门的世界》,但是设计却极为合理,读毕不禁让人赫然长叹。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出版年份:2022年
故事背景:晚清至民国
本书可称得上是马伯庸的长篇小说中最值得阅读的一部。本书创作于疫情期间,书中亦涉及1910年的东北鼠疫,可以称得上是古今呼应。
本书的创作缘起于马伯庸于2017年参观上海华山医院院史馆,这栋楼正是当年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旧址所在地。从此,马伯庸发现了一个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新的切入角度。本书从红十字会这一线索出发,勾勒了中国晚清民国的医疗发展史。其中的人物也往往有其真实的历史原型。国内写历史小说的不少,但这种视角却是极其难得。鄙人认为本作可以视作马伯庸的一个创作高峰,是可以抬高他文学地位的一部作品。(虽然我们谈论通俗类型文学的时候,一般也不必涉及「文学地位」的问题。)
峨利生教授闭上眼睛,再次吟诵起“苍生大医”来。他的发音很流畅,明显是下了苦功夫:“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大医……” 峨利生仿佛觉得自己发音不够标准,勉强重复了一次,旋即彻底沉默下去。只有那只瘦弱的手掌,依旧覆在孙希颤抖的双手之上。 ——《大医·破晓篇》
倪湛舸:《莫须有》
倪湛舸:《莫须有》
出版年份:2022年
故事背景:南宋
从这个标题就可以知本书所写为南宋名将岳飞之事。《宋史》记载,岳飞父子被下狱后,韩世忠质问秦桧罪名,秦桧回答「莫须有」。
而本书为6个短篇,从岳云、宋高宗赵构、秦桧、岳雷的视角来叙述岳飞一案。当然如同本书的名字一样,其中的叙述也是「莫须有」,也许有,也许没有。
这种叙述是带有重构性质的,且本文具有后现代气质。且每个短篇前均会引一段《说岳全传》,与短篇中的文本形成对照,提示读者二者均为一种叙述。
本作中,岳飞不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大英雄形象,不过他也并未发声。所有短篇都是他人对于岳飞的叙述,而无岳飞视角的自述。这也避免了正面解构「民族英雄」的尴尬处境。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忽然从韩相公那里得了消息,说妈妈嫁了他手下的小校,叫父亲去接,这事就连姓赵的都被惊动了,父亲大怒,说跑了的女人怎么还有脸回来,可又不愿做得绝情被人指点,索性拿了一笔钱,叫哥哥给妈妈送去。哥哥向来恭顺,那次却一口咬定不去,竟同父亲剑拔弩张地大吵,结果被罚跪了一夜柴房。后来父亲派了别人,哥哥却忽然又要去,父亲叫我也跟着,还再三吩咐:“妇道人家不仁不义也就罢了,你们决不能对亲娘不孝!” 妈妈住在楚州,哥哥带我在街口打听,居然被人抓着就喊:“你们是那谁的儿子吧!”一群街坊围上来看热闹,都说像,长得真像,尤其是那个大的。然后妈妈抱着个三四岁的娃娃来了,乱着鬓发,笑起来眼角都是皱纹,布裙上还磨了个洞,人堆里却数她最抢眼。听见人家夸哥哥俊俏,她更是整个人都亮了起来,把怀里的孩子一把塞给哥哥,又伸手捉了我的腕子,欢天喜地地往家赶,到家就赶紧闩门,等转过身来,那脸上竟然没了笑。 “母亲这些年辛苦了。”哥哥跪下,我也跟着,还偷眼打量这间粗陋的屋子。 “我没脸回去,你们过来算是什么?”妈妈又抱起那孩子,我们的又一个弟弟,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鼻涕往下流。“送钱,五百贯。父亲知道母亲已是第二次改嫁,生活困顿,愿助不足。”哥哥说话向来声调平淡,那一刻也不例外。妈妈却笑了:“他岳五可是从不曾做过半点错事的,他的好意,我就领了罢!” ——《莫须有》
最多的叙述来自于岳飞之子岳云。本作中的岳云仿佛是一个精神上的现代人。从其父亲之外的视角,淡漠、冷酷地观察着这个破败、荒芜和战乱的世界,并且始终对于父亲的「精忠报国」保持着怀疑。
虽然尽忠报国只是一句空空的口号,但所谓的回报竟是以扼杀为目的的肆意诬陷——我趴在地上,无声地笑了:父亲,到头来,还是我赢你。生比死更残忍,而比毁灭更为无情的,是建造。为了建造他的国,官家,不,不只是官家,而是任何讲究成效的建造者,都可以贪得无厌地索取,理直气壮地毁灭,索取我们,毁灭我们。 ——《莫须有》
本书作者倪湛舸是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副教授,即是创作者,又是文化研究的学者。她对于网络小说的研究也颇为有趣,诸位若有兴趣,也可找来读读。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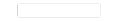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