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当年我们省厅领导特殊的管理风格,我的高中那会儿实行过应该是国内最接近“素质教育”的实践了:
1)不允许占课,节假日不许补课或者偷换概念开设补习班。因此即使到高三我们都是有正常休假的,体育课、广播体操、社团活动当然也不必说。
2)有学园祭。没错,就是日本动漫里那种,全校放假,以社团为单位准备活动内容,每个社团有自己的小摊位,还有个舞台用来表演节目。当初因为会画点儿画,经常被动漫社拉去连夜赶制海报。甚至还有个轻音部整点乐队演出……现在回想起来都十分不真实。
3)高一时还实行过一阵子选课制度,每人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电影鉴赏、诗词、发明创造……之类的,一到下午的后半截,大家就散开前往对应的教室上课,电影鉴赏课人都爆满了。后来大概管理起来太混乱,导致没能执行下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大学就是这样的模式。
代价当然是有,当然我现在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代价,除非你对人生的定义只有高考考大学这一标准:我们县城一本率低到离谱,文科班能上一本的人数平均不超过十人(全县),重本就更少了,大部分人都是过本科线就能举家拉横幅请客吃饭了的那种;另外是整个福建省那几年,因为出题过于容易,甚至被取消过自主命题资格。
再说点我自己的:即使是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我也是足够叛逆的。第一次高考我考了文科班第一(不过在其它省份的观念里肯定不值一提啦)但是因为喜欢上体育组的一个高一学妹,我以“还能考得好一点”为由果断选择了复读(我家人观念一向随意,当然也支持)而且拒绝了许多“保你能上清北,学杂费全免”的复读学校的邀请,执意留在了本校——因为本校成绩好的可以插班到应届的班级,而只有应届班级才能参加校运会(我那会儿年年校运会中长跑冠军)也就是说我留本校的目的一个是为了能继续见到她,另一个是为了在最后一次校运会上在她面前表现一下(她800米也很厉害!省队的水平!我也是主要迷恋这一点)于是,我以“那个考了第一还复读的奇葩”的江湖头衔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学校,一切好像又有了第二次机会,复读生们会觉得这是另一次煎熬,而我则不一样,我是带着绝对坚定的“使命”来的。
那会儿我就觉得高考对我来说意义相当有限(现在也这么觉得)用那时我QQ说说的描述,是“高考就是一坨屎”——用几个分数来决定我的人生也太搞笑了。反而我意识到高中的这些时光是那么宝贵(特别是有爱情加持的情况下)每一分一秒都独一无二,每一点感触都十分值得珍惜。复读对我来说仿佛是真的有了时间机器,我又回到了同样的起点,开始有了第二次体验的机会。
我那会儿有两个习惯,其中一个是上学大概率迟到。上学迟到是因为太不紧不慢,有时还会迷失在上学路上。有一次因为迟到双双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谈话,双双是因为同班的另一个女生也总是迟到,我说我是迟到小王子,她说那她就是迟到小公主……言归正传,班主任说的话我已经记不得了,可能也没听进去,听进去了也没意义——你们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我只是想到要不是因为复读,我连这样的场景都没办法再体验到了,反而很珍惜,阳光斜洒在办公室的墙上,一切都变得梦幻。
因为我插班的班级是实验班,属于下了课都没人出教室,大家继续趴在桌上学习的那种,因此我应该算得上是“模范班级的毒瘤”,迟到早退旷课,上课干扰女同学,有时第一节课能趴着睡到放学,作业更是从来不写,基本上就是为了考试才临时抱佛脚猛学一阵。我的另一个习惯是最后一节课一定不在教室,因为那时候体育组的体育生们开始训练,而我喜欢的女孩子又经常去,为了能遇到她,我自然跟他们也打成一片,再加上我也喜欢跑步,就干脆旷课跟他们一起训练了(也因此很多其他班的都误以为我是体育生)而我的班主任会走到我空着的位置前,问我同桌:“去哪了?”“又不在?”最后干脆就懒得过问了。
最终的结果是:最后一届校运会因为操场修跑道直接取消,我自然没能在她面前大放异彩;经过了一年的单相思,我的感情逐渐磨淡了——有多单相思呢,我这一年,想尽一切办法见到她,跟她说的话总共也就两句,还都是打招呼的那种。不过青春的感情和对方其实不一定需要有什么关系,回想起来我也无怨无悔。最后我考了个他们标准里还挺牛逼的分数(贼离谱,也挺讽刺,我都不知道怎么考出来的,也许正是因为我的心态问题反而学得好一些?)只记得回校拿志愿材料的时候,班主任看着我,绷着个脸嘴角抽搐了一下。在即将出发去上大学的那天上午,我在书桌前写下了给她的一封匿名信,诚挚地感谢了她,并跟她说了再见。骑着自行车去邮局把信投了出去,我的这段青春,从此就告一段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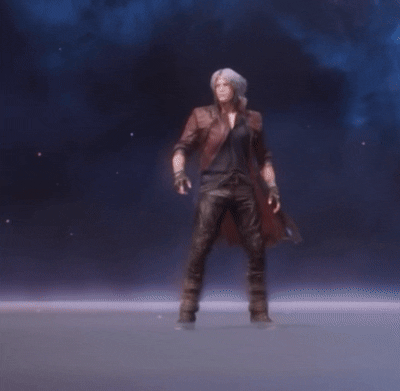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4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