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原文刊登于 The Journal of Immaterial Science, Editorial 作者Schlonk Günther
简介
简介
学术英语(Scientific English)是在希望学术出版物中被广泛使用的一种行文风格[^1],由于广泛使用“要津”这种及其要津的词汇,旁征博引“旁征博引”此类的短语而不是采用“行文”这样的行文,其比日常英语更为复杂和难以理解。在本篇中,我将解释它是如何变成这样的、它为何如此糟糕,以及我们对此应当如何“采取措施”
这种行文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行文是如何形成的
基督教和科学的共同点之一是他们都曾采用了一种平民无法理解的语言——拉丁语。主要原因有二:一个出于实际需求,另一个出于傲慢。出于务实的原因是:自罗马帝国在前现代时期解体后,拉丁语成为欧洲大陆唯一可能跨越地域的通用语言。出于傲慢的原因是:如果你将重要的档案和神圣的文字用一种只有你能看懂的语言写就,那么获取知识的权力就牢牢掌握在你手中了。
“上帝将他想如何让你行于这片大地的期许和指示都写在这本书中,全部都是拉丁语,不过别担心,我会给你解释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意在批判宗教。事实上,教会——至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最早推动现代化的力量之一,早在16世纪就已开始使用本地语言开展事务[^2]。几个世纪后,随着西欧拉丁语使用者的逐渐减少,科学界也开始转向使用日常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等,来撰写法律、行政和哲学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以及美国人普遍只说英语,英语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语言。
事实上,这并不算什么坏事,就语言而言,英语并非最糟糕的那一类。一方面来说,英语可以是精确、犀利且简练的,这些都是当你需要谈论科学和事实时必要的特性。另一方面来说,英语也可以是微妙、诗意且优美的,这些是你描述周遭世界时必要的。目前来看一切都好。
问题在20世纪开始出现,当政治与官僚主义的行文特征开始侵蚀其余所有书面化表达的时候,科学语言也未能幸免。这种行文风格先天就被设计用于掩盖和迷惑,而非传达和解释。在政治领域,此类“模糊言辞[^3]”只为一个简单的目的: 输出大量无意义的内容。在学术英语的领域,这便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但不是灾难的全部。另一部分问题来自于写文章的人的自视甚高,以及他们写作时所处的环境。科研出版的一个底层逻辑是同行评审:你的同行会评判你的内容。这个过程至少在12世纪就已经出现,但是在当今这个引用指标和绩效评估绑定的时代,这个过程被迅速极端化了。在现代科学出版中,作者普遍认为,文章必须写得尽可能复杂,才能彰显其成果的重要性。于是,科学家们竞相使用华丽、晦涩、自我陶醉的语言。这种风格如此盛行,以至于不遵循它就难以发表——就连笔者本人,在撰写这篇投稿在笔者就是编辑的期刊上的,批判该风格的文章时,也不自觉地落入其中。由此可见其普遍性。
某种程度上,教廷其实比科学界更加进步:你可以用100多种语言参加教堂礼拜,但科学家却固守于一种难以理解的行话。如同无聊版本的天主教。
为何这种风格如此糟糕
为何这种风格如此糟糕
与笔者平常在这本期刊上发表的那些狗屎东西不同,这篇文章我确实经过审慎思考。我的思考最终凝结为以下几点对现代学术英语的不满:
i) 它极难阅读;
ii) 它极难书写;
iii) 它完全没有灵魂。
考虑到这些问题,并充分意识到其中的细微差别与复杂性——我慎重地认为,学术英语可以去他妈的了。
“Jigglimide”母核结构(jigglimide moiety)是合成化学家工具库中一个具有特权地位的结构基元。其兼具显著的体内稳定性与广谱溶解性两大特征,为含有该结构的活性药物成分(API)候选物赋予了多方面的潜在优势。因此,围绕 jigglimide 母核的引入与构建方法学的研究在近年来已被视为至关重要。然而,现有的 jigglimidification(jigglimide化)策略在区域选择性不足、催化剂周转率受限以及原子经济性虚高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制约。在本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催化 C–H jigglification(C–H jiggl化)方法,该方法以优雅的方式对上述问题实现了系统性的改良。
Jigglimide 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官能团。它既具有良好的生物稳定性,又能溶解于多种溶剂中。 因此,jigglimide 常被用于药物候选分子的设计中,而能够在分子上引入 jigglimide 的反应也十分实用。不过,现有的 jigglimidification(jigglimide化)反应往往效率低、浪费原料,而且选择性不足。在本研究中,我们介绍了一种新反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些问题。
问题一:学术英语极难阅读
问题一:学术英语极难阅读
大多数科研人员的浏览器里,随时都开着四百多个标签页[^4]。其中一些可能是数据库或常数表,一个会是他们自己的Scopus作者主页,而剩下的那394个,则全是他们“总有一天一定要读”的文献。那为什么他们迟迟不去读这些文章呢?因为从现代论文那冗长而空洞的文字海洋中筛选内容,简直就像淘金——只不过这里的“金子”看起来和泥沙几乎没什么区别。解读那些学术黑话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以至于大多数人读不了几句就会走神,开始琢磨自己到底多久没打扫房间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上文展示了两段示例文字。第一段是一篇关于虚构的“Jigglimide基团”的标准论文引言,第二段则是将第一段翻译成简洁明了、直截了当的英语后的结果。如果有人声称第一段更好懂,那八成是在故意抬杠。
那么问题来了:在从第一段“翻译”成第二段的过程中,有任何实质信息丢失吗?
我认为答案很明确:除了那十几个我们显然用不着的术语之外,一点都没少。
问题二:学术英语极难书写
问题二:学术英语极难书写
如果阅读学术英语是一种苦差,那么写学术英语就像把一个倒立的松果弄出你的屁股。出版社似乎希望我们对自己的文字进行类似一些古代中国缠足的陋习——把它们压碎、重塑成某种时尚的畸形模样。
敏锐的读者可能会察觉到我在这段话里带着一些私怨——确实如此。对我来说,用学术自嗨语写论文,就像试图把方钉塞进鸽子里:无论怎么使劲都塞不进去,最后只会屎溅一墙。抛开这些怨气,问题其实很简单:做科研已经够难了,写论文不该更难。我们常常看到审稿人建议那些英语流利的作者“让母语者帮忙润色稿件”。那么,想象一下对于那些非英语母语者来说,用这种自嗨语言写论文该有多难——尤其当你连在 Duolingo 上都还没学到“围着围巾的熊向你解释什么是‘相关语境范式’”的等级时。当编辑们坚持要求科学必须用这种语言发表时,他们其实是在人为地增加全世界非英语母语科学家的写作难度。
问题三:学术英语缺乏灵魂
问题三:学术英语缺乏灵魂
这是前两个问题的根源。当语言被像抹布般拧干时,最精妙的美感会消失,最鲜明的色彩会褪去,最终变得既难读又难写。或许这正是AI特别擅长生成此类文字的原因。
或有读者质疑:这是科学,不是诗歌,为何要强调语言的灵魂?我同意学术英语应当尽可能简洁清晰地传递事实,但这不意味着它必须被完全“蒸馏”。科学终究是人的科学(至少目前还是),在其中保留些许人情味并无不妥。大多数科研项目都像坐过山车:需要足够高的GPA才能获得入场券,过程中充满猝不及防的起伏,而我们只能紧抓扶手,祈祷能平稳着陆而非悬在半空。若能提及这些波折,作者便能引发读者的共鸣、理解与尊重。
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该做什么
当科学家想到某种干预措施,却不确定是否有效时,他们会去做实验。这正是我们也该做的事。
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一步开始:用直白、真诚的英语写论文。如果你觉得这很难,就想象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拿着电击棒站在你背后催你写。我没能找到任何一篇用平实、直接英语写成的科学论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能实现。我们只需要一个勇敢的人站出来试试——最好是H index够高的那种,这样期刊编辑才不敢一眼就把稿子毙掉。我本可以试试,但我既没有那个影响力,也没有任何值得发表的成果。
总结
总结
学术英语就像一头骆驼,背上驮着一千根由废话堆成的稻草。在本文中,我解释了这些稻草是怎么堆上去的、为什么骆驼走不快,以及如果拿掉几根,也许它能跑得更快。抛开寓言的骆驼不谈——未来或许不远,学术论文可能将由 AI 完成撰写、审稿、出版和阅读,届时“科学语言”的存在本身将变得纯属学术问题。 如果你不想迎来这样的未来,现在就该挥斧砍掉那套学术自嗨语言,让一点人性重新流进我们的文字之中。
附注和引用
[^1]: 当然这里说的是英文,不过其他语言大概也有他们自己的版本和自己的问题
[^2]: "De armento cacas” M. Luther, 1517, Wittenberg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Graffiti. 1, 1–95.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asel_word
[^4]: "Put it on my tab barman: academic reading habits in the modern age” P. Crastinator, 2020, Journal of Spurious Statistics, 8, 5–2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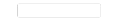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