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一
1993 年
那年我二十六岁,在市轻工局档案科干内勤,是个没人注意的小角色。
说是档案科,其实就两个人。我一个新人,还有一个叫邱仁德的老职工,人都喊他老邱。小个子、驼背、脸常年皱着,好像谁都欠他八毛钱,但人倒是没什么恶意。只是话少,也不爱搭理人。
我们那栋办公楼建于 1974 年,砖混结构,一共五层,灰黄外墙、绿漆铁窗,一楼是信访办,三楼是领导办公室,我们在四楼,靠西的尽头。
这栋楼早该翻新了。楼道里的白炽灯时不时就坏,厕所水龙头响一宿都没人修。每次上楼都得靠「哐哐哐」的脚步声,把感应灯唤醒几盏,不然黑得像井口。
单位最近在做老档案数字化,要整理七八十年代的纸质卷宗。我是新人,自然被安排加班。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晚上都留到七点半,有时八点。
老邱也常留下来,但他不是为公事。档案室角落有个他自己摞起来的小办公桌,上头搁着一台收音机和一盏旧台灯。他下班后就在那坐着,不声不响地翻什么黄页旧书,有时候点根烟,有时候喝白开水。
他总背一个深咖啡色的公文包,方方正正的,拎着走在楼道里,皮子摩擦地砖的「唰唰」声特别响。后来我发现,不管白天他拎没拎着,下班离开前总会从座位后头把那只包拿起来。就像出门前的一种仪式。
那天是个周五,天阴沉沉的,下过午后的雷阵雨,空气里全是潮味。我拖到晚上七点多,准备收工了。楼里基本没人,除了我和老邱,还有信访办的一个老头据说喜欢趴窗看外头下棋,也不清楚是不是那晚也在。
我刚收完最后一份「84 年企业购煤申请表」,准备把档案柜锁上,忽然听见楼道里传来「唰——唰——」的声音。
老邱又走了。
每次都是这个声音,他那双皮鞋走在水泥地上,拎包的节奏不紧不慢,一下一下特别均匀。唰,唰,唰,走到走廊尽头,就该是楼梯了。然后就是楼梯「咚……咚」的回音,越走越远。
我随手关了电扇,刚准备熄灯,就看到办公桌上有一样东西没动:老邱的包。
那包放在他座椅后头的小凳子上。深咖啡色的皮面,两个旧扣子磨得发亮。
我愣了几秒,脑子里冒出个念头:那他刚才拎着的是什么?
楼道还响着风,从窗缝灌进来的风吹动百叶窗「咔咔」响,像有什么人在敲。档案室没锁,但我不敢出去。我靠着桌边站了一分钟,盯着那个包,心里发毛。
「是不是记错了……他今天根本没带包?」我这么安慰自己。
可问题是,我记得很清楚——下午他吃完盒饭,把包拉链拉开,拿出一本报纸,边吃边看《南方周末》的旧版专栏。
我慢慢走过去,靠近那个包,不知哪根神经不对劲,竟想用手去摸。
刚碰到一角,楼道的声控灯忽然「啪」地亮了一盏。
不是我动的,我还在屋里。
我下意识缩回手,愣在原地。楼道安静了一瞬,又陷入黑暗。那盏灯只亮了三秒,就灭了,像是被什么不耐烦地「提醒」了一下:有人还没走。
我不敢多留,赶紧收拾好东西,把门带上,飞快地下楼,连头都没敢回。
二
第二天,我照常来上班。
窗外天还是灰的,档案室那条走廊依旧潮潮的,墙皮起了层薄壳。楼下杂物间的灯一闪一闪地跳,像个头疼的病人。
我以为老邱会来,毕竟他昨天走得匆匆,包也没带。可那天一整天,档案室的门都没开过,铁门上挂的生锈小锁纹丝未动。
直到下班,我都没再看到他的人。
我有些不安。倒不是说我担心他出了什么事,毕竟他那人总有点奇怪,神神叨叨的,今天来明天不来,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他昨天确实说了「你走吧,我得锁门」,包却没拿走——你说他是忘了?可老邱这人背包的动作就像穿皮鞋,像习惯了一辈子的流程,说他忘了,我真不太信。
我下班回家的路上,总觉得包的皮面摩擦声还在耳边响。唰,唰。
第三天中午,办公室开小会。
王姐边敲计算器边说:「老邱这是又请假了?还是没来。」
我抬头,说:「不是吧?他不是一直值这两天档案室嘛。」
王姐摆摆手,「你记错了。老邱前天就没来,昨天和今天他都挂在请假表上,刘主任批的。」
我「嗯?」了一声,愣住了,头皮有点发紧。
前天没来?
我脑子一下子开始倒带——那天晚上的回忆是清晰的:包的声音、他坐的位置、他抬头的那一眼、走廊尽头的脚步声、还有包。那都不是我幻想的。
我想了一圈,忍不住站起来,说:「不是,那天晚上我跟他一块加班的。他还——他走之前,把包落在了档案室。」
王姐愣了一下,「你俩晚上一起在档案室?没听他说过啊。」
我也说不清了,只能支支吾吾地坐回去。整张脸像被人泼了一瓢冷水。
我决定下班去档案室再看看。
档案室的门还锁着。但铁门的锁明显换过了——老锁是个圆头弹簧锁,钥匙不好插;新锁是平头的铜锁,反光还亮。
我皱了下眉,去问门口那位看大门的赵师傅。他人老实,说话慢,我跟他挺熟。
我开口问他:「赵师傅,档案室的锁谁换的?」
他想了想,「哦,昨天下午有人来换的,说是领导安排,说老锁老锈得不行了。」
我问:「是谁换的你记得吗?」
他晃了晃脑袋,「不熟,好像是保卫科那边借来的人吧,也没做登记,穿着工作服,看着不像咱们单位的。」
我不再问了。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晚上我没走,故意留下来晚一点。快八点时,我拿了钥匙,偷偷走进档案室。
门锁不是原来那个,开起来咔咔响,但里面的陈设一模一样。墙角的铁皮柜、桌上的旧茶杯,甚至连那本被压在角落的《人事档案录》都在。
我迅速看向角落。
老邱的包——不在了。
就像它从没出现过。
可我记得我看到它。我甚至记得包扣子没扣紧,边角露出一点文件封皮,是红色的。
老式的那种档案袋,左上角印着单位编号。
我努力回忆那串编号,却怎么都想不清了。
就像我的脑子,把那个细节自己擦掉了。
我盯着老邱的办公桌,发现桌上多了张白纸,上面压着一支掉了漆的钢笔。
纸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右下角用红笔歪歪斜斜写了个日期:1993.7.13
今天是 7 月 15 号。
我盯了很久,拿起纸翻了翻,背面干干净净。我突然注意到,桌下的抽屉开着一道缝。
里面空的,只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
我打开纸条,上面写着一串字,像是潦草的笔迹:
丨「东西不要留,留了就别说。」
我读完,后背一阵发麻。
东西。包?还是指什么?
而那句话——留了就别说。像是告诫,又像是威胁。
我把纸条收进兜里,没再多呆,锁上门就走。
从档案室出来那一刻,我看到楼道灯灭了。
整个楼道陷入一片昏黑。我下意识拍了两下手,感应灯没反应。
可身后走廊的尽头,却亮起了声控灯。
我站在原地。
那里没有人,但灯亮了。
而我,听到了一阵模糊的、几不可闻的唰——唰——唰的声音。
像是什么东西,拖着,在走廊深处擦过墙壁......
三
老邱请假这件事,我始终不信。
如果他真的前天没来,那我跟谁一块加的班?
如果他根本没出现,那包呢?纸条呢?那晚档案室的灯是谁关的?锁是谁上的?
刚工作我总是很积极加班也老留下来,每天最早到的是谁,最晚走的是谁,我心里门儿清。老邱是习惯最后一个走的。他锁门、关灯、拎包、咳一声、再慢慢踱出走廊。那声音我闭着眼都能分辨得出。
可如果说,那天晚上的「老邱」不是老邱,那我当晚到底是碰见了谁,是我的记忆在撒谎,还是真有些什么?
我决定从头开始查。
我先去了人事科。
那时候没有电脑联网,查人事档案还得一页一页翻。好在我跟人事那边的周哥熟,他给了我一个借口,说你查老邱的入职年限、调动信息,拿去翻吧,但别乱动。
档案一共两册,时间跨度从 1979 年到现在。
第一页,是老邱当年招工表格,照片上他戴着深色贝雷帽,眼神怯怯的,有点不像后来那个背着包慢吞吞走路的老邱,工作这些年改变还挺大。
我翻到最近几页,想看看他请假这事。
但很奇怪,这两年的记录全是空白。
调休、病假、轮岗,一条没有。
按理说,单位人事记录非常细致,尤其这几年有外包工调岗、退休临时工转编制等情况,怎么老邱的记录反而断了两年?
我把整册都翻遍了,唯一一份近年的文件,是一张请调申请书。
时间是——1993 年 7 月 10 日,落款是老邱的亲笔签名,申请「因家事原因,调往下属第二资料室暂管」。
下属资料室是我们单位一间很偏的小库房,早年间负责收集政府旧函件,现在基本废了,听说常年没人值守。
最不对劲的是:这份申请上,主管签字是刘主任。
可我记得清楚,刘主任从上个月才接任档案科主任职务。1993 年 7 月 10 日,她根本还在别的科室。
我把纸悄悄拍了个影(照相机当时不多,我借了资料室的傻瓜机),回去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这份申请书,是补上的?
当天我就去找了刘主任。
她一开始不愿多说,只是摆出一副标准官腔:「老邱调岗是组织安排,身体也不是太好,你们不要多问。」
我说我只是关心他,毕竟他包落在档案室,至今没人拿。
这句话似乎戳中了她。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突然问:「你说他……什么时候包落下的?」
我说:「7 月 13 号晚上。」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话变得缓了:「那天,他本来……本来没安排值班的。」
我试着问她:「你有没有见过他请假?调岗?」
刘主任低头点烟,顿了一下,说:「他是个老同志,手续……当时可能是补了。」
「当时?」我追问。
她点了下头,语气模糊:「你要真想找他,也行。去第二资料室看看。」
她递给我一把锈钥匙,说:「诶,小张,你别说我给你的,我没授权。」
第二资料室在单位老食堂后面,一排红砖房的最尽头。那地方我都快忘了还有门,门框上长了青苔,铁门把手发黑。
我试着用钥匙一拧,门「咔哒」一声响,开了。
里面很黑,一股酸臭的旧纸味。天窗落灰,地上全是老鼠屎和碎纸。几排老木架上摞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黄纸信封,很多都潮成了片。
我打开手电,一路往后走。
最里面,是一张桌子。
桌上,有一把椅子斜倒着,地上是一只……皮包。
我愣住了。
我记得这个包,是老邱的。棕黑色,两个铜扣。左边扣子松了,边角裂开一小条口子,露出红色封皮。
那张红色封皮,是我那晚看到的那一份。
我不敢动,只拿手电照着看。红色文件袋上,写着:
「档案封存编号:A19930713」
我看着那串编号,后背凉透了。
这不就是我那晚拼命想记却怎么都记不起的编号吗?
我手电微微一晃,地上的灰尘飞起。
红色档案袋下,压着一张半张照片。
照片发黄,上面是一个熟悉的背影——老邱。
但照片里他站的位置……正是档案室楼道尽头。
他正朝镜头缓缓走来。
身后,墙上的声控灯微亮。地面一长条影子,被拉得极长,模模糊糊——
像有个什么东西,紧贴着他脚后。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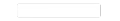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