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二、风语者的片段
二、风语者的片段
「响-2」是在第四晚的凌晨录下的,和第一段一样,由「静区录音」程序自动触发。那一夜我没有被耳鸣惊醒,只是在清晨查看设备时,注意到了这段新的音轨。
它的波形图极其整齐,像人工生成的模型。每 0.72 秒,就有一次规律的脉冲,频率范围保持在 43 到 46 赫兹之间,像是低频呼吸,又像心跳,只是没有温度。
我戴上监听耳机,反复播放这段声音。耳膜开始微微发麻,那种感觉就像有人在你耳边轻声念着什么,但永远只念到一半。
我尝试使用降噪插件,把风声背景滤除,结果出乎意料:声音反而变得更像语言。一种我无法分辨来源的语言,听起来不属于任何已知的语系,也不像动物的叫声。它缺乏语义,却有某种结构。
我用语音分析插件尝试对其切片,还原音素结构。软件返回的结果是:
「齿龈塞音+摩擦音组合,带元音变形特征,疑似人为音调模仿。」
说得通俗点,就是它像在学说话。
我又尝试反向播放、频率翻转、时间压缩,甚至用语言学教材中的古语音标去注释它。每一次处理都只让它更「像话」,但始终没有意义。
可最令我在意的,是一种心理上的诱导感。
我开始不由自主地模仿它。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一种难以言喻的冲动。
那天夜里,我把设备调到手动录音,对着空无一人的帐篷说出:
Sha…sa…do'…kel…sa'a…
这些音节是我从分析图中抄下来的。听起来毫无意义,但我说得很自然,就像早已学会。
回放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说出的,只是前半部分。
后面两个音节,并不是我说的——但音色与我几乎一模一样。
我反复比对录音,甚至调出旧的样本与之对比。结论只有一个:那声音不是从我口中说出的,但它用我的声音继续了那个「句子」。
我没有立刻感到恐惧。恰恰相反,我被一种深层的好奇攫住了。像是小时候用钥匙打开一把锈蚀的锁,锁里落出的不是财宝,是另一个世界。
那一晚的梦,比之前更深。
我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井边,井壁上不是石头,而是嵌着密密麻麻的嘴唇,全都微张着,像在等待风的灌入。风从井底吹上来,穿过这些嘴,带着呢喃的回响:
「我——是——你——所——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被风吹醒的,还是被这句话拉回了现实。醒来后我的头很痛,就像有人在脑袋里用钝器敲击。
从那天起,我的文字开始出错。
记录笔记时,我常常把单词拼写顺序颠倒,或写成奇怪的拼接词。比如将「recording」写成「cordingre」,将「waveform」写成「formwafe」或「welforma」。
更诡异的是,这些错词并非随机,而是反复出现,格式固定,像是某种音律在潜意识里驱动我。
我把这些词写在便签纸上,贴满了帐篷内壁。现在它们看上去更像一首诗,或一段宣誓词——而我,不止一次地在念它们,就像在复诵什么。
也是在那个时刻,我突然记起了一个名字。
它不是浮现在脑中的词语,而是一段无法被忘记的声音。一个不属于任何语言的「称谓」,像风在裂缝中穿行时偶然形成的音调:
Ish…Sa'a…
我记得这个名字。
大学时,我曾在图书馆的罕见文献区读到一本尘封的黄皮旧书,《帕米尔语前宗教音义初探》(1952 年,作者署名为 H.F.Drohm),书籍封面已近乎脱落,内页纸张泛黄,散发着干燥的霉味。那本书甚至没有被系统编入正式索引,像是某个研究生留下的私人藏品。
那本书讨论的主题诡异至极:作者主张,在帕米尔山区流传的某些史前民间信仰并非基于图腾或祖先崇拜,而是基于「声音」本身的拟神性。换言之,他们崇拜的不是神明的形象,而是「某种被听到过的声音模式」。这些声音无法复述,亦无法转录,只能通过模仿来保留。
其中有一节记录了一种被称作「风语痕迹」的祭祀仪式,据说祭司会在风中静坐,将耳朵贴近山石,在耳语之间「听见神明」。Drohm 在那一节的脚注里写下了一组音节,他自称无法翻译,只能以国际音标近似还原——
/ɪʃsaʔa/
他称这两个音节是「模糊但反复出现」的核心语音单元,具有「某种催眠性」与「语言结构前的嵌合律感」。
当年我草草翻过这一段,只当是学术异想天开。
但现在,这个声音就在我耳中,一次又一次,用 0.72 秒的节拍对我说话。
「响-3」与「响-4」也录下来了。它们比前两段更稳定,节拍更清晰,甚至在接近结尾时留下了一段无意义的低语。
我试图标注它们,但发现自己已经不敢重听了。
因为那声音在叫我。
是我的名字。
用我自己的声音念出来的。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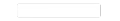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