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前言
前言
“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了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亮光也看不见。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境,凝视了好一会。”——《城堡》第一章 开篇
《城堡》之于作者或许可以说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但是窃以为之于社会进程的演化,其故事走向和结果并非完全不可预料。故事中各种事例的高度写实性,以及作者在发散、处理这些意向时的高度抽象性,使得作品变得较为难以阅读,而较容易于理解。使得并不需要多么丰富的想象力,便能将文章里种种普遍的意向投射入读者自身所处的物理现实之中。或许在评论的角度上而言这篇小说可以被以任意的方式修饰、整理或归类,但同时也使得相关评论并不指向与作者或作品,取而代之的则是指向于评论家自身。
出于以上理由,或许我们可以怀疑作品之中所展现出的种种[客观口吻]是经过精心修饰而出现的,种种被观测到的客观实在并不完全出离于经验,但又可以与任意种类、任意形式的观测者意识相结合,在这种含义上,作品将作者明确而可见的主观观点隐藏起来,隐匿于故事中所展现出的种种真实状态之后;隐匿于故事所展露出的家庭关系、社会秩序之后;隐匿于故事人物相交互、对抗的模式之后。
“于是他继续前行,但路途漫长。因为那条路,也就是村里的主干道,并没有通向城堡,它只是靠近了城堡,然后,仿佛故意一般,它转向了,虽然它并没有远离城堡,但也没有更靠近城堡。K一直期待着这条路终于会转向城堡,而正是因为这种期待,他继续前行;显然是因为疲倦,他犹豫着是否要离开这条路,他还对村庄的漫长感到惊讶,它似乎没有尽头,一间间小房子、结冰的窗户、积雪和无人迹的景象不断重复一—终于,他挣脱了这条束缚他的路,一条狭窄的小巷接纳了他,积雪更深,拔出陷入雪中的双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他汗流浃背,突然间他停下了脚步,再也无法前行。”——《城堡》第一章 K走向城堡
在这种意义上,阅读这篇文章并尝试理解的行为,几乎无异于主人公“K”尝试走近城堡。
K,无知者/求索者/牺牲者
K,无知者/求索者/牺牲者
展现K无知的并不只是某一个具体的教训,而是充斥在他怀有明确目的去推进的每一个具体事项之间;充斥在城堡相关每一个与他进行交互的具体人物之间;充斥在每一次K拒绝城堡方人员所施加的“恩赐”并再度重申自己只是要讨个公道时。与K所接触的几乎每一个人,几乎都以各种方式表示过这样一个信息:“关于城堡/克拉姆/这里的规矩,您无知得可怕。”所有人都在尝试向着K解释说明和村子、城堡有关的一切,提供的所有这些信息以这些角色们所认为的不会危及自身安全为前提(就像作者写作时所使用的文笔风格这样),每个与K对话的人都在填充着城堡相关的新信息,这些信息与他人所提供的信息相互交织,相互排斥,部分地否定先前所提供地种种可能性,并且提供给K新的期望,使之对于自己所要作的事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K这一角色的无知与无辜相对应,根据其自称,远赴城堡周边来求取一份作为土地测量员工作的正式任命。K对于城堡当局,及其周边村子的信息一无所知,无论是人员构成或者是管理构架、甚至是敌方风俗。这直接导致了K并不尊重当地的权贵,并不小心谨慎地对待所有地表层规则和潜在规则,并不懂得在何时退让、并放弃先前自己所主张地权益。K关于此地的无知一步步地加深了其处境地困难,所在地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可以向他提供先前所未知的信息,这些信息彼此间相互支撑、甚至在部分时候相互否定,然而产生的作用却可以预料:所有求得的信息,都将会进一步加深K的无知和无助。
求索的行为却不仅仅是针对于信息而言,同样表现在求得“所处在对应社会构架中的地位”,K作为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并不能通过城堡电话的应答者获得;并不能通过克拉姆的“私人信件”获得;并不能通过村长处未被寻找到的公函处获得(尽管村长此前煞有其事地声称“上面有‘土地测量员’字样、底下还划了蓝道道”);并不能通过私人秘书、比格尔、埃朗格的讯问获得。K所求索的,作为“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丢失在浩如烟海的公文和公函中,丢失在一次次间接传达的电话通信里,丢失在秘书与秘书的秘书所批复的一张张小纸条内。所有他所预期的社会性身份都是预设的,无论这种预设来源于环境或者是给了他某种潜在期望的具体个人,K唯一能够被信服的身份只剩下了一个,他不能成为土地测量员,不能成为当地女招待的未婚夫,不能成为在此地教师的助手,只能成为“不被信任的外乡人”。而他所求索的程序正义(或者是某种微观程度下的真理)很显然并不会那么快地到来,至少在其尚处于人世时显然不可能到来。K为求索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显得徒劳无益,更何况还将一步步加深K所处的困境,并且为他后续的行为增添新的阻力,这种情景所表现出的阻滞感同样体现在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中,只不过在人际庞杂,阶层林立的《城堡》里,这种现象同样突出罢了。
K的牺牲并未直接在故事结尾中表现出来,但是对于卡夫卡所表现讽刺方式的熟悉,使得K真正可能遭遇的结局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城堡所能够给予K的身份与认同,仅仅可能存在于K无力继续抗争,乃至于无力继续生存时。作为作者的卡夫卡常将安宁和喜乐的情绪安排在主角所出场前,以及主角无力抗争一切并故去之后,用生命期间的晦暗色彩和生命之外的鲜活来凸显出针对整个生命历程的讽刺感。在中文里 色纯为“牺”,体全为“牲” 。K这一角色的无比强烈的执着构成前者,其可塑造性、可能存在的珍贵价值构成了后者,精神世界的纯粹和对现实世界投射的执着使得这一角色成为了整个故事中最适宜成为献给某种超然存在的祭品。在这种意义上,K生命的被动舍弃并非是正义的,但是却符合了程序所预期的,城堡当局所预期的,乃至于符合整个村子各方潜在需求与预期的程序正义。
卡夫卡没能完成这篇作品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将写作视为某种程度的自我体现的方式的话,卡夫卡的写作间杂了自渎与自戕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在故事剧情中不断地对自我投射的身份造成难以忍受的伤害,另一方面又从彻底击倒这些角色之后的愉悦中获得了超然般的自我认同感。通过在作品中否定“威权”,并解构它的同时,卡夫卡本人获得了借由创作来任意创造,任意否定,任意定义的威权。
克拉姆,名为权力的幽灵
克拉姆,名为权力的幽灵
克拉姆存在,如同权力存在,就好像城堡中所有的权力都来源于指向于那不可言说的存在。克拉姆可以被看到,许多人都声称自己见过他,关于这个形象的出现从弗丽达(酒馆女招待)开始。弗丽达引导K从窥视孔中隐约地观测克拉姆的身影,并且以克拉姆的情人自居,以获取酒馆各方明面上或者是潜在的资源。
“这而得人呢”K问。她撅起下嘴唇,用一只非常柔软得手把K拉到门边。通过这个显然是为了窥视而钻出的孔,整个隔壁房间他几乎一览无余。 房间中央的一张书桌旁的一把舒适的圆靠背椅里坐着克拉姆先生,一盏低悬在他面前的电灯亮得刺。一个中等身材,体态肥胖臃肿的人,脸上还没有皱纹,但是由于年龄关系面颊已经有些下垂。黑色的髭须蓄得长长的。一副歪戴着的夹鼻眼镜遮住眼睛。——《城堡》第三章36页,K从窥视孔中看向“克拉姆”
弗丽达通过这样未被否定的宣称,而成为了酒店老板娘所“心爱的女佣人”,通过关于自己作为情人身份的宣称弗丽达获得了切实的权力,使得她在工作环境中享受到种种额外的资源,在工作环境外得到种种额外的礼遇。在出于自证身份的迫切需求上,弗丽达为了向更多人证明自己作为克拉姆情人的身份而与K相互利用,利用其外乡人的身份,利用其比佣人可能还要更加低微的身份,塑造出一个对弗丽达穷追不舍、至死不渝的痴情人形象来。
但从弗丽达角度对于克拉姆的观测真的准确吗?她所编造的所有故事,塑造的所有形象都将作为她从克拉姆处窃取的权柄。以弗丽达为原点的观测之真实性同样在后文中被另一位酒馆女招待(佩碧)所否定了。身份同样低微的存在将弗丽达塑造身份的方式视为谎言,同时认为K只不过是弗丽达用于证实自己作为克拉姆情人身份的牺牲品。
“...这样一个姑娘要是走合法途径也许连一个客房女侍也当不上,她自己也知道,有几个晚上她曾为此哭泣,紧挽住佩碧,将佩碧的头发绕在自己头上。但是她一当起差来,一切疑虑便一扫而光,她以为自己是最美的,而且她善于用正确的方式使别人也产生这样的感觉。她了解这些人,这就是她的真正本领。而且她撒谎得快,行骗得快,让人没有时间仔细观察她。 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大家长着眼睛,终究会看清楚的。但是在她发现有这样的危险的那个时刻,她就已经准备好了另一种手段。譬如最近她就搬出她和克拉姆的关系。她和克拉姆的关系!你若不相信,你可以去核实嘛,你去找克拉姆,去问他。多么狡猾,多么狡猾。”——《城堡》第二十五章284页,佩碧对于弗丽达的看法
克拉姆不可见,如同权力不可见。K从窥视孔中得见,而后在马车处久等而无法得见,得到了其私人信件而无处可用。就像没人能够通过克拉姆来证伪弗丽达情人身份一般,就像K费劲千方百计也不可能寻得克拉姆的正式聘用文书一般,就像执行其意志是克拉姆位于各地的代理秘书而远非他本人一般。而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又无比尊崇他们认知之中的“克拉姆”,许多人仿佛就连提及他的名号都显得多少有些不敬一般。如同现实之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对权力来由或去向有一套自己的的看法,但是在此范围之中更多的人更倾向于闭口不谈。权力每一次被讨论,每一次被定义,其范围就缩减一分;权力每一次被敬畏尊崇,每一次被纳入潜移默化的认知,其范围就扩充一分。在这种情景中,克拉姆(权力)无意志,无道德,无善恶,仅需要凭借权力结构的演化过程就可以不断推演自身,就可以起到权力在对应结构中预期发挥的功能,就可以调动并生产出权力扩大、演化自身所必须的生产条件。
自此,K与克拉姆在名称上,在故事的构架上起到了某种近乎于同构的性质,追求权力的的人和不可得的权力本身。在故事内外,克拉姆(权力)的幽灵同样遍及社会秩序所能够接触到的每一个角落,而人们往往只有在其切实施加不可抵抗的伟力时才会惊呼其不可战胜。
阿玛莉亚,“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阿玛莉亚,“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信是索尔蒂尼写的,寄给戴宝石项链的姑娘。信的内容我不能复述了。要阿玛蒂亚到贵宾酒家他那儿去,而且要她立刻就去,因为半个小时后索尔蒂尼就得乘车离去。那封信里全是些不堪入目的话。谁不了解阿玛蒂亚并只读了这封信,谁就一定会以为,有人敢于这样给这姑娘写信,这姑娘一定是个破烂货,即使她根本就没被人碰过一下。这不是情书,其中没有一句恭维话,索尔蒂尼显然是恼火了,因为见到了阿玛蒂亚后他便心神不定,他无法专心工作了。”——《城堡》第十七章188页,奥尔嘉关于家族遭遇的描述
关于阿玛莉亚与巴纳巴斯一家的故事可以进行一个粗浅的总结:权力并不彰显于持握它的人,而显现在它施加的人身上。就是这样一封求欢的非正式书信,阿玛蒂亚拒绝了、并撕碎了这封信,使她们一家拒绝当局的行为广为人知,然而她们一家却并未受到官方直接的处罚,取而代之的是所有村民的疏离,规避与之交往、不再与之贸易、往来、施加以鄙夷和排斥。
“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什么正经的惩罚。人们只是不再和我们来往而已。这里的人,也包括城堡里的人。我们当然觉察得到这儿的人的规避,而对城堡方面我们就丝毫觉察不到什么了。从前我们也没觉察到过城堡的关怀,现在我们怎么会觉察到一种骤变呢。这种宁静是最糟糕的。人们的规避远不是最糟的,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某种信念,也许和我们也根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今天的鄙视也许还根本不存在,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恐惧,现在他们还观望事情会怎样发展。”——《城堡》第十八章203页
自此,这一家人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双重含义之上的难以生存。权力的伟力在这样一个家庭的遭遇中彰显无遗,向故事里其他所有的村民昭示拒绝官方人员的要求将会遭受什么样的下场,而这样一个执行结果由城堡官方的潜在默许和村民主动疏离两者共同构成。在这种情景之下,城堡与村庄构成的整个社会单元中,每一个个体都成了行刑的潜在执行者,而行刑的内容则为与对应一户人家的所有成员保持社交距离即可。
《城堡》之中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单元之间的隔绝尚且需要参与者有意识地执行,而现实中基础的社会单元之间的疏离、隔绝则可以天然自动地完成这项功能。K作为缺少常识的主人公天然比其他常识角色具备更少量的人权,作为外乡人的身份天然比本地人具备更少量的人权,作为城堡当局的聘用方天然比城堡公务人员具备更少量的人权。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不服从、拒绝服从的个体都拥有着成为阿玛莉亚的潜质,都将会在不同时刻、不同程度地面临与其相接近的境遇。在这种意义上而言,阿玛莉亚与K的境遇相近,这种情景不因二人的性别不同、认知阶层不同而区别对待。
焦灼着的和冷漠的
焦灼着的和冷漠的
言尽于此。
感谢
感谢
感谢小伙伴西呼金提供的德语翻译校对。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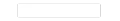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