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2075年3月2日 星期二 多云转晴
今天上午,我接到了一个特殊的委托。客户说自己的父亲是人类学家,曾经在深山中考察某个村落,直到前几天他突然病逝。客户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他考察时做记录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语义不明的中文和标点符号。他看不懂这些文字,但明显感觉到笔记的内容对学术界有重要作用,于是希望我能够帮他翻译出记号的内容。
我点开邮件里附带的文件,看到了笔记的节选:
【她她——它】
她:嗯!它它。
她:嗯~你它它?
她:嗯~它它。
【他她——它】
她:你啊它我它!
他:哈它它!哈它它!
她:呜啊啊啊啊!她!她!
啊她它它,它它它她她。
她:你它!???它—她它?
他:她它它—~,——~它我它。
她它他它它,——它它它,它她它/。
【他他——它】
他:你你它——?它?
他:它——。我我它它这。
他:我它——~你你它它,那个——它它它它,我我它“它”它,它!它它它。
他:它——这。你你它它它——。它——它它它它它。它~——~你你它它——,我它————~它你你它它。
他:哈哈,它——它——~,我我它它。
【他他——它】(它它它——)
他:那它它——。
他:它它?
他:那那啊!你它它——~?
他:哦,那——~“萤火虫”??
他:“萤火虫”——?
他:那它它。
他它它。
他:那那,——~“萤火虫”。"
嗯……确实是一份奇怪的笔记,简直像是加密文本一样。虽然全文都是用中文记录的,但几乎全是“它/她/他”等代词,夹杂着标点和语气词。除了“萤火虫”以外,没有任何实词。
虽然这份文本看似杂乱无章、毫无意义,但对于同时掌握50门语言,拥有语言学、人类学和情报学三重背景的我来说,还是能够一眼就看出其中的蹊跷。
首先,从人类学家的研究方向来看,这份笔记很可能记录了当地的宗教仪式或者日常生活。笔记中反复出现的三角关系结构(她她-它/他她-它/他他-它),很可能是当地的某种“人-灵”沟通仪式。这在某些部族的宗教当中也很常见。
这样来看的话,“它”或许指代的是神灵/祖灵,而“她/他”代表不同性别的参与者?
不过还是有很多疑点,例如那个突然出现的“萤火虫”,那或许是仪式中的核心象征物?还是某位神灵的代称?那些感叹词和标点(呜啊啊啊、~、——、?)也很奇怪,难道是用来还原说话人语气的记号吗?
光凭现在的线索还无法推断出什么有效结论,但这并不妨碍我有十足的把握完成这个委托。我在草稿箱里敲下回信,表示我愿意接下这个委托,并希望他能给我提供更多信息,包括父亲考察的地点,未公开的论文等等。回复完邮件后,我开始在私人数据库中搜寻相关资料,尝试对文本内容进行解读。
没过多久,客户就发来了回信,内容如下:
真的非常感谢您!要是没有您的帮助,我现在可能就孤立无援了。关于考察的地点,父亲一直非常谨慎,没有告诉任何人。连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方面恕我无能为力。但关于解读笔记的资料,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已经把文件放进邮件里了,您只要点开邮件就能看到。再次感谢您愿意接手我的委托,事成之后,我一定会给您好评的。
我点开附件的文档,里面是一篇典型的人类学论文,格式工整,术语精确。但结论与结论之间的论述过于跳跃,与其说是学术论文,倒不如说是思维笔记。
那篇文章描述了一个特殊的族群:他们可以通过音调刺激出大脑中的画面,直接通过脑海中的画面进行“神交”。正因如此,他们的文字非常简单,只有代词。他们仅凭说话人音调或语气细微的变化,就能明白话语所指。
原来如此,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代词和语气符号吗……这样一来,原本的“仪式密码论”就不攻自破了,因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交流的。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当地人不需要实词就能交流,那为什么会出现“萤火虫”这个词呢?
我坐在屏幕前思考,始终得不到有效的结论。我一遍一遍地阅读文件,逐渐感觉头脑发热,昏沉沉的,仿佛机器过载了一样。这时,我看到了一句重要的话——“笔记里的内容是村民之间的日常对话,部分是我和村长的谈话”。
有没有可能,“萤火虫”是一个外来词汇呢?那不是当地人使用的词汇,而是客户的父亲带过去的词汇。这样的话,“萤火虫”就不再是解读的重点了,我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音调和语气的分析上……
我的思路瞬间打开了。我感觉自己把握到了真相,于是开始运用数据库中的资料破解文本。不到10分钟,我就完成了第一份解读报告。报告的内容很长,这里就只展示第一部分吧:
【她她——它】
整体场景推断: 两位女性村民通过极简音调高效共享并确认了关于某个共同任务、眼前物品或即时状态的视觉信息。
她:嗯!它它。 => 【女村民A用肯定短音触发核心画面】 (A用短促、确认的音调“嗯!”,接着发出特定音调的“它它”,瞬间与村民B共享了关于当前话题/物品/任务的清晰核心画面。可能伴随点头或手势指向)
她:嗯~你它它? => 【女村民A用婉转音调向B确认理解】 (A用拖长的、带有询问意味的“嗯~”,接着用特定音调的“你它它”,试图在B脑海中激发:“你是否看到了我指的那个画面/是否理解?”的画面流。可能带有期待表情)
她:嗯~它它。 => 【女村民B用相同音调回应确认】 (B用同样的拖长音“嗯~”和完全一致的“它它”音调回应,表明完全相同的画面已在脑中生成并理解。达成无声的默契)
…………
报告完成后,我的情绪十分激动,就像郭沫若刚写完《女神》那样,出了一身汗,敲字的手都在发抖。我自认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将报告交付客户。
我从办公桌上起来,冲了杯咖啡,眺望窗外的景色:电子屏幕播放着日落的虚拟影像,没想到已经到这个时间了吗……我差不多也可以下线了吧。
电脑的提示音响了,我重新坐到屏幕前检查邮件。
我要的不是这个!你有没有听我……
后面的内容我已经不用看了。不知道为什么,客户突然发火了,语气完全变得像是另一个人。这对我的工作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毕竟我需要的是精确的需求描述,而不是这种富有感情却毫无内容的废话。
不过也并未完全没有收获。至少可以判断,我之前的视觉音调语言假说并没有偏离方向。客户强调父亲论文明确指出代词有具体指代物,要求补全完整句子。
他需要的是一份已经翻译好的文档,而不是零零散散的研究报告。那为什么一开始不说清楚呢?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这种后期临时增加的需求也是常见的,我应该早就习惯了才是。但我还是为自己被浪费掉的时间精力感到不爽。
看来今天又要加班了。
我调用语料库中的数据,开始搭建出可能的对话场景和内容。说实话,这种翻译并不准确。我刚才给出的那份报告才是最正确的,因为仅凭少量的文本根本无法知道“所指”是什么。但无所谓了,既然客户需要,那就随便做一份给他看看吧。
十分钟后,我完成了第二份报告。报告内容如下:
【场景1:两位村民(女)关于某工具[它]的检查】
她A:嗯![火塘]好。 (检查火塘状态良好)
她B:嗯~你修[火塘]了? (询问对方是否修理过)
她A:嗯~修[火塘]了。 (确认已修理)
【场景2:村民(女)与村民(男)关于某动物[它]的紧急对话】
村民女:你啊看[野猪]我陷阱! (提醒父亲看陷阱里的野猪)
村民男:哈抓住了!哈抓住了! (父亲兴奋回应)
村民女:呜啊啊啊啊![野猪]![野猪]! (突然发现野猪挣脱或异常,惊呼)
(记录者注:啊[野猪]状态,状态关乎[野猪]。) (记录现场混乱)
村民女:你管[野猪]!???[陷阱]—[野猪]坏? (质问村民男为何没管住,怀疑陷阱损坏)
村民男:[野猪]状态—~,——~[它]我责任。 (父亲描述野猪状态,承认责任)
(记录者注:村民父亲[野猪],——[状态],[野猪]/。) (对话结束,问题未决)
【场景3:您父亲与村长关于某物品[它]的商议】
父亲:你你补[陶罐]——?能补? (询问村长能否修补陶罐)
村长:[陶罐]——。我我补[陶罐]行。 (村长停顿后表示自己能补)
父亲:我补—~你你看[陶罐],那个—[裂痕],我我补“关键点”好,好!补好了。 (父亲描述修补过程,强调关键点)
村长:[陶罐]—这。你你补[陶罐]好—。[陶罐]—完美。补~——~你你手艺好—,我补————~[陶罐]你你修吧。 (村长称赞修补结果,婉转推辞后续修补)
父亲:哈哈,[陶罐]—补好—~,我我满意了。 (父亲大笑表示满意)
【场景4:您父亲与村长关于“萤火虫”的指认(核心突破)】
村长:那[光点]它—。 (村长注意到远处光点)
父亲:[光点]? (父亲询问)
村长:那那啊!你叫[光点]——~? (村长追问父亲如何称呼光点)
父亲:哦,那——~“萤火虫”?? (父亲迟疑地用汉语词回答)
村长:“萤火虫”——? (村长用疑问语气重复该词)
父亲:那[萤火虫]。 (父亲确认指代)
(记录者注:村长父亲[萤火虫]。) (双方达成共识)
村长:那那,——~“萤火虫”。 (村长用拖长音正式接受该词指代)
这样客户应该就满意了吧。我再次点击发送邮件。这次的回信很快:
谢谢您的回答,我感觉您说的完全正确。我现在就去联系出版社,让他们发表这些内容。感谢您的帮助。
系统弹出了一个窗口,显示我收到了客户的五星好评。
嗯,临时的加班也算是有价值吧。我关闭电脑,以及办公室的电源,然后下线。
——————
后记:在本书出版前,基罗斯先生曾经拜托箱南大学的“类人体侦探模型”对文本进行解读。从结果来看,解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错误的。但它的部分推理和预测,却又意外地与实际内容相契合。因此编者在这里将该类人体的思维过程附在书后,以供参考。文本的精确解读,请以下面的版本为准:
【老妇人之间的谈话】
妇人A:今天吃饭了吗?
妇人B:还没有,你晚上打算吃什么?
妇人A:不知道,等会再说吧。
【小朋友之间的对话】
小女孩:你不要抢我的玩具!
小男孩:就要抢就要抢!
小女孩:呜啊啊啊啊啊!妈妈!妈妈!
此时一个女性走过来,看起来像是小女孩的母亲。
女性:你干什么呢?啊?就不能让着点妹妹?
小男孩:是她先弄的,不关我事。
女性打了他一巴掌,随后把玩具抢过来,带着小女孩离开了。
【我和村长的对话】
我:你们的语言为什么如此特别?
村长:我不知道。我们生来就是这样。
村长:我反而无法理解你们那种思维方式,对什么东西都要起一个名字,我们只需要一个词就能解决了,一说大家就都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我:确实如此。你们的思维构造太奇妙了,只需要一点音调的提示就能显现出完整的画面。如果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我恐怕也无法理解你们说的话。
村长:哈哈,时候不早了,我们去吃晚饭吧。
【我和村长的对话】(刚进村子的前几个月)
村长:那个东西就在里面。
我:那个是什么?
村长:那个就是那个啊?你看不见吗?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我:哦,那不是萤火虫吗?
村长:萤火虫是什么?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东西。
村长摇了摇头。
村长:那个就是那个,不是什么“萤火虫”。
*本文部分内容由AI辅助完成。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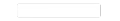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