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在你的印象中,店主,是一种什么形象的人?是像《Moonlighter》中和冒险者一起勤勉开发地牢的亲和小哥?是像《生化危机4》里两边通吃大发战争财的大卫?是像《荒野之息》里表面人畜无害,暗地里为了黄金独角仙盘算着你命数的甲虫商人?还是京极夏彦笔下刻薄冷峻的中禅寺秋彦?
在用符号化构建明确功能的游戏中,商人们的个性被予以放大和强化,以增加游戏中的色彩。但真实生活中二手书店的老板们,他们拥有着以上的全部特质。就好像上帝将所有商人的品质揉成一个面团之后,不小心打翻了对二手书的执念到面盆里。然后一气之下把这团面摔在地球上,散落到世界各处。
以小见大,围绕着二手书的群像
以小见大,围绕着二手书的群像
对于二手书店主们的故事,我曾经读过一本有趣的书。《Second-Hand Books, First-Hand View》,二手的图书,一手的看法。这本书国内有翻译,《二手书那些事儿》。在这本书中,戴维森作为二手书店老板,从各个方面用各种方法揶揄了二手书和看二手书的人的方方面面。他在记录自己一次乡下访问,结果发现自己觊觎已久的老人家后代把藏书都廉价卖给另一个当地奸商时,在书中大骂:“那原本是属于我的宝藏!应当由我来搜刮!” 将二手书店老板们生动地描述成了一丘之貉。而对于二手书读者对这些珍宝的狂热,他又用短篇小说的方式来将这种不可理喻用故事的形式予以掩饰。但任何曾经浸淫在二手书之中的读者们,看到这篇小故事的时候肯定是嘴角一咧,“这说的不就是我嘛!”
书中对店主和爱好者的关系也有不少描写。下面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每一天,这个人都会进门,看一看书架上的一本书,细细品味它的装帧,烫金的书名,摸索、嗅闻其中特有的味道。满足于它存在于这个世界, 这个书店,这个书架,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接着赶路。店主们就会过上几天,把这本书换一个地方。这个人就会开始疯狂地搜寻,在这个书架上,旁边的书架上。失去它的恐惧贯注全身,然后冲到柜台,“我的那本书呢?!” “什么书?先生?” “少装蒜!就是那个架子上左起第三行第二本!” 然后报出书的全名,作者,出版年份。 “哦,刚才收拾书架的时候挪到别处了。” 然后不紧不慢地从身后的柜台抽出来。对方则会在全身警戒放松之后,火速买下这本书。
关于二手书,戴维森并不是唯一的作者。而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和英国这个国家产生一些联系。为什么是英国?好吧,接下来是《读者》环节。你们适当跳过吧。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英国有非常好的阅读习惯。这和英国早期在媒体爆发之前就开始阔起来有关。印刷术在欧洲开始发展之后,书籍的相关工业开始兴起,并成为了有钱有闲阶级的消遣媒体。和今天大家玩儿游戏其实是差不多的。而在新教和清教徒开始成为书籍工业主流时,书籍在英国也分为三六九等。圣经和圣经相关的书籍那才是上品,很多知名人士的随笔和通信也在上流中视为必读。比如我之前在机组中提到过的大法官约翰·塞尔登的《Table talk》,桌上对谈,因为他曾经是女王大人的顾问之一。同样可以列入当时3A大作的是诗歌,这是当时文化圈子里的婆罗门存在了。围绕诗歌以及诗人的轶事,就和现在我们谈游戏设计的精妙和小岛秀夫都受过那些东西的启发一样流行。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而在那个体系下,和诗歌有些沾边的小说类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下九流。在《埃科灵顿牧师馆》里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情节,庄园主的小女儿问到访的牧师他喜欢什么小说,后者立刻手画十字,哦!不!我不读小说!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书籍作为消遣,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形式。
上等的老爷们读上品的书,装帧工艺自然是上上之选。漫步在牛津街头,古董店和古书店比比皆是。而在牛津这么一个教会一手拉扯大的大学联盟,旧书店里几乎全都是圣经相关著作。而在他们的书目中,我们也能一窥宗教思想的变迁。天主教指定的圣经读本,厚厚一大本,大多由金属和皮革装订。很多书上的烫金部分都已经变色,皮革也已经老旧,仍然等着不知道什么会对他感兴趣的人来。
这里贴一个St. Philips Books. 圣菲利普书店。图片是我从谷歌上找的,大家可以看出当年书籍装帧的模样。(部分配图有说明文字)
1 / 4
如果您对牛津的历史有所了解,那么您应该知道Towns and Gowns。前者是当地镇民,后者是穿着长袍的学生。这个词组有个典故,当时自视甚高的学生们和看不上虚不拉几学生的镇民们一直不对付。直到有天一个学生不满当地酒吧老板的酒而把酒桶倒扣在店主头上,爆发了连续数日的暴力对抗。
英国,东滨
英国,东滨
那和这些象牙塔里穿着长袍的大学僧们相比,这些“民风淳朴”的世俗居民们又是什么样貌呢?如果他们也读书,那么他们的书店又会是什么样呢?
这家书店位于英国东滨(Eastbourne)市。这里是英国日照时数最长的地方,最出名的地标是它滨海路上的的花圃。我曾经在这个城市住过半年,是这家书店的常客。看过照片您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混沌!无序!和之前牛津的店比起来,这间店简直就是地狱。还记得那家店书架上的绿色书架吗?随时等着新书在上面摆放?这里完全不存在那种情况。没能在书架上找到一席之地的书只能在人们通行的空间里被堆起来。而支撑着他们的,是那些直接被放在地板上的书籍。在这家书店,你的视力得好。不然隔着那些放在过道的书籍,根本看不清书架上都有啥。跟这家店相比,《血源诅咒》里那种到处摞起来的书已经算是整齐的了。
上上下下的楼梯也有一半被书籍填满。而这种在很多咖啡兼营书店的小资空间里作为小巧思的设计,在这里完全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不论你身处这个书店的任何角落,周围排山倒海的书似乎随时都会向你压将过来,急着要把自己书页里的内容挤进你的脑海。碰到那种在楼梯上一屁股坐下开始看书的客人,就算站起来也过不去,只能一起走到上层或下层的深处,把自己焊在墙上接着看。我有次就跟店主说,你这个店感觉就不是给活人准备的,想在你店里挑书得是魂儿,飘着才行。
以及如果您看一下图二,这家店里也不乏有装帧非常考究的书。但他们得到的最好的待遇,也就只不过是在书架上有一席之地罢了。店主斯图亚特对这些书的护理令人发指。先不说在一个海滨城市,石墨地板对那些压在底层的书有什么影响。书店里随处可见靠在斑驳墙体的书,摆在外面风吹日晒的书,放在地下堆肥温度一样的书,疑似杰瑞居所附近的书。甚至连门框上面的空间都被用来放书。不论是对书还是对顾客,都是不小的安全隐患。
我小时候家附近的治安不太好。主要是天灾和交通,所以相对来讲,家里更倾向于让我在家看书。以及因为当时在图书馆也受到一些馆员的影响,我对书的态度都是毕恭毕敬的。因此第一次来这个书店,我的感觉就是震惊。当时店主从楼下的楼梯探出头来看见我,说他来了批货要安排,让我自己溜,然后就缩回地下。我原本打算帮忙把一楼收拾一下,下楼打招呼的时候我就震惊了。当时的盛况比照片还夸张,完全没有落脚的地方。斯图亚特似乎是从堆在楼梯口的书上面爬进里面开始核对书目的。我就大概明白,这家店平常就是如此。
一回生,二回熟,后来和老哥也偶尔聊聊天。但那时候我高中刚毕业,见识尚浅,很多后来想问他的事情还没有在我的心中萌发。只能听老哥谈那些收书时候的故事和一些其他有的没的。我很想和他学学如何给他手中的书定价,老哥随手拿了一本给我演示了一下:
他拿起书,双手摩挲着封面,然后是纸张。他看了几眼书页的边缘,边看便跟我说,金箔页边保留完好,裁纸痕迹整齐,纸质是拿什么什么我听不懂的专有名词做的。然后打开扉页,看了看罗马数字的年份和出版商,如数家珍地跟我说了几个厂家的特色。然后看了看里面的作者肖像,还有完好的磨砂纸保护着这幅画像。书签带断了,但断开后剩下的部分仍然在书页里面夹着。这本书是查尔斯·兰姆的《伊利亚随笔》,这一本是随笔和后续的合订本,所以虽然是第一次印刷,也上不了首版的价格。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吐了吐舌头,“我编不下去了。” 之前念念有词有的没的,除了知道伊利亚随笔分原版和后续,其他的都只不过是品相描述而已。除了一些品相完好,或者文学界比较有戏的珍本,他都任由自己从业几十年的经验和本能接手。旧书的采购和销售成了一种近乎于赌博的行为。不单单是他的这家书店,恐怕放眼全球都是一样的。总有那么几本书,它的价值没有被买的一方或者卖的一方所认知,从而让另一方占了便宜。而从这个角度出发,像我这种二手书店爱好者也是一种赌徒,成天妄想着能发现比我们还要上道儿的老板们会看走眼,从而让我们这些喽啰们低价买到绝世珍品。
如果您刚才仔细放大了图片想去看看店里都有什么类型,那我可以说他们家专注的范围相当广。用老板自己的话说,不爱书开不了这个店,不了解书做不了买卖。很难想象,眼前这个聊起军武、历史、宗教来头头是道,嗓门洪亮的机核备选老登系嘉宾对音乐也能有同样的造诣。在上面那些照片中都没有包含的内容里,店里有着海量的乐谱!可能是店里除了珍本以外唯一会被透明包装保护起来的商品,非常多的乐谱被挂在墙上,过道里,和楼梯间。这就是我完全不懂的领域了。同样是乐谱,为什么我面前的那份被定价120镑,它和一份现代打印的版本有什么差别。而且从我的观察看,也没注意到有什么记号或者题词。
这就和老哥本人没关系了。我有一次和他聊天,聊到这家店的名字。Camilla,卡米拉。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没回答我,反而跟我说了个小故事。曾有一个中亚来的客人,逛了逛和他聊了聊然后告诉他,Camilla在他们那儿的发音是“卡玛利亚”,“骆驼”的意思。然后开始哈哈大笑。
Camilla 是这家书店的合伙人,是这家店另一面品味的代表。
斯图尔特和卡米拉这二位就是对书籍的热爱达到痴迷程度的人。他们热爱书籍的方式是把那些有趣的书籍用这家书店重新进入人们的书架,书包,帆布袋和牛仔裤屁股后面的口袋。他们的书全都在店里堆成“纸房子”,从我的理解,就是不想让这些已经离开人手的书再在仓库中度过不能被人赏识的时间。
每当一个客人进到他们的店,目瞪口呆之余蹲在地上努力想要看清这摞在“诗歌”分类下垫底的那几本书是不是符合自己口味。当他们坐在店里唯数不多的空间,甚至就靠在另一摞书上翻看手中并不算太久远的旧书的时候。这些书就已经继续把其中的内容贯注给新来者了,即便只有只言片语。
如果说牛津的二手书店再怎么收藏仍然带着学院气息,仍然秉承着阅读应当有一种仪式感的传统。那么卡米拉书店就完全是另一个态度:书就是用来读的!我买走了那本查尔斯·兰姆,并把它放在了我牛仔裤屁股后面的口袋里。这本小书后来陪着我坐火车、坐地铁,去到了它之前的主人永远不会带它去的角落,并在那里让我享受文字的乐趣。
内蒙古,呼和浩特
内蒙古,呼和浩特
卡米拉书店的楼梯,我爬着是有一种亲切感的。类似的楼梯我爬过几次,那是在呼和浩特。如果你生活在呼和浩特,特别是在2、30年前,“文化商城”是你绝对不会错过的地方。一个拉长的“回”字型建筑群,内部包含了学业、艺术、文娱、计算机的几乎所有产品和内容,就是一座文化的堡垒。这座文化堡垒的外面,到了夏夜,是似乎要蔓延到天边的营地。那里售卖的都是盗版书集散地产出的高质量盗版书,价格可以让手中的雪糕变成奢侈品。
堡垒内部有几家书店,其中有两家是旧书店。也不排除是同一家店,但我记忆混淆了。那个时候我年龄更小,去那家书店主要是看铺在地上卖的连环画。《三国演义》、《随唐英雄传》、《封神榜》
重新对这些古旧书感兴趣是在中学阶段。家父进京出差,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本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这是一本给青少年看的哲学入门书,效果非常明显,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哲学类书籍非常着迷。但是呼和浩特是个三、四线城市,书店除了主流图书和工具书之外选择很少,而我就是在这家旧书店发现了很多关于哲学的古旧书籍的。
除了满足了我对哲学类书籍的需求,这家店还差点让我误入歧途。哲学这个柜子除了西方哲学,还有社会学和宗教学。然后宗教学里面有弗雷泽的《金枝》,有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有费孝通的《云南三村》。那个时候还没有三联的文献图书计划,没有小橙本和小绿本,这些书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见过其他版本。
西方的东西都这么多了,怎么可能没有我们本土的内容呢。这里就是我严重怀疑我自己记忆的部分了。看一下下图,这是在咱们国家中央网站上关于书店的内容,但是我印象里不太记得老板的长相,以及我记得那家书店要更加逼仄一点。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对萨满非常感兴趣,在我的印象里,当时这家书店里有很多关于藏传佛教和萨满的书。甚至有一段时间会两头跑,这家店看一会儿再跑去一家蒙文书店。我的水平看不懂神歌,另一家店的店主就给我拿念经的调儿给我念。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是一个主攻藏传佛教,个人兴趣是萨满的哥们儿。有一年假期我们碰巧都在呼和浩特,我就兴冲冲拉着他去文化商城,结果里面已经没有相关的书籍了。老板跟我说再早个几年还有不少,后来因为这个学科不怎么流行等原因就不再收集了。非常的可惜。
但那一次我也不是全无收获。如果说古旧书店还有什么多,很大概率跑步掉的一个品类就是地方志。内蒙古东西跨幅非常大,而且历史上中、日、苏、蒙轶事颇多。地方历史的范围也颇为广泛,工艺上从线装毛笔到蓝皮打印的小册子,地域上从现甘肃部分地区到小兴安岭,内容上从普遍意义上的地方志,到人物志,人物传记,回忆录,应有尽有。我曾经一度动过在这里面挖上一段时间开始写小说的念头。
那一天的收获则是翻看一本回忆录。拿起那本书绝非随意而为,而是因为那本书的作者是家父从军时的上司。我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了几张照片。很显然,上一位读这本书的人用这些照片做书签,然后就没再继续读下去了。而他的后人们将他的书做了变卖,辗转到了这里。
这回是真的让我这种人捡到宝了。我付了钱买了书,带回了那些照片给我父亲看。他盯着那些照片看了好久。似乎是想记起什么,但最后只说,下次去扫墓的时候给上司的后人带去。
也许二手书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吧。他把一个人、一片土地、一段时间,变成一段记忆,凝结成一片片书页。钉在一起,作为一种纪念。它承载着这些记忆,从一个人的生活流入到另一个人的生活,从而一直延续下去。
澳大利亚,悉尼
澳大利亚,悉尼
延续也有多种方式。就像非洲大草原上的生生不息,有些记忆的延续就要以终结开始。
悉尼的生活节奏很怪,店铺门都在5店关门,甚至餐馆也少有延长营业时间的。但我某一天下班之后就来到了悉尼的一个二手书店。灯还亮着,门还开着,老板娘还在柜台站着。于是我斗胆走了进去。
这家店不大,整齐利落。除了书架里的书,周围只有一些盆栽和装饰品。看得出来这家店的老板娘是那种把书店纳入自己生活的类型。店里的书主要是小说和科幻,情感类小说和非虚构历史事件相关书籍为主。每一个分类书架的旁边都有一张椅子,与我之前所去过的任何古旧书店都不同。
就在我坐在一张椅子中琢磨着看怎么跟老板娘聊聊的同时,一个一身皮革,头顶鸭舌帽的家伙进来了。丝毫没有为书店里的任何东西作为铺垫,直接和老板娘攀谈起来。这是个二手书店?怎么想起来做二手书店的?做了多久了?生意如何?如此种种。而老板娘一一回复之后,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今天就是书店的最后一个营业日,明天就会有另一家店的人过来把书全部拉走。
话题从这个问题开始继续。书会何去何从,您有打算退休之后做什么?这个鸭舌帽皮革小哥甚至端起自己胸口的照相机开始给老板娘和她的朋友开始合影。感叹于外向的家伙们多么可怕之余,我也发出了和戴维森类似的咒骂:这原本应该是由我挖掘出来的故事!
拜这位开朗小哥的语气所赐,他们的对话我也听的一清二楚。这家店原本是个普通的书店,老板娘原本也是着重情感类小说,曾经有很多女性读者。店里的布置也是因为她们来店里的频次逐渐增加而进行的调整。老板娘自己当年还出过两本书,就是这个类型文学的圈里人。书店里曾经不但有读书会,还有创作交流会,在当时的悉尼还算是个小小的文化沙龙嘞。但渐渐地,各种因素组合在一起,读书的比例逐渐下降,甚至曾经一起创作的人也开始从写小说转型到给网飞写剧集。
老板娘对新时代的情感类文学有点不感冒,进书的时候经常是捏着鼻子上货。于是后来干脆改换赛道,就卖自己喜欢的。可那些书已经不印制了怎么办?那就全部变成二手书!从此在悉尼,一个不走二手书商奸猾之道的老板娘出现了。
闭店的决定也很简单,没有人读书了,更别提读这些过去的书了。对于她来讲,这家店逐渐减少的客流所表明的并不是生意的消退,而是她自己所喜爱的文本式微的写照。而她对此又无能为力,索性眼不见心不烦,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英国,伦敦
英国,伦敦
传承不下去,并不光是南半球的问题。回到二手书文化盛行的伦敦,古旧书同样面临传不下去的困境。小五曾经在“核市奇谭”里谈到过一本书,《查令街84号》。这是一本美国作者海莲·翰芙与英国古旧书店店员约翰·诺尔的书信集。两者的通信从直白的邮购二手书到谈及对书籍和人生所感所想,到最后双方和朋友们都结下深厚友谊。这是所有爱书人士都应该看看的情书。因而很自然地,我也去了查令街84号,前去圣地巡礼。
然而当我顺着谷歌地图找到地方的时候,巡礼变成了吊唁。查令街84号现在是一家麦当劳。
书籍行业本身就收到了多重冲击。 阅读人群的减少,阅读习惯的变迁,阅读作为一种行为起仪式感的崩溃,阅读审美的下降,同行模式的竞争,以及书籍本身质量的下滑,都导致了书籍本身式微。我们也不可否认,在媒体的日新月异更新换代之后,书籍客观上已经是一种落后的媒体了。而作为要对阅读本身有相当程度的爱好,古旧书今后电子化,可能才是延续下去的最终可能性。
我现在每次访问一家二手书店,都带着一种且行且珍惜的心情。 她是当地风土和历史实体化之后的记忆碎片。又是这些热爱书籍店主们的心血。每当店主们卖一本这样的书给我,我都会想起《黑暗之魂》中大沼咒术师的那句话:当我分给你这一份火焰,我同时是将我自己的一部分灵魂分给你,请照顾好它。
完
完
东滨的卡米拉书店有网站: Camilla's Books ANTIQUARIAN & SECONDHAND BOOKSELLERS
文化商城的旧书店上过中央政府的网站:旧书店里演绎墨香人生
欢迎看看我之前在机组发的关于书籍的帖子:伯纳德小姐的书斋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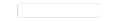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