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本系列旨在翻译Titus Burckhardt所著的Introduction to sufi doctrine。本系列为三大论集。
知识与爱
知识与爱
苏菲主义的特点是,它的表达经常在爱和知识之间保持平衡。一种情绪化的压迫形式更容易整合宗教态度,而宗教态度是所有伊斯兰精神性的起点。爱的语言使得在不与教条神学冲突的情况下,能够阐明最深奥的真理。最后,爱的陶醉象征性地对应于超越话语思维的知识状态。
还有一些表达方式,虽然它们不是出于爱的态度,但无论如何都会唤起爱,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内在美,这是单一位在灵魂上的印记。正是从这种统一中,清晰和节奏诞生了,而言语的任何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和虚荣都与简单相矛盾,因此也与灵魂与真理的透明性相矛盾。
一些苏菲派作家,如穆哈伊丁·伊本·阿拉比、艾哈迈德·伊本·阿里夫、阿勒颇的苏赫拉瓦迪、朱奈德和阿布·哈桑·阿什·沙迪利,都证明了一种从根本上讲是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些作家将神圣现实视为所有知识的普遍本质。其他人,如奥马尔·伊本·法里德 (ʿOmar ibn al-Fārid)、曼苏尔·哈拉吉 (Manṣūr al-Ḥallāj) 和贾拉尔·阿丁·鲁米 (Jalāl ad-Dīn Rūmī),都以爱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他们来说,神圣的现实首先是无限的欲望对象。但是这种态度的多样性与不同学派之间的任何分歧无关,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他们认为使用知识语言的苏菲派受到了伊斯兰教以外的教义(如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只有那些代表情感态度的人才是真正的神秘主义的代言人,而这种神秘主义源于一神论的观点。
事实上,所讨论的多样性源于职业的多样性:不同的职业很自然地将自己嫁接到不同类型的人类天才身上,并且都在真正的 taṣawwuf 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智力和情感态度之间的差异只是该领域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差异。
印度教的特点是精神方法的极端差异,明确区分了知识 (jñāna)、爱 (bhakti) 和行动 (karma) 三种方式。事实上,这种区别可以在每一个完整的传统中找到。在苏菲主义中,三种方式的区别对应于向真主渴望的三个主要动机——知识或灵知 (al maʿrifah)、爱 (al-maḥabbah) 和恐惧 (al-khawf)。但苏菲主义更倾向于综合而不是区分这些方式,事实上,在“古典”苏菲主义中,知识和情感态度的某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伊斯兰教的一般结构,它建立在at-tawḥīd(合一的教义)之上,因此给出了一种强加于各种精神生活的知识方向。至于爱,爱是自发地诞生的,无论在哪里感受到或沉思神圣的现实。
这让我们回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只有那些追求爱的态度的苏菲行者才真正代表了伊斯兰教的神秘面。支持这种观点的标准被错误地应用了,这些标准只对基督教有效,基督教的基本主题是神圣的爱,因此那些在基督教中是灵知的代言人通过爱的象征来表达自己——尽管有一些罕见的例外。
在伊斯兰教中,情况并非如此,在各个层面上,知识都毫无疑问地占据了优先地位。【1】此外,真正的知识或灵知绝不意味着以牺牲情感能力为代价来强调心灵:它的器官是心,是人类存在的秘密和无法把握的中心,而知识的辐射则渗透到灵魂的整个领域。一个已经完全实现了“不可预测的”知识的苏菲,可能同样会利用爱的语言,拒绝所有教条辩证法;在这种情况下,爱的陶醉将对应于超越形式并超越所有思想的知识状态。
【1.顺便说一句,如果穆希伊丁·伊本·阿拉比(Muḥyi-d-Dīn ibn ʿArabī)赋予了ʿilm这个词比maʿrifah更普遍的含义,那是因为在伊斯兰神学中,前者与神圣的属性相对应。Al maʿrifah 是神圣知识的偶然参与,可以翻译为“gnosis”,从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 (Clement of Alexandria) 使用的意义上说。】
实际上,知识之道和爱之道之间的区别相当于一个或另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事实上,这两种精神性模式之间从来没有完全分离。对神的认识总是产生爱,而爱则以对爱的对象的认识为前提,即使这种知识可能只是间接的和反映的。精神之爱的对象是神圣之美,这是无限的一个方面,通过这个对象,欲望变得清晰或清晰。完全的、完整的爱,围绕着一个不可言喻的点旋转,给人一种主观的无误。
我们的意思是,它的无误性不适用于普遍的和“客观的”真理,来自知识边缘的无误性也不适用于这种,而只适用于构成崇拜者与他的主的“个人”关系的一部分的一切。正是在美这个对象中,爱几乎与知识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理和美是彼此的标准,尽管感性的偏见扭曲了美的概念,就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理性主义限制了真理一样。
非常重要的是,几乎没有一个穆斯林形而上学者不写诗,他最抽象的散文在一些段落中没有不被转化为充满诗意意象的有节奏的语言,而另一方面,最著名的爱情赞美诗人的诗歌,如奥马尔·伊本·法里德 (ʿUmar ibn al-Fārid) 和贾拉尔·阿丁·鲁米 (Jalāl ad-Dīn Rūmī), 具有丰富的知识感知。
至于恐惧的态度(al-khawf),它与行动方式相对应,这并不直接表现在表达的方式上;它的作用是隐含的。诚然,恐惧只是站在沉思的门槛上,但是,当它被精神化时,它仍然能把人从“世界”这个集体的梦想中带出来,使他面对永恒的现实。爱高于恐惧,就像知识高于爱一样,但只有直接的、直接的知识超越了理性(或话语性思维)才是正确的,因为精神性的爱拥抱了每一个个体的能力,并给每一个能力都打上了合一的印记。【2】
【2.关于知识和爱的问题,以及回应这些问题的方式之间的区别,参见Frithjof Schuon, Spiritual Perspectives and Human Facts (Lon don: Perennial Books, 1970)】
在他的 Maḥāsin al-Majālis Aḥmad ibn al-ʿArīf 中说,爱 (al maḥabbah) 是“湮灭山谷 (fanāʾ) 的开始,也是从这里下降到自我创造(al-maḥū) 阶段的山丘;这是信徒群众的先遣队与选民的后卫相遇的最后一个阶段”。另一方面,穆罕默德丁·伊本·阿拉比认为爱是灵魂的最高位置,并服从于它的一切可能的人类完美
这似乎很奇怪,因为它来自知识之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解释是,对伊本·阿拉比来说,知识不是灵魂的驿站。在知识的完善中,没有什么是特别的,因为这种知识是与它的对象,即神圣的现实相联系的。因此,就其直接现实而言,知识不再可以归于人或灵魂,而只能归于神,因为它不再有任何精神轮廓。同时,灵魂最崇高的地位不是审慎或真实等知识的心理关联,而是整体的爱,即人类意志被神圣的吸引力完全吸收。这是 “迷失在爱中” 的状态,亚伯拉罕是人类的原型。(参见伊本·阿拉比:Fuṣūṣ al Ḥikam)。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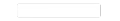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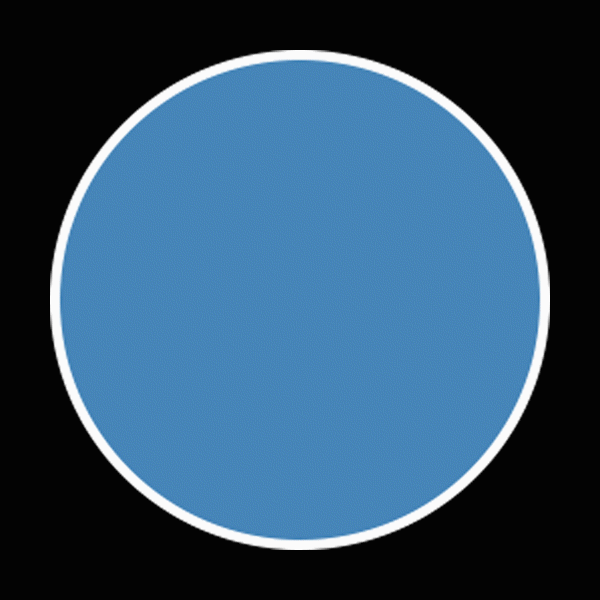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