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本系列旨在翻译Titus Burckhardt所著的Introduction to sufi doctrine。本系列为三大论集。
苏菲与神秘主义
苏菲与神秘主义
科学著作通常将苏菲主义定义为“穆斯林神秘主义”,我们也会欣然采用“神秘主义”这个绰号来指代将苏菲主义与伊斯兰教的简单宗教方面区分开来的东西,如果这个词仍然具有早期基督教的希腊教父和那些追随他们精神路线的人所赋予的含义:他们用它来指代与“奥秘”知识有关的东西。不幸的是,“神秘主义”这个词——以及“神秘”这个词——被滥用和扩展为涵盖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强烈地带有个人主义的潜质色彩,并受到一种不超越外部主义视野的心态的支配。
诚然,在东方和西方一样,存在着诸如 majdhūb 这样的边缘情况,其中神圣的吸引力 (al-jadhb) 强烈占主导地位,以至于 majdhūb 无法为他的冥想状态提供教义形式。也可能在特殊情况下,精神实现的状态几乎不需要常规方法的支持,因为 “圣神吹到它所到之处”。尽管如此,Taṣawwuf 一词在伊斯兰世界仅适用于常规的冥想方式,其中包括深奥的教义和从一个大师到另一个大师的传承。因此,Taṣawwuf 只能被翻译为“神秘主义”,前提是后一个术语被明确赋予了其严格的含义,这也是它的原意。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这个词,那么将苏菲派与真正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进行比较显然是合理的。尽管如此,这里出现了一丝含义,虽然它没有触及“神秘主义”这个词本身的含义,但解释了为什么在所有上下文中都不能令人满意地将其转化为苏菲主义。基督教的沉思者,尤其是那些在中世纪之后出现的沉思者,确实与那些遵循精神之爱 (al-maḥabbah) 的穆斯林沉思者有关,他们是印度教的 bhakti mārga,但他们很少与那些纯粹属于知识分子的东方沉思者有关,例如伊本·阿拉比 (Ibn ʿArabī),或者,在印度教世界中, Śrī Śaṅkarāchārya.【1】
【1.在这个事实中,没有任何暗示一种传统优于另一种传统;它只显示出受有关人的天赋和气质所制约的倾向。由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这种 bhaktic 特征,一些东方学家发现可以断言伊本·阿拉比“不是一个真正的神秘主义者”。】
现在,精神性的爱在某种意义上介于炽热的奉献和知识之间;此外,Bhakta 主题的语言,甚至进入了最终结合的领域,即爱的源泉。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世界里,真正的神秘主义和个人主义的 “神秘主义 ”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被明确地标记出来的一个原因,而在伊斯兰教的世界里,神秘主义总是涉及对事物的形而上学的看法--即使是在它的bhaktic形式--因此与外部主义明显分开,在这种情况下,外在主义可以更容易地被定义为共同的 “法则”。【2】
【2.伊斯兰教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不承认外部主义和深奥主义之间的阶段,例如基督教修道院状态,其最初的作用是构成基督教沉思方式的直接框架。】
每一种完整的沉思方式,例如苏菲方式或基督教神秘主义(按该词的原意),都与一种虔诚的方式不同,例如被错误地称为“神秘”的方式,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积极的智性态度。这种态度绝不是从一种带有知识分子气息的个人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的:相反,它意味着一种向本质现实(al-ḥaqīqah)敞开心扉的倾向,它超越了话语思想,因此也是一种将自己置于超越所有个人主体性的可能性。
为了不对刚才所说的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明确指出,苏菲也实现了一种由宗教形式塑造的永恒崇拜的态度。像每个信徒一样,他必须祈祷,并且通常遵守启示的法则,因为他的个人人性在与神圣现实或真理的关系中永远是被动的,无论他与它的精神认同程度如何。“仆人(即个人)永远是仆人”(al-ʿabd yabqā-l-ʿabd),正如一位摩洛哥大师对作者所说的那样。因此,在这种关系中,神圣的临在将自己显现为恩赐。但是,苏菲的智慧,因为它直接与“神圣之光”相一致,就其精神现实和它自己的表达方式,从宗教和理性强加给个人的框架中抽离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苏菲的内在本质不是单纯的接受,而是纯粹的行动。
不言而喻,并不是每个遵循苏菲之道的沉思者都能领悟到一种超越形式的知识状态,因为显然这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意志。尽管如此,所看到的目的不仅决定了智性的视野,而且还发挥了精神手段的作用,这些手段就像是这个目的的预兆一样,允许沉思者在他自己的心理形式中占据一个积极的位置。
他没有将自己与他的经验性的“我”等同起来,而是凭借一个象征性和隐含性的非个体元素来塑造这个“我”。《古兰经》说:“我们将用真理打击虚空,它将化为乌有”(21:18)。苏菲阿卜杜勒·萨拉姆·伊本·马什什 (ʿAbd as-Salām ibn Mashīsh) 祈祷道:“与我同攻虚空,这样我就可以化为乌有。”在他被有效地解脱的程度上,沉思者不再是这样那样的人,而是“成为”他所冥想的真理和他所祈求的神圣之名。
苏菲主义的智性本质甚至在纯粹的人性方面留下了印记,这在实践中可能与宗教美德相吻合。在苏菲派的观点中,美德只不过是人类的形象或普遍真理的“主观痕迹”;【3】 因此,苏菲主义的精神与美德的“道德主义”概念之间存在不相容性,后者是定量的和二元论的。【4】
【3.人们会记得,对普罗提努斯来说,美德是介于灵魂和智性之间的中间地带。】
【4.美德的定量概念是宗教对功绩的考虑,甚至是纯粹的社会观点的结果。另一方面,定性概念考虑到了宇宙或神圣品质与人类美德之间的类比关系。必然,宗教对美德的理解仍然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只从个人救赎的角度来重视美德。】
既然教义既是道路的基础,也是作为其目标的沉思的果实,【5 】苏菲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之间的区别可以归结为教义三元论的问题。这可以清楚地表达为,如果信徒的教义观点仅限于外部主义的观点,那么他总是在神性和他自己之间保持着一种根本的、不可简化的分离,而苏菲派至少在原则上承认所有存在的本质统一性,或者——用消极的术语来说——所有看起来与神分离的事物的非现实性。
【5.一些东方学家想人为地将教义与“精神体验”分开。他们把教义看作是一种 “概念化”,期待着一个纯粹主观的 “经验”。他们忘记了两件事:第一,教义源于一种知识边缘的状态,这是道路的目标,第二,神不会说谎。】
有必要考虑到深奥的这一双重方面,因为一个外部论者——特别是一个宗教神秘论者——也会断言,在神眼中他什么都不是。然而,如果这种肯定对他来说带有所有的形而上学含义,那么他将被迫同时承认同一真理的积极方面,即他自己的现实的本质,凭借它他不是“虚无”,与神神秘地相同。正如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所写的那样:“灵魂中有一些东西不可创造,也是不可创造的;如果所有的灵魂都是这样的,那将不可创造、也是不可创造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智性。”这是所有深奥主义都先验地承认的真理,无论它以何种方式表达。
另一方面,纯粹的宗教教义要么不考虑它,要么甚至明确否认它,因为绝大多数信徒可能会将神圣的智性与人类的、“创造的”反映混淆,并且无法想象它们的超然统一性,除非在一种物质的相似性中,其准物质的连贯性将与每个存在的基本独特性相悖。诚然,智性在人类和宇宙秩序中都有“被创造”的一面,但“智性”【6】这个词可以被赋予的全部含义范围并不是我们在这里关心的,因为独立于这个问题,深奥主义的特点是它肯定了知识的本质
【6.东正教的基督教沉思教义,虽然显然是深奥的,但在“非受造之光”和理智或理智之间保持着显然不可简化的区别,理智或理智是人类的,因此被造的能力,被创造来认识那光。在这里,“本质的身份”是由“非受造之光”的内在性及其在心中的存在来表达的。从方法的角度来看,智性和光之间的区别是防止智性器官与神圣智性的“路西法式”混合的一种保障。世界内在的神圣智慧甚至可以被设想为“虚空”,因为“抓住”一切的智慧本身是不能被“抓住”的。这种观点的内在正统性——也是佛教的观点——体现在用这个“空”(śūnya)来识别一切事物的本质现实。】
外部主义站在形式智性的层面上,它受其对象的约束,这些对象是部分的和相互排斥的真理。至于深奥主义,它意识到智性是超越形式的,只有它在无限的空间中自由移动,并看到相对真理是如何被划定的【7】。
【7.《古兰经》说:“真主通过真理 (al-Ḥaqq) 创造了天地”(64:3)。】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必须澄清的进一步,此外,这一点与上面所得出的真正的神秘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神秘主义”之间的区别间接相关。那些站在“外面”的人经常把苏菲派的自命不凡归咎于能够仅凭自己的意愿到达上帝面前。事实上,恰恰是那些以行动和功绩为导向的人——即外在的——往往倾向于从意志努力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由此产生了他对纯粹的沉思观点的缺乏理解,而这种观点首先设想了与知识相关的道路。
在基本顺序中,意志实际上确实取决于知识,而不是相反,知识就其本质而言是“非个人的”。尽管它的发展从传统教义传递的象征意义开始,确实包括一定的逻辑过程,但知识仍然是一种神圣的礼物,人类无法主动地带给自己。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上面所说的那些精神性手段的本质,这些手段是严格的“入门”,就像它是道路的非人类目标的预示一样。虽然人类的每一次努力,每一次超越个体性限制的意志努力都注定要落在自身身上,但那些可以说与它们所唤起和预示的超个体真理(al-Ḥaqīqah)具有相同性质的手段,可以而且只有能够解开微观个体化的结——以自我为中心的幻觉,正如吠陀论者所说——因为只有真理在其普遍和超心智的现实中才能消融它的对立面,而不给它留下任何残留物。
与这种对“我”(nafs)的激进否定相比,任何仅源于意志的手段,如禁欲主义(az -zuhd)都只能起到准备和辅助的作用。【8】可以补充的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手段在苏菲主义中从未获得过它们几乎绝对的重要性,例如,对某些基督教僧侣来说;即使在一个或另一个 ṭarīqah 中严格实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8.苏菲不仅在身体中看到滋养激情的土壤,而且在精神上看到积极的一面,即宇宙的一幅图画或简历。在苏菲派的著作中,“神殿”(haykal) 一词被用来指代身体。穆西德丁·伊本·阿拉比 (Muḥyi-d-Dīn ibn ʿArabī) 在他的 Fuṣūṣ al-Ḥikam 中关于摩西的章节中将其比作“居住着主的和平 (Sakīnah) 的约柜”。】
苏菲派的象征主义具有任何心理学分析领域之外的优势,将有助于总结刚才所说的内容。它给出的画面是这样的:精神 (ar-Rūḥ) 和灵魂 (an-nafs) 为占有他们共同的儿子心脏 (al-qalb) 而进行战斗。ar-Rūḥ 在这里可以理解超越个体本性【 9】 的智性原则,而 an-nafs 可以理解为心理,其离心倾向决定了“我”的扩散和不稳定。至于 al-qalb,心脏,它代表灵魂的中心器官,对应于物理有机体的重要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Al-qalb 是“垂直”射线(即 ar-Rūḥ)与“水平面”(an-nafs)的交点。
【9.rūḥ 这个词也可以有更特殊的含义,即“生命精神”。这是它在宇宙学中最常用的意义。】
现在有人说,心具有产生它的两种元素之一的性质,它在这场战斗中获得了胜利。既然 nafs 占了上风,心就被她“蒙上了面纱”,因为灵魂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主的整体,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包裹在她的“面纱”(ḥijāb)里。与此同时,nafs 是“世界”的帮凶,因为它的多重性和变化性,因为她被动地拥护形式的宇宙条件。现在,形式分裂和束缚,而超越形式的精神则联合起来,同时将现实与表象区分开来。相反,如果精神战胜了灵魂,那么心就会变成精神,同时也会改变灵魂,使她充满精神性之光。然后,心也揭示了它自己真正的样子,即作为人类内在神圣奥秘 (sirr) 的帐幕 (mishkāh)。
在这幅画中,精神以阳性的功能出现,与阴性的灵魂有关。但是,精神是善于接受的,反过来,它与至高无上的存在相比则是阴性的,只因其宇宙性质而有所不同,因为它在与受造物的关系上是两极分化的。从本质上讲,ar-Rūḥ 等同于神圣的行为或秩序 (al-Amr),在《古兰经》中,它由创造词“Be”(kun) 表示,是至高无上的存在的直接和永恒的“发音”:“......他们要问你关于圣神的事:说:圣神是我主的等级的,但你所领受的知识却很少“(《古兰经》17:85)。
在进入精神性解脱的过程中,默观被束缚在精神中,并借着它进入对神的原始表达,“万物都是借着它造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在没有它的情况下被造的“(圣若翰福音,1:3)【10】 此外,严格来说,”苏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本质上与神圣行为相同的人;因此,“苏菲不是被创造的”(aṣ-ṣufi lam yukhlaq)的说法,这也可以理解为,这样重新融入神圣实相的存在,根据他的“基本可能性,在其非显现的状态中是不变的”,从永恒中认识到自己在其中“就像他曾经一样”——引用穆哈伊·丁·伊本·阿拉比的话。然后,他创造的所有模式都被揭示出来,无论它们是时间性的还是非时间性的,都只是这种基本可能性的不一致反映。【11】
【10.对亚历山大利亚人来说,解脱也是分三个阶段实现的,具体来说,这与圣神、圣言和圣父相对应。】
【11.如果说每个存在者的基本或神圣的可能性是合理的,这种可能性就是他“个人独特性”的原因,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在神圣的秩序中有任何多样性,因为在神圣的统一性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独特性。这个真理只有在话语理性的层面上才是一个悖论。这很难想象,只是因为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为自己塑造了一幅神圣合一的“实质性”图景】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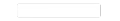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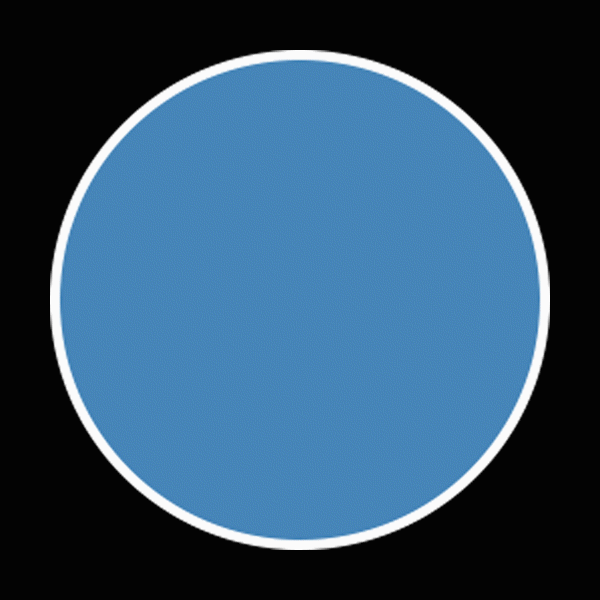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