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告别让肠胃与心灵得到双重满足的宁波,我继续南下。高铁迅捷地驶向温州南站。
温州,这座与中国最庞大的地区性商人群体紧密绑定在一起的城市,长久以来并非理想的旅游目的地。它虽然临海却无独特风光;城市发展缓慢而缺乏规划;文物古迹更是乏善可陈。不过,深入城市西面的群山之中,便可发现隐藏的好景致。
到达温州时已是傍晚,无法立刻动身进山。考虑到交通便捷性,我决定在长途汽车站附近对付一晚。眼见汽车站附近的市容与我记忆里的九十年代街景颇为相似,我不免对即将入住的酒店环境暗暗担心。令我惊讶的是酒店外表虽然稍显老旧,内部装修和房间质量均还令我满意。
入住房间后稍事休息,看表已是晚餐时间。我打开手机搜索了一番附近的热门餐厅,发现有一家口碑老店就在隔壁。事不宜迟,我立刻披衣寻访。餐厅大门开在一栋平淡无奇的商厦转角。一层只有楼梯而无桌椅,登上三层才发现别有洞天:亲切而不失礼貌的接待员、格调优雅的装修风格,以及佐证这家餐厅生意的络绎人潮。
浙江人爱吃蟹,于是发明出数百种吃法:清蒸、爆炒、下面、生腌等等不一而足。素闻温州有道特色菜肴,是把鲜活的梭子蟹冷冻后,做成冰淇淋口感的“江蟹生”。昨日在宁波品尝了梭子蟹炒年糕,咸香尚余唇齿间;今日路过温州,便想一探这“江蟹生”的究竟。
店家听我口音便面露难色。或许是怕北人不习生腌?君不见“生腌小海鲜”已开遍南北网红街区吗?不过我确实没有接触过这类食物。考虑到肠胃状况,秉承着“听人劝,吃饱饭”的教诲——我另寻一道特色美食:“清蒸蝤蠓”。
这“蝤蠓”乃是温州人对梭子蟹科下锯缘青蟹的爱称。每年农历八九月正处虾蟹繁殖季节,此时蝤蠓个大肉多,佐以蟹黄蟹膏,堪称人间至味。宋代的文学家及著名美食家苏轼曾赞曰:“溪边石蟹小如钱,喜见轮囷赤玉盘。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加餐。” 不过我不以为然。
我一向不喜食螃蟹,寥寥几次料理大闸蟹的经历让我对这壳硬肉少的生物难言喜爱。这份不喜后来推而广之到所有“蟹门”成员。以至于这道菜端上来时,我感觉那金黄色的身影似乎仍在向我张牙舞爪。
谁知一口下去,鲜甜的蟹肉在口中爆开——我便停不下嘴了,一只七两的螃蟹里里外外被我舔食的一干二净。苏公又说:“蛮珍海错闻名久,怪雨腥风入座寒。”恐怕他也是品尝后才惊觉乃是人间美味。可惜庸人如我,不能“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了······
前一晚品尝美食养精蓄锐,第二天一大早我赶早班车向西部的茫茫群山里进发。经过一小时的车程,汽车抵达文成县。它位于浙南的峡谷深涧中,因为明代开国元勋刘基(字伯温)的故乡而出名。“改革开放”后走出了不少成功商人。近年县里着重打造“刘基故里景区”,其中包括了一处自然风光——“百丈漈”。它是我此行的目的地。
“百丈漈”里的“漈”是当地方言中瀑布的意思。顾名思义,这个景区内的核心看点似乎是一座高达百丈的瀑布。我一向对夸大宣传嗤之以鼻。为了不至于见到后失望而自责乱花钱,我没有购买直达谷底的电梯票;而是选择走人行步道下到谷中。下行的台阶虽然谈不上陡峭,但看似无尽的数量和炎热的天气让我有些后悔自己的选择。
闷头前行一阵,隐隐听到激流撞击岩壁的声音;再下行几步瀑布隐约露出身影;峰回路转后瀑布完整映入眼中,此刻我的疑虑与疲惫均烟消云散:“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李白形容庐山瀑布的诗句用在这里丝毫不显夸张。
抵达谷底而未近瀑布时,就已感觉水雾扑面而来;近处则入晴空急雨——将近二百米的落差以及丰沛的水量裹挟而出的雄浑气势不负“百丈”之“漈”——在场的游客无人在意被打湿的衣服,大家都沉浸于这壮丽的景色中。
瀑布前的小山包上有一座仿古石亭,与瀑布相互衬托营造了完美的古典气韵。瀑布上游修建了水库,故而一年四季都能保持其雄壮的形象;又因其极具传统美学的意境,吸引了不少游客在这里拍摄古装照——哪怕被溅起的水花淋遍全身也毫不在意。
景区内共有三座瀑布。最漂亮的当属第一漈。第二漈的气势稍逊于前者,不过游客可以从其后的山洞穿过,近距离感受扑面而来、震耳欲聋的水势。穿越过程中身边游人尖叫连连,听起来乐在其中。
在第二漈能拍摄到非常具有中国山水画风格的照片。想到近年中国内地的电子游戏产业势头正盛,不少重量级作品的场景都借用了现实风光。希望百丈漈的身影有一天也能出现在这类优秀的电子游戏作品中,展现给全世界。
沿着景区标识前进一路无话。到达第三漈时,已经靠近景区出口。这里地势平缓,水流已经褪去了狂暴的气势。然而这座并不雄伟的瀑布却与几块石头相映成趣。指示牌上说它们和某位神仙有关,估计也是前人见这怪异的美景而附会得来。
参观完“百丈漈”后我对当地新建的“刘基故居”兴趣缺缺,遂打算前往下一站。无奈文成虽然离我想探访的泰顺不远,可一天只有早上的两班交通客车。此时已到午后,我只能先返回温州,再乘坐汽车去泰顺。一来一回耽误了不少时间。
此行是为了参观保存于乡间的建筑孤本——木拱廊桥。在世界建筑史上,鲜见利用纯木结构制造的桥梁;而在中国,木拱结构的廊桥曾风行于北宋。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有座横跨汴水的桥梁就是典型的木拱廊桥。它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品类,同时具有极高的传统美学价值。
自北宋灭亡后木拱廊桥似乎消失在历史的风沙里,直至900多年后于浙闽交界的崇山峻岭中重见天日。泰顺附近的小镇泗溪有“北涧”与“溪东”两桥,大概是游客最容易抵达的廊桥。近年这里被规划为“廊桥文化园”景区开门迎客。
溪东桥长41.7米,北涧桥长50余米;两桥均为叠梁式木拱廊桥,采用无钉铆榫卯工艺搭建。它们合称“师徒桥”,按当地说法似乎是由师徒二人先后主持设计。北涧桥的造型古拙质朴,溪东桥则飞檐翘角;一静一动间尽显工艺之美。
除了这两座桥以外,我还深入人迹罕至的溪谷深处,探访了一座因道路荒废而鲜有人迹的廊桥——三条桥。它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由于当年在拆旧桥时发现有贞观年号的旧瓦,因此有人猜测三条桥可能建于唐代。如今的三条桥是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重建,桥长约27米。据说三条巨木为主梁跨溪架设成桥,由此得名“三条桥”。
看着这些与青山绿水长伴的孤独身姿,我想起了著名的“忒休斯之船”悖论:由于既处山区又临大海,这些廊桥幸免于人祸却难躲天灾。史料里尽是它们屡毁屡建的蛛丝马迹。尽管设计与工艺都是传统风格,却很难界定它们究竟算不算“文物”?
不过也是在这青山绿水间、在一代代乡民们锲而不舍地营造记录中,我感到这疑惑并不重要了——如果身份并不局限在实际物体和现象中,那么“存在的意义”便能随着时光而变迁——这些桥已经超越了时间,成为当地风土和记忆的一部分。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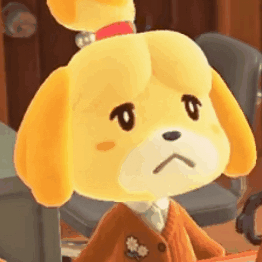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