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没有路的目的,没有目的的路。”
——罗杰·加罗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
当一个人在早上醒来,发现他自己莫名其妙变成甲虫(被审判),但他只是对此感到略微惊讶,随即想到行动不便可能会耽误上班,他努力地蠕动(上诉证明)却进度缓慢,光是这一动作就已耗尽他全部的精力,唯有被某种内心深处的责任感拽着,被周遭时刻注视着的,似远似近的目光敦促着,于是他疲劳的肉体向前蹒跚,前方似乎有着什么能够接触到的进展,但当接近之时却又像迷雾般徒留下朦胧的影像,那种雾气拂过脸上似有似无的触觉又证明了它曾经的“存在”,伸出手来,却抓不住碰不到任何“实在”的东西,既有的道德素养要求他不得僭越道德与法律的大门来取得进展,于是这段努力似乎又成为了徒劳,疲困再度席卷,在感受着这种劳累同时又得强撑着踟蹰,前方又浮现出了一个新的海市蜃楼,于是他只得在梦呓中试图找到道路,在迷茫中寻得目的。
疲困的梦呓
疲困的梦呓
卡夫卡作为现代派文学鼻祖,表现主义文学先驱,他的小说的字里行间处处表现着诡谲的跳脱情节与违反理性的荒谬,里面的每一个人包括主角似乎都陷入着一种无能为力的疲惫,连带读者也一同感到这份疲惫,所有人想保持着理智(非理性)所作出的各种努力注定是徒劳,所有行动只会耗尽全部精力,消磨人的意志。在这种疲困的,睡眼朦胧下所见到的场景便是卡夫卡写出的环境——疲困非常,却保有一定的清醒,在他人敦促下无目的地前行,他的行动如他在这种状态下发出的梦呓,毫无意义。
《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他的思维实际并无改变,思考的事情依旧是上班怎么办,家庭收支怎么办,妹妹的梦想怎么办,被房客发现怎么办,如何让家里人好接受一点?
然而,他的家人却更像是变成了“甲虫”,压低细碎的声音,蜷缩置身于黑暗与幽闭的环境,以此来不让格里高尔发现他们,妹妹甚至以因忍受并照顾格里高尔提高了家庭地位,当母亲试图来帮忙时还以大哭来抗议她僭越了自己的权力。于是先前注视的关系倒差,格里高尔成为了唯一一个被注视的“物体/客体”(Object),逐渐与社会断层,割裂。他在变成甲虫前被家人注视着,成为他们的“主体”,是他们的物质与精神支柱;变形后来被家人注视着,成为他们的“客体”,变得已经不再重要,甚至成为累赘,希望他赶紧死掉以摆脱这种困境。凝视(gaze)时刻存在着,仿佛不是格里高尔这个人的物理形态变化,而是这些它者(the other)的凝视才使得格里高尔存在,最后这些隐秘的,恐惧的目光给他判处了死刑。由此,我们可以从《变形记》中窥得一些线索,以便更好的去理解他后面的作品。
在《审判》里,K起床后莫名其妙发现自己被指控了,要受到审判,所有人都知道他犯了事,且每个人都对他的案情都非常了解,实时更新着他的最新情况,但唯独他至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什么事了,所有人都告知他应该付出努力来争取案情的进展。
但如果凭靠我们的理性,在不知道为什么受到指控的情况下又如何作出努力呢?他周围的人时不时透露出能被我们理性捕捉到的所谓“可能有用”的信息,于是他去了解,交谈,咨询,然后这些人或这些事又引向了新的“可能有用”的线索与方向。
他行走在没有目的的道路上,因为还能行走在道路上,似乎在做着努力所以暂时满足了因漫无目的而想去行动的心理,他可以说出自己做出了哪些努力,并言之凿凿。
但他同时也是行走在没有道路的目的里,他可能连自己都意识到了这种荒谬,不知道做这些事到底有什么用,如同身处在梦境里,只能用一种无奈的愠怒去指责那些人——诘问乱翻东西的同事,内心深处希望他们受到惩罚,于是他们躲在杂物间里被打,被K不小心撞见时引发了他的愧疚,对这超出预期的后果疑惑先前的告状是否有些过分,似乎变成了他在对他们进行处罚;想辞退万众敬仰的律师,诘问他是否真的在有帮助,但他内心深处其实并不在乎这点,只是想以此摆脱这种困境。于是在律师卑微地挽留无用后,律师招进另一个委托人波洛克开始了一场表演,对律师如此敬畏甚至到畏惧的波洛克(原著里他为了时刻听到律师对他的召见而住在律师家里的阴暗小房间,还要受女佣监督,看他“表现”好不好),布莱克是如此卑微害怕,律师又是如此耀武扬威,让K产生了律师似乎在炫耀自己的权力与他机会的来之不易,让他重新疑惑是否真的要完全失去这个机会。
这些场景让人似乎疑惑自己似乎身处极深的梦境中,因疲困索求睡眠,又因社会/家庭的外在条件(如快要上班,上学等时候,想多睡一会的感觉)迫使自己要极力睁开眼眸,嘴里咕哝地发出梦呓来试图让自己清醒,但疲困依旧,甚至愈发失去力气。
《城堡》中的K(同个化名,与《审判》中的K无联系)更是集前二者之最。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封闭。在这个没有进步的天宇下,卡夫卡要以特殊形式引人希望。在这一点上《审判》和《城堡》所走的路子不是同一方向,两者相相成。从这一部到另一部作品,隐隐可见难以觉察的进展,表明在遁世方面取得了不可估摸的成效。《审判》提出的一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由《城堡》解决了。前者文中描述,遵循的方法近乎科学,却没有结论,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解释。《审判》诊断病情,《城堡》设想疗法。不过,这里开出的药方治不了病,仅仅将病症打发回正常生活中,并且帮助人接受这种病痛。“
——加缪《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
这是一个渴望着取得成效却最终注定疲于死亡的人(这种说法源自卡夫卡对朋友的口述,《城堡》的结尾K最后会因劳累而死)。
此处贴出加缪写的《城堡》故事梗概:
迷茫的踟蹰
迷茫的踟蹰
卡夫卡的作品到底想表达些什么,在这些吊诡的文字中,我们如K般彷徨。是如卡夫卡的好友麦克斯·布罗德一样用神学或者神秘主义来理解?
“这座K未能进入、令人不解地连接近都未能真正接近的《城堡》正是神学家们称之为“仁慈”的那种东西,是上天对人的(即村子的)命运的安排,是偶然事件、神秘的决定,天赋与损害的效力,是不该得到和不可得到的东西,它超越于一切人的生命之上。在《诉讼》和《城堡》里,神的(在犹太神秘哲学意义上的)这两种表现形式--法庭和仁慈--恐怕就是这样来表现的吧。
K设法在城堡脚下的村里扎下根,以寻求与犹太的仁慈的联系。”
——麦克斯·布罗德,《城堡》,第一版后记(1926)
抑或是加缪以此作为存在主义跳板的说法?
“卡夫卡否认他的上帝道德高尚,明确无误,善良和始终如一,不过,这只是为了更好地投入上帝的怀抱……从前正是这种思想,带着原始基督教和宣布救世的褔音,掀动了旧世界。然而,在标志一切存在派思想的这种跳跃中,在这种一意孤行中,在这种无平面的神性的丈量中,怎么就看不到自暴自弃的一种清醒的踪迹呢?
……在一个万事俱备而又什么都未解释的世界里,一种价值或一种形而上的丰产性,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
—————————————————————————————————————————
“卡夫卡同他的上帝争执道德上的伟大、启示,善与一致性--但只是为了更热切地投入他的怀抱……存在主义思维的基础是一种无限制的希望,是那种曾经以原始基督教、以救世福音翻掘过的旧世界的希望,但是,在这种为存在主义思维所特有的飞跃中,在这种执拗中,象这样测量不可测量的神性,我们怎么会看不出一种否认自身的明智的特征呢?
……在一个什么都具备、什么都不明白的世界里,一种价值或一种形而上学的效益性将会是一个荒唐的概念。”
——加缪,《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
(前为李玉明译,后为刘半九译,后者现改名绿原,可见不同时期的解读倾向,前者更为客观,而后者则可能更受当时布罗德推崇的解读的影响)
还是像罗杰·加罗蒂一样试图加以革命性与政治化来评价?
“卡夫卡不是一个绝望者,是一个见证者。
卡夫卡不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启发者。
他的作品表现了他对世界的态度。它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它既不想解释世界,也不想改变世界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罗杰·加罗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卡夫卡》
在我个人看来,也许都并不尽然,在查阅资料时,通过了解对卡夫卡解读的一众名家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思潮的坎坷变化。从布罗德推崇的宗教解读开始,将“城堡”的有权却不可及误解成“上帝”的万能却不能及。后来的加罗蒂也同样犯了类似错误,试图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反抗”用作意识形态的表征,赋予一种明确的定义,然后就这样“超越”了它。他们虽都做到了对卡夫卡小说题材与形式解读的精准把控,却错误地将其价值置于超验的范畴,大大淡化了对其解读角度的可能性,同时失去了对更深层次的剖析,此处先按下不表;他们似乎在说:
K,“城堡”的官僚与法官的“审判”就是你道路的终点,你的行为是好的,何必探寻目的与道路,以及这样为什么是“好”的呢?
布罗德之后许多人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尤其以瓦尔策尔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心理学来解读),但也注定会碰壁,因为对于这种看似混乱跳脱的情节,却多以理性逻辑托底,即人物始终都在寻求道路,他的教育与外在表现始终都基于我们所谓“正常人”的思维来行事,他意识清醒,完全可以清晰地作出关于他每一个行为的逻辑推断。故这种解读虽能抓住其一些艺术特点,却又如K般走进“迷雾”,徒留雾气存在的痕迹;
K似乎找到了道路,又似乎找到了目的,有时候他似乎分不清道路和目的有何异同。
那么卡夫卡的作品是不可知的吗?波里策站在实证主义立场断言道:“任何想得到结论或解释谜底的企图必然归于徒然”,似乎所有对他的认识已经走到尽头,犹如缘木求鱼,对K讲道:
K,你是没有终点的,放弃吧,连那试图迈出步伐的踟蹰都毫无意义。
“能唤起愤怒的明了性”,卢卡契读出了K,抑或者说是卡夫卡的恐惧,这是一种对“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恐惧,所有可见的事物都是影像,所有目光都将他吞噬;
K,你究竟在顾虑什么,为什么会迷茫,又为什么会踟蹰,是因为恐惧吗?
K始终在走着,他变成甲虫的同时挪动着身体,却不在意身体的变形(《变形记》);他被审判的同时走在上诉的路上,却永不见院长(《审判》);他在受聘的同时寻求着通往城堡的道路,却永不见领主(《城堡》);他修筑长城的同时疑惑其作用,永不见皇帝(《万里长城建成时》);他恐惧敌袭的同时不停地修筑地洞的暗道,却永不见敌人(《地洞》)。
结合卡夫卡本人的切身经历,我们能找出这些作品的一些线索。卡夫卡在父亲的企业里工作,感受到剥削与压迫,有着“逃出父亲范围的愿望”;在保险公司做职员,研究司法让他备受折磨,“我的精神食粮是一堆木屑,更要命的是几千张嘴巴已经在我之前嚼过这堆木屑了。”(《致父亲的信》) ,同时为处于他的地位经常要说谎而痛苦;他寻求爱情的慰籍,但对于他来说这是种接近现实又远离现实手段,他希望能在这个港湾稍作歇息,但同时深知这不过是种模糊的暧昧,正如《审判》的莱妮与《城堡》的弗里达,佩琵与主人公的关系。
迷茫踟蹰,游离失所,寻求慰籍,依附同化但警惕异化,竭力保持清醒但劳于奔波,陷入被消磨力气的疲困,只能徒劳地发出梦呓以试图驱赶,这便是K,也是卡夫卡,甚至是我们,以及跨越不同时代的各种人的生活困境。
我们竭力地与时代抗衡,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保持清醒,主动获取的知识让我们保存警惕,切勿陷入沉沦。但日复一日的劳作,疲于维持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却在逐渐消磨我们的激情与特性。《审判》让我们等候在法的大门外,在疲困中死于不知何时裁定的判决;《城堡》中作为一个多余的人,疲竭于寻找前往城堡道路上。
借用加缪在《西西弗神话》的附录《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一文中的一个故事:
“……那个疯子在澡盆里钓鱼的故事。一位对精神病治疗有方的医生问他:“咬钩了吗?”只见他毫不客气地回答:“没有,笨蛋,这是在澡盆里呀。”这则故事颇为怪异,但是从中能明显地领悟出,荒诞的效果同过分的逻辑结合得多么紧密。卡夫卡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不可育状的天地,人决心自虐,在澡盆里钓鱼,明明知道什么也钓不上来。”
既知没有目的,也没有道路,那么又为何迈出步伐,行走在这天宇间。
K,你为何而行走,为何而存在?
(待续)
本篇参考文献:
《论卡夫卡》前言,叶廷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已停版)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罗杰·加罗蒂
《西西弗神话》,《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加缪
《城堡》,第一版后记麦克斯·布罗德
《城堡》,《审判》,《变形记》,《地洞》(节选),《致父亲的信》(节选),《万里长城建成时》(节选)
以及一堆网络资料
PS:关于下篇已经有思路了,但是不太敢打包票发布的时间,敬请期待
笔者才疏学浅,还望各位海涵,批评指正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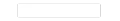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