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我把装着蛇尸的证物袋扔进后备箱,钻进了车里。从万达广场的地下停车场到我租住的公寓大概有30公里,绝大部分路程都在笔直的团黄路上,过去两年我几乎每天都走这同一条路线。我把手一放上方向盘就开始思考,怎样用这袋湿垃圾吓一吓我那个植物学家室友。
我的室友叫林博,比我大一岁,又高又瘦,白得惊人,活像一只得了白化病的巨型竹节虫。两年前我在本地论坛上发了合租广告,过了半天他就出现在公寓门口了。他搬过来的那天晚上是我的女房东开的门,在看到他那双下垂的棕色大眼和又高又大的鼻子后,她误认为他是高加索那边来的洋移民,大声嚷嚷着不让他把行李搬进来。他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出过省。他在武汉某所双一流大学的植物学系本硕博连读,毕业后就一直在光谷的一家生物企业的海洋生物实验室工作。当时听完他的自我介绍后我还以为他是那种前途一片光明的年轻科学家,跟我合租只是暂时负担不起武汉的租价,要不了多久肯定就会搬到武汉去。
跟他住了一个月后,我才发现现在的科研已经跟我认知中的科研完全不同了。
他根本就不出门,每天起床洗漱后就往客厅的电脑椅上一坐,通过放在电脑桌上的全息影像仪远程指挥实验室里的机械臂进行实验,就连实验日志也是用神经同步的手段操控仿生机械手输入到实验室的电脑里。据他说这是实验室的硬性要求,每天必须在实验室内部写完当天的日志。公寓里有厨房,各种器具、调料一样不少。但他只点外卖,而且只在固定的三家店里点餐,在每家店里只点固定的菜式,每星期全部轮换着点一遍,下周又重来。
一年中有一半的工作日我会值夜班,每次我在凌晨四点多回到公寓时,他房间里的灯都还亮着。我问过他的作息规律,每次他都是咕哝几句后吐出五个字:“反正不确定。”我到现在都还有些担心,要是他哪天猝死在公寓里,会不会导致我被剔除出警队。
我缓缓踩下刹车,车身完美地停在公寓旁属于我的停车位上。我打开后备箱,提起了里面的证物袋。在后备箱关上的一瞬间,停车位的边线发出幽幽蓝光,闪烁了几下,我的标致自动进入了充电模式。
公寓一共两层四套房,我们在二楼,对门的那一套正空置着。一楼的两套都是短租客,每几个月都会换一波人。当然,全是国人长相,房东从不租给洋移民。我的室友几个月前在我们的房门上装了虹膜锁,哪怕我把前罩玻璃的不透明度调到0,这倒霉玩意也没法隔着头盔识别出我的眼睛。我已经养成在上楼时就摘下头盔的习惯了。
我把双眼对准安装在猫眼下面的一块黑色屏幕,一阵电子音效响起,门打开了。他今天仍然像往常一样坐在他的电脑椅上,只穿着纯黑的T恤和裤衩,手上戴着一对我没见过的蓝色手套,上面布满了复杂的纹路。电脑桌上的全息影像仪安静地工作着,一排培养皿悬浮在他的面前。他抬着右臂,手腕垂下,大拇指和食指做出夹取的姿势,整只手不停地晃动。其中一个培养皿里有一块绿色的东西,跟随着他右手的动作同步晃动着。
“今天回这么早?”他鼻音很重地打了招呼,仍然聚精会神地盯着培养皿。
“接在我后头的是个新人,照规矩得包了头一天剩下的白班和夜班。”我晃了晃手里的证物袋,还没想好怎么吓他。
他大概听到了证物袋晃动的声音,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用左手揉着右肩,扭头看着我说道:“带了什么吃的回——”
“我操!”他两脚猛地一蹬,电脑椅载着他滑向后方,撞在墙上停了下来。
“你他妈疯了吧!带条死蛇回来干嘛!”他本来就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两只手都举起来对着我,仿佛要隔空把我推出门外。
呃…证物袋是透明的,但没想到这么朴实的方法都能吓到他。他跟我说过他不喜欢爬行动物,尤其讨厌蛇。不过与其说是“讨厌”,我宁愿将这种反应归类为“害怕”。
“咳…那新人是个事儿逼,换班的时候要我把路上的一条死蛇带回局里报备。我懒得浪费时间跟他讲道理,就装着带回来了。呃,这一路上没找着处理这种垃圾的地方嘛。”我装作无奈的样子解释了几句。
他没好气地回道:“你应该知道把垃圾扔到花坛里也会有清洁机器人收走吧?别给我装什么遵纪守法的老条子。”
我耸了耸肩,吓也吓到了,也懒得再编理由了。我把证物袋放到了厨房里,打算明天出门的时候和其他垃圾一块扔了。我拉开了厨房的窗户,虽然证物袋的密封性很好,但我还是不想冒闻一晚上尸臭的风险。
我回到客厅时,他已经溜回了电脑桌前,手里正拿着一根粗大的深绿色玻璃管。
“这是啥?”我问道,一边用双手在蛇鳞衣的领子内侧摸索着触发点,我打算直接用自动脱衣功能。
他似乎已经从惊吓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了,嘿嘿笑了两声,控制着电脑椅转向我,说道:“别急着脱你的蛇鳞衣,我托同学送过来个好东西。”
我停下了动作,不禁好奇:“同学?你这样一年不出一次门的还能和同学保持熟络?而且你的同学看到收件人是个条子不觉得奇怪吗?”
他所有快递的收件人都是填写我的信息,因为交通警察有任何快递免费上门的特权,对于他这种懒狗来说当然是不蹭白不蹭。
他学着我的样子耸了耸肩,慢悠悠地说道:“你一个交警还有资格说我呐?你一年到头除了跟支队长交报告,能跟你的同事说几句话啊?现在谁不是在网上的社交多过现实中的社交啊,总有一天大家都会彻底依赖网络进行交流的,我只是提前进入了那个时代而已。”
他又举起手中的玻璃管晃了晃,笑眯眯地说:“再说了,这种高度机密的东西怎么可能用快递邮寄呢?这是我的同学亲自送过来的。”
“这到底是啥?全新包装的青岛啤酒?”我把腰间的手枪放到了电脑桌上,一边问道。
他先是猛翻了一阵白眼,然后又正襟危坐,举起手里的玻璃管:“这是盗食质体的合成物。”
“啥?哪四个字?”
他好像已经预料到了我的反应,自信满满地说道:“哪四个字不重要。这是一项秘密工程的产物,旨在用新技术对以前因为实验条件不足而放弃的生物工程项目重新展开研究。有一种生物叫绿叶海蛞蝓,能够从藻类中吸收叶绿体,并利用这些叶绿体进行光合作用为自己储存能量,被它吸收进体内的叶绿体就被称作盗食质体。这种生物在出生时是白色,但在进食了绿藻后就会‘变绿’,甚至会变成叶子的形状。上个世纪就有实验证明,存有叶绿体的绿叶海蛞蝓能在完全不进食的条件下存活十个月,这种生物一辈子也就活这么长了。但是叶绿体在进行光合作用时会消耗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90%以上都要依赖藻类的核基因组编码合成,绿叶海蛞蝓不知怎的却能够保持这种蛋白质的供给。”
他抓起电脑桌上喝到一半的罐装红牛吞了一口,继续向我解释:“当时前美国有个团队用实验证明了绿叶海蛞蝓体内含有藻类的核基因组,就判断绿叶海蛞蝓能像吸收叶绿体一样‘夺取’藻类的DNA。不过没过几年就有人指出实验设计不严谨,并设计新的实验给证伪了。尽管没有明确结论,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方向很有前景,国内、前美国、欧盟、印度都有相关的项目。”
“绿叶海蛞蝓的主要食物是一种叫滨海无隔藻的真核藻类,只在前美国东海岸有分布,要想在实验室里培育绿叶海蛞蝓就少不了这种藻类。后来美国解体那几年乱得很,等北美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以后,滨海无隔藻已经被认定灭绝了。野生的绿叶海蛞蝓越来越难找,研究相关项目的科学家基本都转移去别的领域了,这些项目要么搁置要么终止。”他一手握着玻璃管,一手拿着红牛,跟表演快板的相声演员似的滔滔不绝。
“但是!”他“啪”的一声将红牛拍在桌上,“在所有人都放弃了滨海无隔藻,进而放弃了绿叶海蛞蝓后,我说服了公司的技术总监,派人去加拿大找了一家渔业企业在北美洲东岸大规模搜寻绿叶海蛞蝓。”
“果然不出我所料,滨海无隔藻并非真的彻底灭绝,在弗吉尼亚王国的海岸上再次发现了滨海无隔藻的踪迹,和绿叶海蛞蝓的发现地点高度重合!我一直有所猜测,绿叶海蛞蝓和滨海无隔藻恐怕不仅仅是食物链上相邻的两层,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是一种深层次互利共生的关系。实际上,那个前美国团队的结论虽然是错误的,但也给了我某种灵感。我想,在绿叶海蛞蝓将藻类叶绿体化为己用的过程中,其本身就充当了藻类的基因库,绿叶海蛞蝓‘变绿’也不仅仅是叶绿素含量上升导致,实际上也是其自身的基因表达被‘污染’的结果。”他的表情逐渐有些得意洋洋了。
“等等…”我用脑中残存的高中生物知识勉强跟上他的思路,“如果绿叶海蛞蝓的基因已经被污染了,那它们的后代不是就不需要吃藻类,直接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吗?再说这不就是那个前美国团队的结论吗?不是已经被证伪了吗?”
他又露出了那种“就知道你会这么问”的表情,接着说道:“你看,你陷入了之前的研究者所踏进的陷阱。我说的‘基因污染’并不是指把外界遗传物质直接吸进细胞核里,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储存在绿叶海蛞蝓干细胞的细胞质中。”
“什么形式?”我顺水推舟地问道。
他竖起左手的食指:“转座子,或者叫跳跃基因,这是基因跨物种传递的媒介。”
“不是你等等,”我有些糊涂了,“不是说了绿叶海蛞蝓没吸收基因吗,怎么又绕回来了?”
“耐心听。自然界几乎所有真核生物的基因组都含有转座子,在植物中转座子更是占到基因组的80%以上。而对于绿叶海蛞蝓来说,滨海无隔藻的转座子比例达到了100%。在被绿叶海蛞蝓进食后,滨海无隔藻的DNA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分片段全部解离,就像掉在地上的乐高积木一样四散开来。这是一类全新的转座子,它们并不会整合到海蛞蝓的基因组上,而是被贮存到海蛞蝓干细胞的细胞质中。与光合作用相关的转座子在细胞质中就会进行转录,生产光合作用所需的蛋白质,这就是为什么海蛞蝓的基因组中不含光合作用所需的基因序列,但仍能为叶绿体补充蛋白质。而海蛞蝓的‘变绿’以及叶子形状,其实是其他与植物性状相关的转座子也进行了转录,使得绿叶海蛞蝓这种动物具备了植物的特征。而在合适的条件下,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分布在这些干细胞的细胞质中的转座子会进入细胞核,以‘鸠占鹊巢’的方式使海蛞蝓干细胞分化成滨海无隔藻,最终实现‘复活’。”
“等会,”我努力在脑中串联起他讲的东西,“这些转座子就是DNA片段吧?它们是怎么从海蛞蝓的消化道跑到干细胞里去的?这个过程中转座子不会被分解掉吗?”
他略显无奈地看着我:“我知道你从转座子那里就听不懂了,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不要解释的好。”
“我操,这些你都是怎么发现的?”我实际上在转座子之前就开始听不懂了,但还是大受震撼。
“天才嘛,就是1%的努力和1%的灵感再加上98%的运气。”他挠着头嘿嘿笑了一声,“在几个大城市里有这种实验仪器,可以在零点几秒内以超低温冻住实验体,而且不用做切片就可以直接观测实验体的细胞,甚至可以检测遗传物质。我当时是第一次接入这种仪器,我本来想观察一下海蛞蝓进食时的消化道细胞的,结果…”
他摊开双手,轻松地说:“幸好在超低温状态下DNA更加稳定,才刚好让我‘抓拍’到了这一瞬间。我在此基础上利用超低温继续展开了一系列实验,花了差不多一年才分析出整个过程的机理。实验证明,滨海无隔藻在被其他生物进食后也会解离出转座子,但无一例外都被无情地消化掉了;而绿叶海蛞蝓在进食其他藻类时就不会容忍它们的DNA进入自己的干细胞,会将其无情地消化掉。滨海无隔藻和绿叶海蛞蝓,就像海洋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滨海无隔藻无私地为绿叶海蛞蝓提供叶绿体与光合作用所需的蛋白质;而绿叶海蛞蝓则充当了滨海无隔藻的基因库,即使后者灭绝,也能给予其新生。”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变大了,离开电脑椅站了起来,张开双臂,活像乡下教堂里的神父:“这一对生物就是自然界高超设计的完美证明,对基因了解得越深就越能感受到人类认知的浅薄。不论生物工程、仿生学再怎么发展,也只是对自然设计的拙劣模仿。就像那帮编辑宠物基因的家伙,他们没有资格将自己的行为称作‘造物’。我们可以不断接近自然,但永远无法达到自然的高度。”
我叹了口气,他又开始了。不过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有办法把他从这种状态拉出来。
“你就说你信神嘛,不用搞得这么复杂。没必要不好意思,你看杨振宁不也信神嘛,没事的。”我用开导的语气对他说道。
他仿佛被人泼了一盆冷水,眼睛和嘴巴都耷拉了下来,说话的鼻音更重了:“第一,杨振宁不信神。第二,我所说的自然…”
这时他才发现我又玩起了老花招。他停下话语,对我比了一下中指,一屁股坐回电脑椅上。我当然知道他那套“宇宙设计论”的观念,但将宗教和这种观念混淆每次都能惹得他发毛。我控制不住地呵呵笑了起来。
当然我还是很想知道那根深绿色玻璃管的作用,便立马转移了话题:“呃…你说的这些东西和你手上的那根玻璃管,呃,还有我的蛇鳞衣,有什么关系?”
他斜眼瞧着我,又恢复了一点热情:“事实上,你身上那套蛇鳞衣某种程度上就是这项工程的产物。”
“哈?”我顿时大惑不解,“那为什么这身制服要叫蛇鳞衣,而不是叫鼻涕虫衣?”
他调低了电脑椅的靠背,懒洋洋地说道:“你现在这套蛇鳞衣是迭代了20几代的产品,第一代蛇鳞衣确实主要参考的是基伍树蝰。在后来的更新迭代中,蛇鳞衣加入了更多其他生物的仿生学设计。你是两年前入职的,刚好赶上最新一代的蛇鳞衣。但所谓最新一代实际上并不完整,它还缺少了关键的盗食质体合成物。”
他举起手中的玻璃管:“这是刚从实验室里出来的产品,大概一周后就会在一线城市的交警队里列装了,像你这样的四线警察恐怕要还等五六年。要不是我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发起人,而且主持那项秘密工程的刚好就是我同学,我也没法这么快就拿到手。”
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我居然有个能量这么大的室友。
我努力不让自己的表情显得过于震惊,谨慎地追问道:“跟公安部有关的科研项目,连副部级的领导都不敢轻易干预吧,你那同学这么牛逼,提前一星期给你开后门?”
他哈哈笑了两声:“公安部的可不敢惹她。她可是号称生物学界的居里夫人,很有可能成为建国以来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南边那些企业抢着要她去当独立董事。那间实验室本来是只有老资历、有重大贡献的教授才有使用权限的,她写份报告我就能接入里面的神经同步仪了。”
居里夫人?是个女的?他能跟女性产生交集?我瞪大了眼盯着他,这简直比那什么质体更令人震惊。
他似乎没看出我的疑惑所在,义正言辞地接着说道:“你那什么表情?不相信女性能在科学界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告诉你,你这种大男子主义的思想是跟新时代格格不入的!”
我不想跟他争,立马把话题引导回来:“你这管…呃,盗食质体,怎么用?”
“是盗食质体合成物。”他站起来说道,“把你的头盔戴上,不然没法触发安装程序。”
我把挂在墙上的头盔取下来,戴到了头上。
“激活语音系统,然后念:‘启动盗光计划安装程序’。”他站在我面前,继续下达着指令。
“道光?这是你取的名字?你很喜欢清朝吗?”我一边摸索着头盔上的语音激活点一边说。
“不是那个道…哎你快点!”他双手环抱着,不耐烦地说。
于是我仍旧像之前那样把整个手掌摊在头盔上,轻声念出:“启动道光计划安装程序。”
蛇鳞衣左侧锁骨的位置突然安静地裂开一道竖着的缝,里面是纯黑色的材料,什么也看不清。
他用右手握住那根玻璃管,将一端靠在这道缝上。这道缝立即打开,将玻璃管的那端牢牢地包裹了起来,仿佛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接着玻璃管内传出液体流动的声音,其中的深绿色物质逐渐被灌进我的蛇鳞衣里。当深绿色物质全部消失后,那根玻璃管也恢复了透明的色泽。他一把拔出玻璃管,蛇鳞衣上的那道缝立即消失不见,仿佛从不曾存在过。
我感到那些物质从我的左侧锁骨流向了脑袋以下的所有部位,物质流过的地方都传来了凉凉的感觉,就跟涂了风油精一样。大概5秒后这些物质完全覆盖了我的身体,我感觉自己像是泡进了一个凉水池里。
“可能会有点凉,过几分钟就好了。”他检查着玻璃管内还有没有残存的深绿物质。
“蛇鳞衣怎么没跟绿叶海蛞蝓一样变绿?”我低头打量着似乎没有变化的蛇鳞衣,问道。
“你应该用过蛇鳞衣的变色功能吧?这种问题有什么问的必要吗?”他转过身将玻璃管扔进了垃圾桶。
“感觉没什么变化啊。”我扭动着腰身,蛇鳞衣的穿着感依旧跟之前一样,我甚至都没感觉到重量的增加。
“它只在必要的时候发挥作用。如果有具备高动能的物体朝你飞过来,比如有人对着你开了一枪,蛇鳞衣就会在身体即将受到打击的范围内高度致密化并吸收动能。根据南京那边的实验,可以抵挡住市面上流通的绝大多数纳米集束子弹。”他斜靠在电脑桌上,像欣赏一件杰作似的看着我。
我不禁张大了嘴,这下一线城市里的局面恐怕会被搅得天翻地覆。
“头盔呢?头盔也有强化吗?前罩玻璃呢?”
“当然,在设计的时候都考虑到了。不过你最好还是别用前罩玻璃硬顶纳米集束子弹,实验中偶尔出现了前罩玻璃致密化速度不够的情况,导致部分小弹片还是穿过了玻璃。虽说不一定会把你打死,但这个风险咱还是别冒了。”
他拿起桌上的红牛,仰头灌下了最后一口,随后说:“提供这些防护能力所需的能量,你应该也想得到,在太阳底下晒晒就能获取了。对于你们交警来说应该完全不是问题。”
突然,我感到蛇鳞衣右肩后侧变得僵硬,而且离我的体表变远了,仿佛中间多了一层气囊。接着我听到了后方传来“呼呼”的声音,像是射出的箭和空气摩擦发出的响声。
是不是蛇鳞衣设置出问题了?我张口打算问问我的室友。“咚”的一声从我背后传来,我感觉有人往我的肩膀轻轻推了一把。随后我的脚边掉下来一只鸟形生物。
“我操!”我和室友异口同声地骂了出来,他立马窜起来躲在了电脑桌后面,我下意识地抄起桌上的手枪并打开保险,转身对准地上那玩意。
躺在地上的是一只大鸟,肚子朝天,两只翅膀都摊在地面上,脑袋偏向一侧,眼睛紧闭着。应该是从厨房的窗户飞进来的,居然直接从窗户外对准我的肩膀俯冲,真是够有种的。这只鸟的颜色很漂亮,脸、肚子、翅膀里侧都是点缀着乌黑竖纹的雪白色,脑袋、背部和翅膀外侧都是蓝灰色。特别是那阿拉伯弯刀一样的喙,从根部的纯白色渐变到尖端的深蓝色,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色调高度统一,充满了设计的美感。看样子是撞晕了。
我的室友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突然激动地大声喊出:“游隼!我操!我操!我操!是游隼!”
我被他吓了一大跳,差点走火。我关上保险,仍把枪握在右手,扭头对他高声说道:“你他妈发什么疯啊!在一个枪手后面突然大喊大叫,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他的目光死死地定在地上那只游隼上,手足无措地叫道:“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猛禽重新在南方出现了!你知道有多少弃置的项目现在可以重启了吗!你知道这会带来多少机会吗!”
我被他的反应搞得有点懵,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把枪收到腰间,摘下头盔挂到墙上。等到他似乎脱离了那种亢奋的状态,我便向他问道:“这只鸟看着像基因编辑过的,会不会是从哪家宠物店的新品区逃出来的?”
听到我的话,他颤抖的身体忽然不动了。他蹲下来开始观察这只鸟,低声说道:“我确实没想到这种可能性…”
“你看这毛色就知道是编辑出来的,说实话设计得还真不错。”我也在他一旁蹲下,看着这只陷入昏迷的游隼。
“毛色?这就是天然游隼的常见毛色啊?”他抬头看着我,表情很疑惑。
呃…我从出生到现在就只在小时候见过几次活麻雀,对鸟类的认知完全来自小学时看过的几本插画书。不过这家伙不是植物学家么,怎么对鸟也这么了解?
他又低下头继续观察这只游隼,嘴里咕哝着:“没看出来有什么后天设计的性状啊…完全符合南方鸟类灭绝前的天然游隼特征…诶,这爪子怎么看着有点奇怪…”
他伸手拨弄着一根黄色脚爪末端的黑色弯形指甲,嘴巴叽叽咕咕地说着:“这个关节结构完全不正常…没有机械改造的痕迹…纯粹的有机组织…难道真是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
嘎吱一声,黑色指甲被掰开了,只有皮肉还连着,露出中空的内部。
“啊!”他被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
果然是基因编辑的产物么,我倒也没太惊讶。不过这种形态确实让我觉得十分诧异,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我伸手拽了拽那根透着锋芒的黑色指甲,里面似乎有东西。我一只手抬起并慢慢旋转着鸟爪,另一只手轻轻把指甲朝天竖起来。一团白色粉末像流沙一般从指甲内部扑到地上。
我的脑中仿佛响起了轰的一声,在徐州度过的九年人生、提交辞呈的红头信纸、她离我而去的那天下午、在感官仪中仿佛没有尽头的神经训练、击中我的那颗.22口径的子弹,这一切如同进攻的蜂群一般携着巨大的噪声钻进了我的脑海里,却让我的判断愈发清晰。
我感觉全身像灌了铅一样的沉。在室友疑惑的目光中,我颤抖地伸出右手食指,在那团白色粉末中轻轻一点,将指尖送入口中。几十个小时的感官训练早已在我的神经系统建立了无比牢固的条件反射,我即使忘了自己的警号也不会忘掉这个味道。
是可卡因。
I

Barmaster_L
8 人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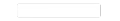
故事烩
9269 人关注




评论区
共 10 条评论热门最新